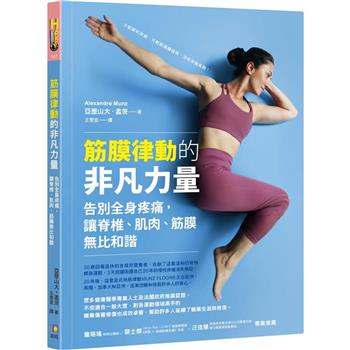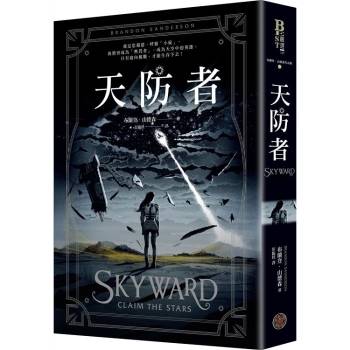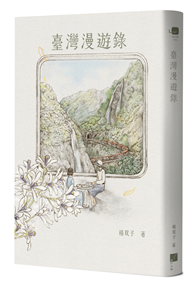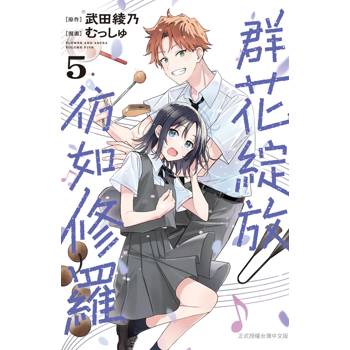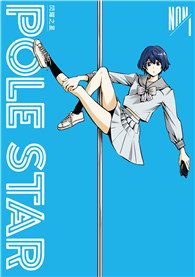譯者序
觀看醫學發展前緣的反思
王業翰
新藥物的發現在現代醫學的發展中占據極重要的地位,從盤尼西林開始,一個個突破性的新藥賦予臨床醫師扭轉病人病況與命運的神力。然而隨著醫藥科技的快速進步,醫學從過去單純針對「病人」的疾病醫治大步邁出,踏足了「健康人」的生活保養,不斷追求養生、長壽、防病於未然。光是更健康還不夠,還要更高、更瘦、更美、更帥、更聰明……這個被醫療社會學家稱作「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過程,使得藥物的服用者從病人擴展至健康人。藥物的角色在這當中逐漸轉變、延伸、膨脹,從治療疾病到控制各種生理上的風險數值,從有病治病到沒病強身。打開藥罐的動作成為生活日常,仰口吞服後開始身心舒暢的一天。藥物不只回應了人類追求健康的渴望,同時也帶來了龐大的商機,打造了繁盛的醫藥產業,跨國藥廠挾其巨大的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神不知鬼不覺地推動醫學前進的腳步。
藥廠與臨床醫療的關係一直是敏感而尷尬的問題──節節攀升的藥價、針對醫師或病人(某些國家允許)的藥品廣告、提供給醫學會與醫師的贊助、與保險機構檯面下的價格協商、對研究或臨床試驗的介入等等,在在都可能引發倫理道德的爭議與辯論。只要檢視藥廠在這之中的商業角色,沒有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因此有許多學者嘗試對藥廠在現代醫學中的角色提出批判或是懇切的呼籲,試圖排除這些商業利益對醫療可能造成的潛在道德危機,然而其中多數的論點在實務上的迴響卻極其微弱。現實世界中,藥廠追逐利益的各種手段從不可能被完全禁絕,某個程度上來講,也不宜被禁絕,因為所有人(至少包括了醫師、病人、與政府)都同意新藥研發在醫學發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至今仍然棘手的不治與難治之症──醫師需要新武器,病人需要新希望,政府需要經濟與醫療水準的提升。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沒有人相信在缺乏市場利益的驅動下,醫藥仍能基於公益性質快速而有效率地進步。因此一方面從藥廠提供的各種藥物與服務中獲益,另一方面也不阻礙藥廠的獲利,容許一定程度的行銷手段,成為現實世界中必須妥協的現況。既然倫理上的灰色空間難以避免,法規監管就成了約束藥廠商業行為的底線。臨床試驗應該怎麼做?可以宣稱藥物療效到什麼程度?對醫師與學會的贊助可以如何進行?以目前來說,各先進國家大多已發展出相應的種種規範與準則,各跨國藥廠都達到一定程度的遵法性,顯而易見的舞弊或賄賂等非法行為雖難說完全不會發生,但已非常態。這顯示出醫藥市場的一大特點:法規遵循。綿密的法規管制使得藥物的行銷有別於一般商品──什麼樣的藥品可以上市?法律允許的行銷文案與手法為何?可以在什麼通路經銷販售?都有法律的明文規範,這些規範形塑了藥廠的行銷模式,使得不同的藥廠採用了類似的手段彼此競爭──以科學數據來支持藥物的行銷。
這種以科學為名的行銷手法之所以有效, 與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興起並成為醫學主流脫不了關係。在實證醫學的架構下,各種醫學論文依其研究性質與實驗設計,可區分成不同高低程度的科學證據力。過去帶有權威性的專家意見落居最低層級,端坐在最高實證寶座的則是隨機分派的雙盲對照試驗,醫師據此在心中自有一把尺,用以評斷各方言論虛實。藥廠的行銷若要能言有所本打入人心,自然得拿出研究數據與文獻。多數醫師不認為一般常見的行銷手法適用於醫藥市場,各種文宣小物、精美包裝、誘人文案、價格競爭常無用武之地,更難以影響醫師的處方開立。選擇藥物雖然難免有個別考量(如使用經驗、保險給付等),但基本準則仍是按科學數據判斷行醫,方能避免各種不當的利益衝突與道德危機。故唯有拿出貨真價實的知識來說服醫師,藥才開得出去,藥廠也才有利可圖。
遵循法規與實證因而成為當代醫藥市場的重要特徵。然而,即使藥廠依據法規進行臨床試驗開發藥物,並據實以科學數據行銷給醫師,就真的毫無疑慮,不致衍生任何惡意誤導或欺瞞的風險嗎?希斯蒙都的《醫藥幽靈》就對這個看來講究科學證據、又受監管的醫藥市場做出了重要的提醒。
與眾多批判藥廠的書籍不同,本書關注的是醫藥知識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knowledge),也就是把知識視為一種具象的物品,探討其生產、流動與消費的背景與細節。既然行銷藥物靠的是實證醫學架構下的知識,那麼重點就不在於藥物本身的成本、定價或品質好壞,而是這些與藥物緊密相連的知識──什麼疾病或症狀適合用這個藥?為什麼需要用這個藥?跟其他同類藥相比,用這個藥的好處為何?透過發掘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的知識,藥廠業務在面對醫師時才言之有物,取信於醫師後,藥也才賣得動。故在這個重視法規、強調實證的市場架構下,我們應該關注藥物的知識是基於什麼理由,又是經過怎樣的過程被生產出來的?這些知識又是如何被代理、經銷、配送到消費者(醫師)的面前?而這些知識的消費者又是怎樣被打動、進而買單的?
經過數年的研究與調查,本書以「幽靈管理」來描繪藥廠對知識生產、散布與說服醫界過程中在檯面上下的介入手段。經此合法也合於科學的運作模式,藥廠得以相當程度地操弄醫師接收到的資訊,使種種利於其行銷的醫藥新知成為繼續教育的重點,醫師往往在不知不覺間便受到洗腦式的資訊轟炸,到達其「裝配行銷」的目的。這並非暗指醫師缺乏判斷力,易受到藥廠愚弄;也不是貶責藥廠散布偽科學或假知識。正因為幽靈管理的過程中往往產出的是真科學、傳遞的也是真知識,使得醫師更容易接受藥廠的暗示,傾向以更為先進新穎的藥物來治療病人,然而這樣的選擇卻未必能使患者的整體獲益大於藥廠的商業獲利。更進一步來說,這種由藥廠推動並塑造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未必能使現代醫學朝向最能促進整體人類健康的方向發展,因而值得我們更為謹慎警醒地看待這種現象。
從知識生產最初的源頭開始,作者揭露了藥廠對藥物研究論文提供幽靈寫作與發表規劃的介入模式。為了製造有利於販售藥品的知識背景,藥廠發起或贊助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研究,這些研究在發表為學術論文後為藥品的行銷增添柴火,帶來動力。為了讓這個過程有效率、並達到最大的行銷目的,藥廠會委託發表規劃師管理專案的研究與發表進度,並雇用幽靈作者主動撰寫論文。一方面掌握研究主題並確保結果詮釋合於藥廠利益,另一方面則以此與醫界關鍵意見領袖打好關係。這樣的操作手法顯然違背一般研究者信奉的學術倫理,作者坦率而直白的陳述,想必也讓許多清白正直的醫師感到冒犯。但我會建議,不必爭論這種情況究竟是少數個案還是普遍通例,而是要覺察體悟到現代的醫學研究主題,極度容易與藥廠瀰漫四溢的商業利益搭上邊。藥廠當然不可能主導世界上的每個研究、捉刀撰寫每篇論文,如一類稱作「研究者自發型試驗」就是由研究者獨立發想、申請贊助、執行完成後發表論文的。雖然這樣的研究反應了純粹源於醫學專業的學術興趣,但我們同樣可以想像藥廠為何會願意贊助這樣的試驗?為何藥廠審查完提案後,決定贊助這些研究而非其他?預算大小、與試驗主持人的關係等自然都會是決策時的考量重點,當某些試驗更有利於商業利益時,藥廠會更願意提供贊助。當然這些研究成果大都對病患有利,而且出發點也都是基於追求病患的利益。然而需要謹慎提防的是,當病患利益與藥廠利益出現可能衝突時,這樣的體制是否還能及時有效地產出知識,並讓這些科學事實公告周知。
講到醫藥知識的流通,期刊論文發表與醫學繼續教育無疑是醫師獲得新知的主要管道。藥廠透過發表規劃,除了能儘快讓於己有利的研究成果以最好的方式(通常是世界級的醫學會、或重要的期刊)面世並廣為流傳外,同樣也能委婉地壓制不利於己的消息快速散播。雖然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現代,失敗的臨床試驗幾乎也是在第一時間就會在專業社群間快速流傳,但絕不會有任何一位藥廠業務主動跟醫師討論或提醒:「對,我們那個試驗失敗了,建議您暫時不要對病患使用此藥。」更多的時候反而是澄清與消毒。要能正確合宜地解讀科學文獻,促使有利行銷的知識流通,藥廠就需要動用關鍵意見領袖的影響力。
本書花了相當篇幅來描繪善用關鍵意見領袖在醫藥行銷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這些直言不諱的陳述恐怕比對幽靈作者代筆的部分更加令醫師們感到不悅。畢竟能夠被邀請擔任掛名作者的醫師與研究者僅是少數,但接受過藥廠邀約擔任演講者的醫師可就不少,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醫師恐怕都無法認同自己精心準備的內容只是藥廠行銷的工具,多數講者為了自己的專業名聲也都會努力平衡內容,避免學術演講淪為商業宣傳。儘管如此,從知識的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仍然無法抹滅藥廠舉辦或贊助的醫學演講最終仍將導向其商業利益。議題設定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在政治上,有錢有權設定議題的一方,才能充分掌握話語權,進而主導輿論走向。由這樣的觀點來看藥廠贊助的演講,所有受邀醫師的發揮空間都被會議主軸所框限,也從來不會有人舉辦以少用藥或不用藥就能有效治療病患為主題的講座。如果這樣的舉例太過極端,也可以回想一下,當某個藥過了專利期,或是該公司有了取代自家老藥的新產品時,這些老藥在醫學講座中是否就如被打入冷宮般,鮮少有相關的講題?在主辦方定下會議主題的那一刻起,就算所有醫師的講稿都是自己準備的,就算都以最公正客觀的角度來論述相關的醫藥新知,這些活動本身也在提供繼續教育的同時,無可避免地打造並推進了一個更適於用藥、更善於用藥的醫療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