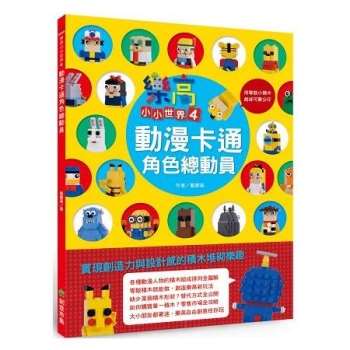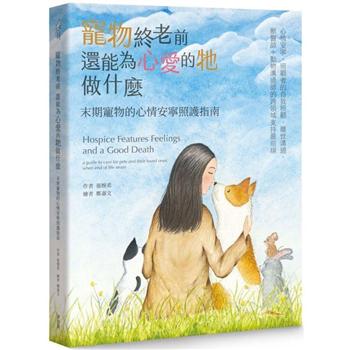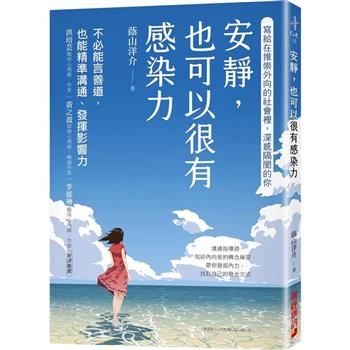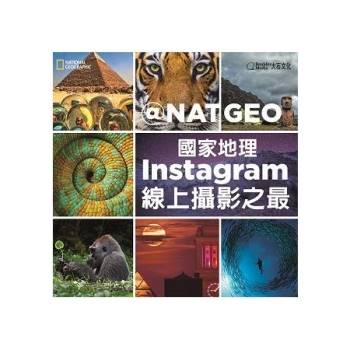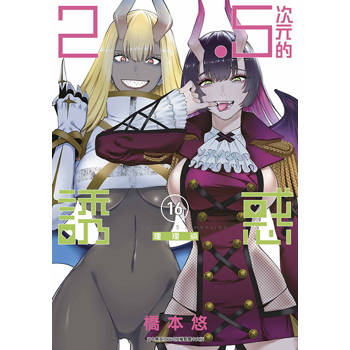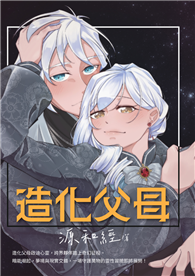前言
「安內攘外」政策,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1930年代前半期處理國政事務的基本方針。他強調一切以先求「國內統一」為要,而將抵抗日本侵略的急迫性置於剿共之後;故對日方進逼,採取退卻戰略,妥協政策因此成為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應對日本的主旋律。
此一妥協政策反映到中日關係的具體情勢,是日本軍方在華北地區肆無忌憚的開疆拓土;「進軍熱河」、《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華北五省自治」,可謂其分割華北地區有成的五部曲。然對中國人而言,不啻一段喪權辱國、尊嚴掃地的民族悲痛史。
評析「安內攘外」政策的是與非,向來是海內外學術界歷久不衰的熱門議題。例如以單一事件為主題研究者,無論是聚焦於熱河戰役、長城保衛戰、《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盧溝橋事變等事件的相關研究,不勝枚舉;而以探討相關人物為觀察視野的主題研究,也不在少數。
以1930年代的中日關係或抗日戰爭,或國共關係為主題的研究專著中,「安內攘外」政策更是必須觸及的課題。例如質疑何以先安內再攘外者,將其視為「違背全民族的意志」之反動國策。認為此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國民黨政權者,則將其解讀為「妥協與抵抗」。而從維持民族生存與發展角度論述者,則將其詮釋為國民政府的「應變圖存」。而從忍辱負重角度論述者,則稱讚其為國民政府的「對日備戰工作一大成就」。
海峽兩岸學術界對「安內攘外」政策評價不一,日本學術界則是一致推崇,將國民政府能戰敗日本,歸功於蔣介石備戰有成。惟日本政府何以輕易發動侵華戰爭,各家解說不一。有的研究將其歸咎於日本政府長期縱容日本駐華日軍,讓軍方主導國家走向。有的研究認為日本政府長期低估蔣介石的抗敵意志。有的研究指出日本政府低估國際社會的反彈。有的研究顯示日本政府內部失控導致。有的研究則歸咎於元老為了維護天皇體制,不敢與軍方對決。
顯然,戰後的日本,在全面承認啟動戰爭是錯誤的選擇後,學術界已無質疑「安內攘外」政策合理性的聲浪。他們的重點聚焦於何以當時的日本政府不能認清「安內攘外」政策的實際成效?對日本政府的重大誤判,又該如何解讀?
海峽兩岸學術界對「安內攘外」政策,雖有評價不一的爭議,然無論持否定或肯定論者,基本論述的主軸仍未脫離民族大義。前者強調其違背全民族意志;後者強調「安內攘外」政策達到階段性任務以後,各方政治勢力最終之所以不計前嫌而願與國民政府共赴國難,還是因蔣介石堅守民族大義之本分。
可是這一些以民族大義為主軸的論述,尤其固守國族主義之觀點,仍援用國與國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既有框架之研究取徑,卻難免忽略華北地區及1930年代中日關係的特殊性。以前者而言,華北問題之難解,除了日軍入侵熱河省時,民眾不堪軍閥暴虐,主動開城降敵;其餘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河北等華北五省,名義上雖屬國民政府中央管轄,實際上皆為軍政自主、財政半自主的狀態。而且所有掌管軍政大權的要員均出自北洋軍系,並皆曾與國民政府兵戎相見,中央、地方自始欠缺互信基礎。在華北地區權力架構還沒有定於一尊,日本軍方自然有眾多可操縱的機會,也讓日本政府一度誤信可在華北地區複製滿洲國模式。
以後者而言,1930年代的中日兩國皆是多事之秋。當時的日本,正處於軍方奪權、憲政體制瓦解、暗殺橫行,動盪不安的脫序時代。日本的內政場景,在外交層面的反映,無非令出多門,軍方及外務系統除相互爭取對華政策的主導權;各自內部派系林立,相互傾軋。相較於日本內部的動盪不安,中國國內秩序的混亂程度亦不遑多讓。除了長年的國共內鬥,國民政府內部有蔣介石主軍、汪兆銘主政的軍政二元化體制之間的猜忌與制衡;外部有南京派及西南派之爭;中央當局對眾多半自主的地方省分,更是欠缺實質的管轄能力。是以,1930年代的中日關係史,可以說是一部多方勢力相互角逐的鬥爭史。雙方國內政爭不斷,也讓兩國政府的對峙,已非單純的國與國之間的權力利益之爭,更廣泛的涉及兩國內部各派系之間爭奪政治主導權的生死之戰。參與角色眾多,局勢詭譎多變,可謂此一時代的主要風貌。
既有研究成果中,雖有少數研究注意到國共內鬥及華北地區的特殊性,而將其援用為探索當時中日關係時的重要元素。例如石島紀之,聚焦於「安內攘外」政策與國共內鬥之間的互動關係;探討中共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逼使蔣介石放棄「安內攘外」政策之始末。Marjorie Dryburgh的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 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認為通過考察「南京國民黨政府與華北地區的緊張關係」,可以看出宋哲元與南京政府之間的矛盾與較勁;故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中日關係,並非雙邊關係,而是三邊關係。另外,長年從事日軍謀劃華北五省自治研究的內田尚孝,所著《華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1932─1935年》,詳細剖析了日中雙方對塘沽停戰協定解讀不一的來龍去脈,以及日軍爾後逐一在華北地區擴展影響力之過程。而光田剛的《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1928-37年》,則分析了1928年到1937年間的華北政局;該書對於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黃郛等要素,以及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
關於國人晚近的專著,以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為代表。該書針對「不抵抗政策」、華北危局、關內外通車通郵交涉、華北自治運動、南京「從安內到攘外」的變遷等,均有論述。其特色是大量援用《蔣中正總統檔案》等史料,從中國內部派系爭鬥不斷之角度,解析國民政府與華北各地方首長之間的合縱與連橫,進而整合抗敵之經緯。
以上的既有研究,皆各有見地,但因研究的主題侷限於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爭鬥,或中、日及華北地方首長之間的三邊關係,忽視日本政府內部派系互鬥對華北政局造成的影響。易言之,1930年代中日兩國政局的詭譎,除了國民政府無法駕馭華北地方首長,日本政府同樣也無力駕馭日本軍方,日本中央軍方本部又無力駕馭派駐在東北及華北的軍隊。華北問題之複雜棘手,緣於這是一場涵蓋國民政府、日本政府、日本軍部、日本駐華日軍以及地方首長等五方勢力相互競合的鬥爭。在沒有一方能僅憑一己之力掌控全局的情況之下,不將五方勢力的角逐皆納入觀察視野,將無法掌握蔣介石在執行「安內攘外」政策時的所思所見及所行。
有鑑於此,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既非就軍事論軍事,亦非單純分析國與國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而是從中日雙方國內政爭不斷的時代特點出發。在結合兩國國內各派系之間爭奪存活的研究架構中,探討中日圍繞華北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具體檢視蔣介石在熱河戰役、長城保衛戰、《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盧溝橋事變等一連串戰和過程中的對應策略,冀望建構出不同時空背景如何影響他主觀意志的分析框架,進而掌握「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以及蔣介石落實這項政策的準則。特別是解析他在處理華北事務時,堅持與退讓的基準何在?盧溝橋事變時,他又為何不願再退讓?
1928年6月,國民政府雖然宣稱北伐成功,實質僅是驅逐原先控制華北區域的張作霖集團出關;易之以新加入北伐陣營的閻錫山晉綏軍、馮玉祥西北軍兩大集團,分而治之。及至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又得借重張學良入關救援,方能順利擊潰閻、馮兩大軍閥。張學良既已入關,乃又順理成章成為統率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等華北五省,及北平、天津、青島三市的新霸主。
1931年7月,歷經原西北軍系的石友三變亂後,宋哲元及傅作義即由張學良力保,翌月分別出任察哈爾省及綏遠省的代理主席,華北形成三軍系鼎立之勢。亦即,察哈爾重歸西北軍系的宋哲元,山西及綏遠則由晉綏系的徐永昌、傅作義領軍;河北及平津、青島三市仍由東北軍主政;山東省則是交由早在中原大戰以前就歸順中央的原西北軍系韓復榘。
易言之,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地區的政務,名義上是由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主持,然張學良直接管轄的只有河北省及平、津、青島三市;其餘各省仍由原東北軍系的湯玉麟,及原本分屬晉綏系及西北軍系的各軍頭領軍。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也無權直接過問華北事務。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脈絡,本書特以蔣介石對中日局勢的認知為經,兩國多元勢力相繼投入及競逐的互動為緯,逐一探討蔣介石如何籌建團結全國的備戰工程。
本書第一章,聚焦於探索華北地區的多元勢力所導致長城保衛戰的困境。首先解析熱河省主席湯玉麟雖曾署名「滿洲國宣言」,然因與主持華北大局的張學良在北平共同經營鴉片專賣,得以繼續盤據熱河之緣由。其次,再以湯玉麟與張學良、蔣介石等三人之間的權力與利益共生關係為研究線索,解析國民政府在熱河戰役失利的前因後果。最後,強調長城保衛戰是國民政府動員華北各地方派系的軍隊,在統一指揮的體系下禦敵的初步嘗試。華北軍隊在各戰場的抗敵表現,不僅影響戰事的發展走向,也影響戰後華北地區的政治結構以及中日兩國在華北的布局。論述的主軸,在於介紹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對長城各關口的攻防部署;進而詳述中央軍進駐華北以及在統一指揮系統下,國軍在長城各關口的奮戰經過。接著,再以蔣介石在落實抗日政策上,對華北地區的適用順序,以及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之間在對華政策上的異同為研究主軸,探索何以《塘沽協定》成立的時空背景。
第二章,以行政院政務整理委員會的成立始末為焦點,探討蔣如何任用黃郛,以在華北建立親日反共政權為誘因,爭取日本政府及關東軍的認同;並藉此接收戰區及完成關內外的通車及通郵談判過程之經緯。黃郛之所以為關東軍接受,關鍵在於關東軍認同其過去的資歷,期盼與他取得合作基礎,在華北建立一個親日地方政權;但在實際的交涉過程中,卻逐漸發現,黃郛不僅無意培植嫡系武力,也無意擺脫國民政府,且一心敷衍關東軍。於是,關東軍決定主動出擊,先藉由《何梅協定》,以赤裸裸的武力逼使國民政府勢力退出華北。其次,又改推宋哲元入主北平,希望藉由他成立五省三市的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發行獨立通用貨幣,並與日圓掛鉤,建構日華經濟圈。
針對宋哲元成為日本軍方利益代言人後的華北新變局,解析蔣介石何以憑藉「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成功瓦解關東軍所策動的華北獨立運動之始末,則是第三章的主題。復次,再藉探討蔣介石所倡導「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以及他又如何在安內攘外的大戰略架構下,利用其與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關東軍、宋哲元等四方勢力的互相牽制,成功維護中國在華北主權之始末。
宋哲元既然是以日本軍方代言人的身分入主冀察兩省,當他無意再替日本代言時,不僅意味著日本軍方將棄他而去,冀察政務委員亦將無以為繼。尤其中日兩國之間已無緩衝者,稍有摩擦,星星之火即可燎原。第四章即旨在探討「盧溝橋事變」的緣起,以及事變擴大的原委,並將導致衝突的各種因素,尤其西安事變以後國際情勢變化,如何促成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改弦更張,進而在事變發生後勇於一搏的來龍去脈。最後,再以「一擊論」成為日本陸軍主流思維之始末為軸心,探索何以此一過程最後成為主導兩國走向全面戰爭的經緯。
「消滅反側」、「厚植中央政府國力」、「迴避對日作戰」,是「安內攘外」政策的三部曲。藉剿共之名,讓中央軍可順勢入駐原本半獨立自主的各省分,將桀驁不馴的地方勢力納入中央政府體系,是蔣介石籌建全國團結備戰工程的一環。至於剿共何以可迴避作戰,乃因當時中共向持敵視日本的姿態,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抗日,是其爭取國民認同的最重要手段。而日本為了維護天皇體制,一向視提倡平民革命的共產主義者為勢不兩立的大敵。蔣介石意識到中共與日本互不相容的敵對態勢,在剿共議題上與日本有合作的空間。
易言之,如何維繫日本政府在華北地區的主導地位,日本政府與關東軍、天津軍之間有相當差距。日本政府認為,維繫一個穩固的國民政府,將有助於兩國在華北建構合作反共之體制;特別是在國內暗殺事件不斷、前線將士動輒滋事,政府忙於善後,惟有維持現狀方符合日本利益。
相較於日本政府尚存與國民政府合作想法,關東軍與天津軍則時時以在中國擴張勢力為念。然關東軍及天津軍內部有皇道派及統制派之爭,兩派的共同想法是:熱衷對蘇備戰、堅持滿洲國不可放棄,以及中滿接壤需設緩衝地帶。惟如何處理對華關係,兩派頗有爭論。皇道派的對外政策雖以「反共反蘇」自居,一向高唱蘇聯才是心腹之患,主張早日解決蘇聯,然又不欲與同樣推動反共政策的國民政府為結盟對象,使得該派言行反而成為鼓動中國各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外來勢力。
統制派則主張:為確保能戰勝蘇聯,需先鞏固滿洲國,並收編國民政府。其雖倡言不惜與國民政府一戰,但若國民政府願承認滿洲國的既成事實,兩國不獨可共謀親善,也可合組中日滿三國反共聯盟。皇道派表面主張激進,言必欲國民政府勢力徹底退出華北,實際上期望華北一直處於懸歭的緊張局面,以利自身派系發展。
面對此局勢,國民政府表面上拉攏統制派,私下卻寄望皇道派攪局,兩派對立。皇道派屢欲滋事,每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實際上戰事終未爆發,中方所失有限,華北的主權終能在風雨飄搖中維持。
上述史實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在研討「安內攘外」政策時,鮮少著墨之處。故本書的意義,除了補闕既有研究,釐清蔣介石何以在華北採取「退卻戰略」的前因後果外,也希望從蔣氏籌建全國團結的備戰工程之脈絡,具體評析「安內攘外」政策的成果,並給予其應有的評價。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中日華北攻防: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再評價(1932-1937)的圖書 |
 |
中日華北攻防: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再評價(1932-1... 作者:黃自進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25-02-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精裝 / 504頁 / 15 x 21 x 7.0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科學科普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教育學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日華北攻防: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再評價(1932-1937)
本書在研究的方法上,既非就軍事論軍事,亦非單純分析國與國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而是從中日雙方國內政爭不斷的時代特點出發。在結合兩國國內各派系你爭我奪、生死存亡的研究架構中,探討中日圍繞華北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具體檢視蔣介石在熱河戰役、長城保衛戰、《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盧溝橋事變等一連串戰和過程中的對應策略,冀望建構出不同時空背景如何影響他主觀意志的分析框架,進而掌握「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以及蔣介石落實這項政策的準則。特別是解析他在處理華北事務時,堅持與退讓的基準何在?盧溝橋事變時,他又為何不願再退讓?
作者簡介:
黃自進,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客座助教授、日本立命館大學客座教授、慶應義塾大學特別研究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著有《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北
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蔣介石と日本:友と敵との狹間で》、《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阻力與助力之間:孫中山、蔣介石親日、抗日50 年》、《圍堵在亞洲:日美同盟關係的深化(1960–1972)》、《中日華北攻防: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再評價(1932–1937)》以及主編史料彙編、專書論文集多本,並撰有近代中日關係及戰後日本外交等相關論文80 餘篇。
章節試閱
前言
「安內攘外」政策,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1930年代前半期處理國政事務的基本方針。他強調一切以先求「國內統一」為要,而將抵抗日本侵略的急迫性置於剿共之後;故對日方進逼,採取退卻戰略,妥協政策因此成為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應對日本的主旋律。
此一妥協政策反映到中日關係的具體情勢,是日本軍方在華北地區肆無忌憚的開疆拓土;「進軍熱河」、《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華北五省自治」,可謂其分割華北地區有成的五部曲。然對中國人而言,不啻一段喪權辱國...
「安內攘外」政策,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1930年代前半期處理國政事務的基本方針。他強調一切以先求「國內統一」為要,而將抵抗日本侵略的急迫性置於剿共之後;故對日方進逼,採取退卻戰略,妥協政策因此成為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應對日本的主旋律。
此一妥協政策反映到中日關係的具體情勢,是日本軍方在華北地區肆無忌憚的開疆拓土;「進軍熱河」、《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華北五省自治」,可謂其分割華北地區有成的五部曲。然對中國人而言,不啻一段喪權辱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山田辰雄序
黃自進君早年專研日本政治思想史,爾後逐漸將領域擴展到近代中日關係,並以中日戰爭為主題。
歷來的中日戰爭研究,大多從國共對立到合作共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攜手抗敵為敘事範本。然本書將視野擴大到1930 年代初期中國多元政治勢力同時並存的政治現狀;強調國民政府實際能支配領域有限,面對的卻是眾多治權不及的區域,例如中共控制的華中地區、親日傀儡政權控制的冀東地區、日本控制的東北地區、部分獨立派領袖控制的華北地區以及廣東、廣西、四川等地。面對這些不服從國民政府管轄的地方勢力,蔣介石如何反制,以求有效...
黃自進君早年專研日本政治思想史,爾後逐漸將領域擴展到近代中日關係,並以中日戰爭為主題。
歷來的中日戰爭研究,大多從國共對立到合作共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攜手抗敵為敘事範本。然本書將視野擴大到1930 年代初期中國多元政治勢力同時並存的政治現狀;強調國民政府實際能支配領域有限,面對的卻是眾多治權不及的區域,例如中共控制的華中地區、親日傀儡政權控制的冀東地區、日本控制的東北地區、部分獨立派領袖控制的華北地區以及廣東、廣西、四川等地。面對這些不服從國民政府管轄的地方勢力,蔣介石如何反制,以求有效...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山田辰雄序 iii
自 序 v
前 言 1
第一章 華北地區的多元勢力與長城保衛戰的困境 13
一、華北權力架構的多元化與熱河戰役失利 14
二、長城保衛戰三部曲 57
三、和議難成 73
第二章 《 塘沽協定》與「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的階段性任務 95
一、蔣介石的和戰策略及黃郛出任政整會委員長 95
二、《塘沽協定》的簽訂與餘波 117
三、政務整理委員會的成立 140
四、政務整理委員會的結束 168
第三章 「 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方策動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之間的角力 191
一、「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 191
二、「...
自 序 v
前 言 1
第一章 華北地區的多元勢力與長城保衛戰的困境 13
一、華北權力架構的多元化與熱河戰役失利 14
二、長城保衛戰三部曲 57
三、和議難成 73
第二章 《 塘沽協定》與「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的階段性任務 95
一、蔣介石的和戰策略及黃郛出任政整會委員長 95
二、《塘沽協定》的簽訂與餘波 117
三、政務整理委員會的成立 140
四、政務整理委員會的結束 168
第三章 「 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方策動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之間的角力 191
一、「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 191
二、「...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