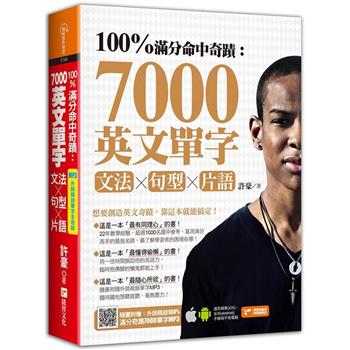已遠之聲,尚有殘響──
未走的你們務必平安健康。
★港台多項重要文學獎得主、香港七○後小說家——張婉雯,首部台灣出版作品
★全書借題張國榮音樂曲目的短篇小說集,著眼青壯世代,將舊日璀璨帶入下一恆光
★房慧真•洛楓•朗天•陳慧•黃宗慧•黃宗潔•楊佳嫻•董啟章•鄧小樺•謝曉虹——有心推薦
荒地者、無眠者、戀慕者、腐壞者、虛耗者、
憾念者、歡愉者……乍洩春光裡,到處傳奇。
借題張國榮的音樂曲目,
玻璃之城所鏡射──
原來城市另有一座真實,
原來凡事的反面另有洞察。
原來不慣適的角度,
方能將舊日璀璨帶至下一恆光
「這些年來,我,與我身處的香港,均產生了極大變化,經歷過飛揚,置身於困頓。
儘管生病與追星只是個人經歷,但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點時代的陰影吧。」
有心人∣婉雯多年前有了「以張國榮的作品為題,出一本小說結集」之想法,起初紀念少女時期偶像的單純念想,年歲匆匆,時代與社會高速遷異,感於青年世代面臨著與當年己身截然不同的處境,環境、政策、矛盾、運動……原為香港黃金年代裡熠熠璀璨的icon張國榮,反而成為嘗試解構的投射與美化,或許不是擺脫,而是該如何帶著過往旋律往前,找到新的香港日常。過往擅於寫實取材的婉雯,本次更多從角色內在出發,描繪他們生活裡的多重拉扯,看似無終點,卻已有深厚定見。書中如小津安二郎的低仰視角,淡化敘事者位置,以凸顯小人物之於當代的龐大心境,卑微、怯懦、安適、寬容等等,舉輕若重,一首首曲目下,等待的是掠過左鄰右里間的光影。昔時流轉卻人事已非,這座玻璃之城所折射出的寫實的幻影,是你也會突然哼起的那首張國榮。
作者簡介:
張婉雯∣生於香港,喜歡寫作,關心動物。小說集《那些貓們》、《微塵記》皆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潤叔的新年〉獲聯合文學新人小說獎(中篇小說);〈明叔的一天〉獲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短篇小說),另獲香港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等。曾出版《參差杪》、《那些貓們》、《微塵記》、《甜蜜蜜》等。
章節試閱
〈灰飛湮滅〉
在我丈夫失踪的時候,我的貓病了。
我的貓病了,鼻子長出了腫瘤,柔軟而岩巉;膿水隨著呼吸流動,使貓的鼻梁不時變形,貓的樣子也因此變得陌生。那是怎樣的一回事?那似乎是同一個靈魂被丟進不同的軀殼中;又或者,每次打開門,都發現自己置身於不同的房間裡……貓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的變異;牠依舊盡最大的努力生活,進食、上廁所、睡覺。然而和貓一起活在的這個城市的我,卻確實地感受到這種難測的詭異的變化。
我的貓病了的時候,我剛好懷孕了,而我的丈夫失踪了。於是我獨自帶貓去看醫生。我把牠放進寵物用的手提籠子裡,走在煙霧瀰漫的街上。到達獸醫診所時,我才發現我熟悉的醫生已經離開了──我的意思是,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城市。診症室裡是一位新的、年輕的醫生。我站在那裡,花了一些時間,消化又一個舊人離去的事實。
「你好,」年輕的醫生說,「我姓余。」
「你好。」我的聲音從口罩後傳出,比正常的模糊低沉,「我……」
我不知道事情該從何說起;而且,我這時才發現,余──余?──醫生沒有戴口罩。他的臉清楚地呈現在我面前:長臉、尖下巴、薄薄的嘴巴。
「動物不懂得人話,動物的主人也不懂得動物的話。」余醫生似乎知道我在想什麼,「我身為動物與人之間的橋梁,必須讓雙方看到我的表情。」
「嗯嗯。」我說,想不出回應的話。突然見到一張完整的臉,令我有點震驚。
「讓我看看你的貓,好嗎?」余醫生說。於是我打開籠子,把貓抱出來;牠的鼻與在家時又有點不同了,彷彿我在養很多頭不同的貓,又彷彿我在養同一頭如觀音一樣,變身三十三遍的貓。
「噢,乖乖。」對於貓的樣子,余醫生一點也不害怕,「你好。」
貓由他撫摸著,閉上眼睛,沒有反抗。
「牠的鼻,什麼時候開始的?」余醫生問,語氣很平靜。
「大約是…」由於熟悉的醫生已經走了,我得把事情重新說一遍,「大約是,煙霧開始蔓延的時候。」
余醫生的目光仍然停留在貓身上。貓的毛色因病已暗啞無光;本來白色的地方變灰,本來灰色的地方變白,像老者僅餘的毛髮。
「最近,因為煙霧而患病的個案,多了。」余醫生斟酌著字眼,「人,和動物,都是。」
我不作聲。對於疾病我了解不多。
余醫生為貓做了仔細的檢查。他輕輕地打開貓的嘴巴、眼瞼;翻看耳朵;從脖子開始輕按,按貓的胸口、腹部、大腿的內側。看著醫生的手指,我彷彿觸摸到貓的心腎膀胱:乾癟,鬆垮、失去彈性。然後,余醫生拉起貓的尾巴,看看貓的肛門口。
「很乾淨。」余醫生終於抬起頭,「你照顧得很好。」
我勉強地微笑了一下,然後想起自己仍戴著口罩。
「謝謝。」我只好說。
「我看過貓之前的病歷。牠的確是因為煙霧的緣故,長出了腫瘤。這種病太新了,坦白說,我們暫時沒有針對性的療法,因為沒有人知道煙霧的成分。」余醫生依然維持他平靜的語氣,像說著一宗日常必然遇上的事,「我能做的,就是盡量維持貓的生命質素,讓牠和你都不用太辛苦。」
我不作聲。我知道余醫生說得對。類似的說話,我已聽過很多遍。余醫生一邊輕聲和貓講話,一邊替貓打了點皮下水;然後,開了營養液,一點點地用小匙給貓餵食。貓湊近,聞了一下,試探著黏一口,轉過頭去。余醫生放下小匙,摸著貓的背,跟牠說話,好一會,又把小匙遞到貓的嘴邊。於是貓又重複剛才的動作。他們這樣來來回回,我在旁邊看著。
「以前的醫生都用針筒,從嘴邊打進去。」我說。
「針筒的好處是分量準確,而且省時。但到了這個階段,我覺得貓的感受比較重要。」余醫生臉上掛著微笑。「是不是呢?小貓咪?」
事實上,貓已經七歲,一點也不小了。牠來我家的時候也已經兩歲。貓是某個社區的街貓,吃垃圾長大,長相不算討好,直到兩歲才來我家。
三十分鐘後,余醫生終於把五十毫升的營養液餵完。在等候的期間,我坐在一旁的摺凳上,拉下口罩,慢慢地喝水。
「不好意思,讓你久候了。」余醫生終於抬起頭來,「貓的胃只有一個乒乓球的大小。如果餵得太急,牠會很辛苦。」
我拉上口罩,「我明白的,謝謝你對牠有耐心。」
「可以的話,下星期再覆診。」余醫生看了我的肚子一眼,「你有其他家人可以帶貓來嗎?」
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自己帶牠來便可以了。」
「貓是很聰明的動物,牠們能感受飼主的情緒。」余醫生點點頭,「照顧一頭生病的動物並不容易,希望你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謝謝。」我由衷地說。貓大概也累了,打開籠子的門,牠便自動走進去,等著我帶牠回家。
「護士會替你叫車的,在車來到之前你可以在候診室休息。」余醫生替我打開診症室的大門,「路上小心。」
他看著我微笑。我這才驚覺自己已許久沒見過笑容。
回家後我把籠子打開,貓便走到熟悉的窩子裡睡著了。外出讓牠疲倦,我也是。然而在休息前,我必須先把口罩除下,用信封裝好,丟進有蓋垃圾桶裡,洗淨自己的雙手,換衫,把外出的衣服丟進洗衣機,倒進消毒劑,開洗衣機,然後休息。街上的煙霧不知何時出現也不知何時消失;而無論如何,空氣中殘餘的粒子仍然飄落四周,滲進衣物的纖維、人體的頭髮與毛孔中。
沒有人知道煙霧何時來襲。上一次帶貓出門看病,我在街上遇見一群不認識的人。據說他們負責維持秩序。
「你大肚的,你上街幹什麼?」他們問。
「散步。」我答。
「散步?」他們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遍,彷彿我是個瘋婦。我沒能力解釋太多;如果我告訴他們,因為貓長了腫瘤,要帶牠求醫的話,大概只會得到「這個時候還要顧貓來作什麼」之類的回答。
「是的,我想散步。」
「大肚就別出門!回去吧!」他們又說。
煙霧刺鼻的氣味使我流淚,我無力辯駁,只好離開。
現在,我拉上窗簾,攤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覺得自己像一條被海水拋上岸的魚,唯一能做的是等待,等待另一個浪把我捲回水中。貓喝了營養液,大概不會肚餓;我閉上眼睛,強迫自己入睡,卻不成功。胎兒在我的子宮內動了一下。我再次爬起來,倒了一杯豆漿,迫自己喝下。
一個星期後,我和貓再次出現在余醫生的面前。我仍然戴著口罩。余醫生仍然露出整張臉。
「貓咪還好嗎?」余醫生問。
「差不多吧,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差。」我答。
「沒有變壞,就是好事了。」余醫生把籠子打開,把貓抱出來,「啊,感覺體重沒太大變化呢。」
接下來,像上次一樣,余醫生用手替貓的身體進行檢查。這次,貓的鼻子變成了橢圓形,大小相差無多。
「旁邊有一張凳子,你先坐下來吧。」醫生說。我這才發現,上次的摺凳已換成堅固的木凳,有椅背的。
「不用抽血嗎?」我問。
「對有病的動物來說,血是很珍貴的。」余醫生的指頭在貓的頸上按壓,「能不抽便不抽。」
我坐下來,忽然感到疲累的感覺蔓延全身;診症室的光管散發著刺眼的白光,把一切傷口與病變照得清清楚楚;我在這強烈的燈光中努力地保持清醒,好幾次幾乎打起盹來。
「剛才過來的時候,的士司機繞了路。他說,前面街口爆發了煙霧。」為免自己睡著,我只好找個話題。
「是的,就在診所附近。」余醫生拿起聽筒,「如果你早十分鐘到,大概進不了門口,我們臨時拉閘了。」
「啊?」我清醒過來,「有這麼嚴重嗎?」
「護士嗅到煙霧的氣味,便馬上拉下鐵閘。診所裡都是病弱的動物,有的在留醫。我們要盡力保障牠們的安全。」
說罷,余醫生把聽筒貼在貓的胸口,檢查心跳與呼吸。我只好閉上嘴巴;睡意再次滲進我的身體,像水緩緩上漲。
「很好。」
我醒來。
「呼吸的聲音清楚,心跳有點快,但暫時沒有雜音。貓很努力,你也照顧得很好。」
這句話無端令我有流淚的衝動。我以為煙霧又攻進來了。
「我現在要餵營養液了。」醫生放下聽筒,「會用上一些時間。」
「會不會太麻煩你呢?你上次示範過,我想我做得到。」
「不是因為擔心你做不到,而是,身為醫生,看見患病的動物進食,是很快樂的。」余醫生把枱面的燈亮起,關了天花板的一枝光管,「你好好休息一會。」
然後,跟上次一樣,余醫生一邊餵食,一邊跟貓溫柔地說話;在這些低語中我毫無抵抗力,迅速掉進睡眠中,連夢都沒有一個,直至光再次在頭頂亮起。
我張開眼睛。余醫生抱著貓,抬起頭,看著我。我看一看手表──我睡了四十五分鐘。
「非常抱歉。」我連忙站起來。本來放在大腿上的手袋掉在地上。
「沒關係。」余醫生彷彿看不見我的狼狽,把貓放進籠子中,「能夠好好休息,對人和貓都是很重要的。」
「謝謝。」我收拾好手袋裡掉出來的東西,帶著貓逃出診症室。
是的,自從貓生病以後,我的睡眠變得很淺很淺;我生怕牠會在我熟睡時死去。以前,我的丈夫總是工作到夜深;醫院的工作太忙了,日間要看的症太多,文件只能晚上做。丈夫是個認真的人;一想東西便皺眉。未結婚時我以為那是良好的品格與引人的魅力,婚後我才發現,家裡的氣氛會因為一個認真的人而凝固。那時我是處於懷孕初期,總是感到疲累;每一晚,我都如同掉進枯井裡似的,掉進了睡眠。偶爾半夜醒來,我看見我的丈夫仍然開著小小的夜燈,在電腦前工作。
「我吵醒了你嗎?」他問。他的目光仍然逗留在屏幕上。
「不,」我答,「沒什麼。」
「你先睡吧。」他說,仍然沒有朝我看。於是我爬起來,把蜷曲在床尾的貓抱到身邊。
「貓身體裡的弓型蟲會影響胎兒。」丈夫終於望向我。
「家裡的貓不吃生肉,沒事的。」我答。
「我知道,不過提一句。」丈夫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電腦上。於是我再次矇矓睡去。那時我還不知道,一場無以名狀的煙霧將會覆蓋全城,而我的丈夫和他的同袍正在討論一些奇怪的先兆,例如患上呼吸道疾病、驚恐症、憂鬱症的人在同一時間增加。醫院的病床只能開到走廊上與廁所門前,但管理層卻不讓前線醫生說話。這些,都是在我丈夫失踪後,我才知道的。
逐漸,我聽到風聲,說是別區開始出現不明氣體,刺鼻如同燃燒時的柏油──燃燒的柏油其實是怎樣的?那會像火山爆發時的熔岩嗎?還是鐵鍋中滾動的熱油呢?終於,某一個晚上,我們正打算入睡之際,窗外忽然傳來一聲聲的驚呼;我們望出去,見到外面灰暗厚重的、雲樣似的濁氣正向這邊移動。我走近窗邊,尖刺的氣味像無數枝針扎進鼻腔、眼眶。
我咳嗽起來。丈夫把我拉開,把窗關上,拉上窗簾。
「我要出去一趟。」丈夫說,開始收拾上班的背包。
「現在?」我大吃一驚,「你到哪兒去?你看不見窗外的煙霧嗎?」
「就是因為看見了,才要回醫院一趟。」丈夫已經走到門前,然後又回頭,吻了我的面頰,「放心,我很快回來。」
這個戲劇化的舉動令我整夜無法安眠;自那個晚上開始我便難以入睡,而貓也開始生病了;貓的身體比人細小太多,一點點煙霧便足以致病。
我模仿余醫生的方法,用小匙給貓餵食;那比我想像中困難多了。一隻不願進食的動物比石頭還要頑固;才十分鐘我已唇乾舌躁。
「這是你愛吃的罐頭,」我盡量讓語氣聽起來平靜,「你先試試看,好嗎?」
貓別過臉去;鼻梁上的膿包晃動。貓大概感受到我並不真誠,我真實的浮躁與疑惑。
「你就吃吃看,好嗎?」
再過十五分鐘我放棄了。貓徑自走到床邊,躺在陽光照到的地方。窗外,有一棵正在緩慢地枯萎的樹;我看著它的葉子變成黃色,變得乾躁脆弱,如雪紛飛落下。
如果煙霧沒有出現,樹,和貓的生命會長一點嗎?我無法想下去,因為我的丈夫說過:「假設性的問題於現實無益。」
警車的笛聲在窗外響起,又匆匆遠去;腹中的胎兒翻動,像一隻小手一拳搥中我的胃。我衝進洗手間,卻吐不出什麼。
再次踏進診症室時,我坦白跟余醫生說:這個星期貓不願用小匙進食,我只能用針筒灌,確保牠有基本的能量。
「請不要怪責自己。」余醫生點點頭,「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貓的錯。」
眼淚毫無預警地紛紛落下,如同窗前的樹葉。余醫生沒有看我。他把工作枱上的毛巾拿走,換上一塊厚毯。
「天氣開始變涼了,要注意保暖。」余醫生搓揉自己的雙手,然後把貓抱出來。
「像之前一樣,檢查需要一點時間,請你在椅子上休息吧。」
椅子是上星期的椅子,上面多了一個靠背的墊,上面繡著太陽花的圖案,有點俗氣,卻熟悉。我坐下來,把腰陷進靠背中,看著貓。每星期一次,我能從旁觀者的位置,看著別人懷抱中的我的貓;牠的鼻子與今早又不同了,但至少看起來沒有我想像中的痛苦。
「體重是輕了一點點。體重變化的因素很多,數字只是參考,貓的整體狀態最重要。你覺得牠這個星期過得怎樣呢?」
「我……」我努力地回想,「大致平穩吧。有時牠寧願吃超級市場買來的便宜貓糧。我只好由得牠。」
「這是對的。治病本是希望病癒後可以享受生命。如果治療的過程太痛苦,那就本末倒置了。」
我點點頭。其實我不太能聽清楚余醫生的話。心不在焉。
「那麼,你呢?」余醫生忽然問,「你這個星期也過得好嗎?」
「我……」我想不出該如何回答,也想不出該如何拒絕回答。余醫生是可信的;只是我自己不想過於唐突。
「如果你想的話,可以脫下口罩,這樣呼吸會暢順些。」
「謝謝。我昨晚跟貓一樣,吃了罐頭。」我按照余醫生的建議,脫下口罩,交出笑容。事實上我沒胃口。
「能吃就好,身體會主動告訴你,它需要什麼。」
「不是說孕婦要有足夠營養嗎?懷孕的貓也得吃夠。」
「比起營養,懷孕的貓更需要安全感,所以臨盆時貓會找個牠認為安全的地方生產。」
「我不知道這個城市是否還安全,」我鼓起勇氣,「我也怕別人知道我吃不好睡不好。他們說,為了胎兒,我應該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照顧自己是應該的。」余醫生笑道,「不管你是否懷孕。想吃什麼便吃什麼吧,心情好比較重要。」
余醫生把貓抱起,撓牠的下巴。貓「咕嚕咕嚕」地叫,顯得很舒適。
我們沉默了一會;診症室的空調發出低鳴。
「其實……」我清一清喉嚨,「余醫生,你怎樣看最近發生的事呢?」
「我只是個動物醫生。」余醫生笑道。
「動物醫生也是醫生,人類不過是哺乳類動物而已。」
余醫生低頭,親了貓一下。貓聳一聳變形的鼻子,並不拒抗。
「上星期,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著一隻麻雀從半空的煙霧中掉下來。」余醫生的語氣像在講一個陳年笑話,「牠掉在行人路中心,就在我幾步前。我快步過去看看,見到牠還有微弱的呼吸,便捧上手,往牠的嘴巴裡吹氣,看看能否救活牠。 」
「結果呢?」
「結果牠在我手上斷氣了。」余醫生撫摸著貓的背,「我知道醫生不是上帝。但那一刻,我實在非常憤怒,非常難過。」
我看著余醫生的臉,想像他憤怒難過的樣子,不太成功。
「我……」我試著說,「在某個煙霧瀰漫的晚上,我的丈夫外出了,再也沒有回來。」
余醫生看著我。
「他跟你一樣,是醫生,不過他是人類的醫生……他說,他要返醫院。」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的煙霧。像深海。整個城市彷如陸沉。
「我不認識你的丈夫,不想評價他的決定。但我想,我明白他的心情。」
我不作聲。
「我想像不到你生氣難過的樣子。」我試著轉換話題。
余醫生莞爾。
「這是正常的。我在診所時是一個樣子,離開了診所是另一個樣子。」
「類似的話,我也聽丈夫說過。也許,我從沒了解過他。」
「『了解』。」余醫生重複這兩個字,像嘴裡含著甘欖,「你愛你的貓嗎?」
我對這個明知故問的問題感到一點愕然,「愛的。」
「那麼,你能了解牠的想法嗎?或者說,你能改變牠,讓牠吃你想牠吃的食物嗎?」
我無法回答。
「我知道,你很愛你的貓。」余醫生的手摸到貓的肚,「愛和了解有時沒有關係。」
我靜下來,讓余醫生專心地為貓作觸手檢查。貓在他的手下,總是很平靜。
「了解,是認知層面的事,屬於理性範圍。」余醫生忽然問,「你在這裡出世嗎?」
我想了一想,才明白「這裡」指的是「這個城市」。
「是的。」
「我也是。」余醫生的手移到貓的尾巴,「我沒想過有一天,這裡會變成這個樣子。也許,我從來沒有了解過自己的出生地。」
那個晚上,我看著窗外的夜色:蜿蜒的天橋像夜色中的河,橙紅色的車頭燈是河面上流動的燭光。只要不看新聞,不管世事,這個城市依然相當美麗。如果煙霧沒有出現,我和我的丈夫應該正在平靜地生活:上班、下班,期待孩子的出生,然後讓他上學、放學,直至他也上班、下班……而現在的我,正擔心孩子的將來,擔心貓、擔心丈夫的安危;我甚至在擔心這些擔心只是出於懷孕期的荷爾蒙分泌變異。事實上,人們知道我懷孕後,並不替我高興;他們先是停頓幾秒,然後遲疑地說:「恭喜你啊」,那聲調跟「有煙霧啊」是一樣的。
我連明天怎樣過也無法想像;假設性問題於現實無益。
貓的鏡像出現在玻璃上。牠蹲在我的旁邊,和我一樣,看著外面的風景。牠的畸形的鼻重疊在天橋後面的高樓上,像是明信片裡的、背景上的高山。
「我跟貓一起看夜景,看了十五分鐘。然後,我嘗試給牠餵食。」
「順利嗎?」
「不,」我重重地嘆了口氣,「牠不吃。」
這時,貓正在余醫生手裡的小匙上,小口地喝營養液。
「為什麼會失敗呢?」我又問,等候余醫生提出一個可行的方案。余醫生望著貓,微笑著。
我等了好一會──大約五分鐘。貓終於喝完了,別過頭去,然後用爪抹面。
「為什麼會失敗呢?」余醫生看著我,「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我對於這個答案並不滿意,然而也想不出該如何回應。
「你上次說,愛不等於了解。」我嘗試掙扎,「我曾經以為我對愛很熟悉。我每天餵貓,給牠梳毛。我每天打點丈夫上班的衣服,煮飯時考慮營養均衡與顏色配搭。」
「你做得很好。」
「可是一切並不如我所願。貓寧願餓死都不理我。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飼主。」
話才出口我便知道自己非常唐突。余醫生只是個獸醫,不是心理輔導員。我為自己的失態流下羞恥的眼淚。
「謝謝你把感覺告訴我。」余醫生把枱面的紙巾遞給我,「正如我上次所說,飼主的心情對貓的健康有直接的影響。你能宣洩情緒,對你,對貓都是好的。」
我想哭,但不太能哭出聲音,只好擤擤鼻子。
「貓在你這裡,好像比在家還適應。」我勉強笑道。
「放心,我不會搶走你的貓。」余醫生用浸過暖水的小毛巾替貓抹臉,「養貓,是最傻的。貓不會感恩,不會給你尊重,不會陪你玩。貓甚至不愛你。」
我一時分不清余醫生說笑還是認真。
「我是認真的。」他彷彿知道我在想什麼,「動物醫生也是醫生,同樣要接受嚴格的訓練。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理性、程序與規條。不但是診症的時候,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對於醫生來說,愛的體現就是秩序與判斷。」
我考慮了一會。
「這樣說很冒昩,但,你讓我想起我的丈夫。」我把話說開。
「說來聽聽。」余醫生對我的比喻似乎並不意外。
「我丈夫一家都是醫生。從小,丈夫的父親便嚴格訓練他的孩子。例如,明知求求熟人便可以讓兒子進入心儀的教會學校,他仍堅持要孩子們靠實力考進去。」
「嗯。」
「我的丈夫從小學開始便被安排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小提琴、英語會話、畫畫……到現在,丈夫的母親仍在抱怨:你這個父親做得太心狠了,你是醫生,病人都感激你,你有的是各種門路。丈夫的父親先是『哼』一聲,然後勉為其難地解釋:做人不能隨便破壞規矩,也不能隨便欠下人情。」
「嗯。」
「所以……我丈夫也是個守規矩的人。他跟後輩訓話時,語氣跟他父親一模一樣。」
「那麼,」余醫生點點頭,「你喜歡這種生活態度嗎?」
「不喜歡,」我很快回答,「但我羨慕。」
「為什麼羨慕?」
「我從未見過我丈夫失眠。剛結婚的時候,我曾問他為何能夠隨時入睡。他說,醫生必須保持頭腦清醒,而讓頭腦清醒的最佳方式就是充足的睡眠。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睡眠與痛症的關係』。」
「聽起來很厲害。」
我聳聳肩。
「因此,對於那些無法入睡的病人,我的丈夫總是寄予同情,毫不吝嗇地給予安眠藥。交往的初期,我們的話題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睡眠質素。」
余醫生哈哈大笑起來。
「如何早睡早起、少夢、REM保持良好的節奏;專注集中,少胡思亂想,」我忽然笑了,『睡不安穩的人很難產生正面情緒,也沒能力面對生活上各種難題』,我的丈夫說。」
「我也同意啊。」余醫生點點頭,「你呢?」
「那時我不過是個戀愛中的女子,我當然聽他的。」
「哈。」
我們安靜了一會。
「直至煙霧出現之前,我都以為我非常了解我的丈夫,而且愛他。」我又聳聳肩,「就像對我的貓那樣。」
離開診所的時候,我帶著貓,到附近的商場買了一袋二袋的嬰兒用品,然後跳上的士。然而車子駛到十字路口便無法前進。前前後後俱是停下來的小巴、巴士、私家車,連電單車也無法駛過去。
「前面封路了。」司機說,「有煙霧。」
「噢。」
我們又默然地等了十分鐘。車廂外,巴士乘客開始魚貫下車,走上行人路;漸漸地又溢出馬路面。
「你要下車嗎?」司機看著倒後鏡內的我。
我挽著手抽袋下車,橫過幾輛車的前後,擠上行人路,跟著黑色的人群走。這裡是市中心,街道在平時熟悉不過;前面是百貨公司與銀行總行交界的十字路口,那裡有地鐵站。然而,當我們走到那裡時卻無法前行。
我們處身煙霧封鎖區的外圍。
十字路口平時往來各式車輛;現在,這裡變成無人的空地。部分人留下來,我跟著其他人往右轉,漫無目的。我一邊走一邊回頭,忽然想起結婚之前我和丈夫約會時到郊外野餐的情景:我們在大公園的的草地上吃蘋果、奔跑,看著草如何被風壓低。當時的世界是那樣的遼闊、青葱、蒼茫,如同眼前這片空地。
「小姐。」
我轉過頭來。
「你的臉色不太好,需要幫忙嗎?」
對方是個年輕人,戴上黑色棒球帽,黑色口罩。很高,很瘦,我抬起頭才看到他的眼睛。
我拎著貓籠的右手有點痠,只好換到左手,「我聞到煙霧的氣味。」
「是的,你最好快點離開。」
「我會的。」為了貓,我必須盡快回家,「你呢?你一個人嗎?」
「我沒事。我留在這裡,看看有什麼能幫忙。」
「但……」我咳嗽起來,不由自主地被人群推向前;最後一次回頭,我看見黑色的棒球帽消失在煙霧中。
那個晚上我安全回家,沒有頭暈眼花也沒有流血受傷。我甚至為自己做了簡單的晚餐;等到在餐桌旁邊坐下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根本沒胃口。電視新聞報道,煙霧來過我們下午路經的路口,又離開了路口:就像我跟年輕人的對話,如同幻覺。
我關掉電視,把沒吃過的飯菜放進冰箱裡,然後洗碗。冷水從水龍頭裡流出,沖在洗碗海綿上,撞出一堆泡泡,透明而綿密,從手心中湧出來,彷彿廚房裡有個製造夢想的神仙。人工的芳香散溢;據洗潔精上的說明,那是薰衣草的香氣,和我日間在嬰兒用品店所聞到的氣味一模一樣;只是,那幾袋嬰兒衣物,只怕已沾上了煙霧。
一陣嘔心的感覺湧上來。我把手浸在滿盤的洗碗水中,試著讓冰冷的水讓自己冷靜些。然而我終於大哭起來。
「這個星期,有好些嗎?」余醫生問,「貓有吃些什麼嗎?」
「好些。」我苦笑,「三餐裡有一餐願吃我餵的東西。」
「這不是很好嗎?」余醫生的語氣像在鼓勵小學生,「那麼,你自己呢?胃口好些嗎?」
「嗯……似乎好些吧。」
「那太好了。」余醫生滿意地點點頭,「希望你是為了自己而吃,而不是為了你的貓,或你的孩子。」
「有什麼分別嗎?」
「為自己而吃,味道會好些。」
我笑了。余醫生也笑了,然後替貓量體重。
「跟上星期一樣。能維持原狀,很不容易呢。」
貓好像聽懂醫生的話,瞇起眼睛,看著他。貓的眼睛本來已被腫瘤擠壓,變得很小。
「貓的髖關節比上一次硬。」余醫生摸到貓的大腿,「我們來按摩吧。」
「按摩?」我問。
「貓吃的藥已經夠多了。我的看法是,餵藥的過程令貓和飼主感到壓力;能用別的方法,彼此都會輕鬆些。」
我沒見過獸醫為動物按摩。對於新事物,我的適應能力不高,只好保持沉默。余醫生慢慢地轉動貓的四肢,先是前腳,然後是後腳。到了右面的後腳,貓明顯地抗拒,大聲叫起來。
「應該是這隻腳感到痛楚。你在家裡有見到貓走動的情況嗎?」
我努力地想,卻想不起來。為什麼呢?我不是整天留在家裡嗎?我明明哪兒也沒有去,也無法去。
「久病的動物少動,關節不適是常見的,你不必怪責自己。」余醫生抬起頭,看著我,「你過來,試試看。」
「我?」
「是的。」余醫生依然看著我,「你才是貓的家人。」
我把手放在貓的右邊後腿上。
「試試轉動貓的大腿關節,幅度小一點。」
「會弄痛牠嗎?」
「可能。這需要你和貓逐步協調。」
我吸一口氣,摸到貓大腿與軀幹連接的位置,慢慢地旋動;才一下,貓便痛苦地「喵」了一下。我連忙縮手。
「我有點怕。」我坦白說。
「面對恐懼是需要學習的。現在,把自己的手心搓熱,按在貓感到痛苦的地方。」
我把雙手放在胸前,用力地上下搓揉。
「這樣,可以了嗎?」我問。
余醫生伸出手,拉著我的手腕,輕輕地,把我的手放在貓的大腿上。他的手很溫暖。我感受到貓的動脈在跳動,一下,一下。
「你能感覺手心的溫暖嗎?」
「能。」我答,「我也感受到貓的疼……牠說,骨頭的部分,很冷。」
「保持平穩的呼吸。」余醫生收回他的手,「貓會感受到你的節奏與脈搏。你能平靜,貓也就能克服痛苦。」
我在貓的身體上輕輕地揉動;我心裡想著:別怕,我們愛你。
這樣想的時候,我確實感到心裡的虛怯,然而我清楚知道,我沒有說謊。
離開診所的時候,我忽然覺得,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余醫生了。到了下星期,可能是貓已經不在了,也可能是余醫生離開了,他已經把他所懂得的,全部告訴我。街上的人仍然戴著口罩,匆匆地掠過我的身旁;他們的影子投影在商店的櫥窗上,矇矓而真實。
到家的時候,我把籠子打開,讓貓出來。那輕快的步伐讓我想起之前牠的確有點腳步闌珊。現在,牠像剛來到我家時的樣子,沿著玄關的走廊一直走,走到客廳上的沙發,敏捷地跳上去。
沙發上躺著我的丈夫。
丈夫睡著了,鼻鼾如雷,大概是累了。他看起來瘦了些,頭髮長了些,下巴的鬚渣讓他的臉看起來憔悴。
我站在原地,想叫醒他,想說些什麼,卻什麼也說不出來。貓跳上丈夫的胸口,轉了一圈,把自己圍起來,然後安穩睡去;牠的腫瘤歪向丈夫的鎖骨,像找到了一個被安置的地方。
我摘下口罩,坐在餐椅上,看著沉睡的他們。胎兒翻動了羊水;窗外,煙霧正緩慢地、濃密地,帶著它的祕密與詛咒,吞噬了整個城市的天空。
〈灰飛湮滅〉
在我丈夫失踪的時候,我的貓病了。
我的貓病了,鼻子長出了腫瘤,柔軟而岩巉;膿水隨著呼吸流動,使貓的鼻梁不時變形,貓的樣子也因此變得陌生。那是怎樣的一回事?那似乎是同一個靈魂被丟進不同的軀殼中;又或者,每次打開門,都發現自己置身於不同的房間裡……貓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的變異;牠依舊盡最大的努力生活,進食、上廁所、睡覺。然而和貓一起活在的這個城市的我,卻確實地感受到這種難測的詭異的變化。
我的貓病了的時候,我剛好懷孕了,而我的丈夫失踪了。於是我獨自帶貓去看醫生。我把牠放進寵物用的手提籠子裡,...
目錄
track 01春夏秋冬
track 02灰飛煙滅
track 03無心睡眠
track 04金枝玉葉
track 05怪你過分美麗
track 06無需要太多
track 07大熱
track 08潔身自愛
track 09不想擁抱我的
track 10路過蜻蜓
track 11紅蝴蝶
track 12熱辣辣
track 13春光乍洩
bonus track後記:這些年來
track 01春夏秋冬
track 02灰飛煙滅
track 03無心睡眠
track 04金枝玉葉
track 05怪你過分美麗
track 06無需要太多
track 07大熱
track 08潔身自愛
track 09不想擁抱我的
track 10路過蜻蜓
track 11紅蝴蝶
track 12熱辣辣
track 13春光乍洩
bonus track後記:這些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