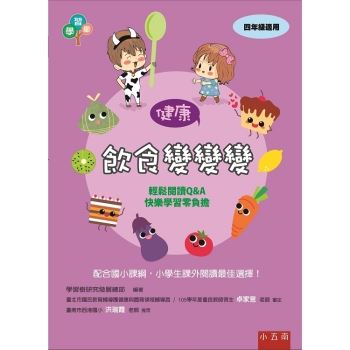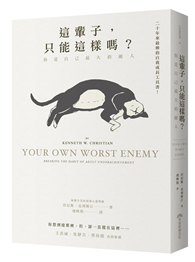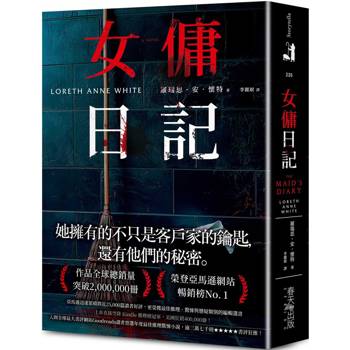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菊花如何夜行軍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散文 |
$ 332 |
現代散文 |
$ 332 |
Books |
$ 332 |
Books |
$ 332 |
歷年誠品選書 |
$ 332 |
散文雜論 |
$ 378 |
現代散文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九八○年代中,我受三件事嚴重衝擊,跟彗星撞地球一樣,得耗上長長歲月,氣候生態方可再平衡。首先是我家南邊兩公里的山丘──獅形頂腳下出現奇景:一畦畦菊花頂著一排排日光燈管,夜夜通明。難道現在連作物都不得日落而息了嗎?我心中感到哀憐且不祥,隱約覺得某種異變正在蔓延,但又不明何以。每回傍晚經過,我不安地遠視山腳下那一片詭譎的光明,彷彿是一群藏著祕密動機的無聲軍隊在夜裡行軍……──鍾永豐
交工樂隊與生祥樂隊作詞人鍾永豐,在臺灣首本散文集錦。一位投入社會運動的農村子弟,由音樂蔓生出對土地的關懷,在政治路上不離農、不離土,唱自己的歌。
本書從鍾永豐的「我庄」──高雄美濃龍肚庄起始,呈現兒時那商業不發達、人際關係卻繁複綿延的客家庄,無論是拿橡皮筋當籌碼的頑皮小鬼永榮哥、賣豬內臟賺大錢的添富、地方黑道老大阿欽、移民南美洲又返鄉的貢祥哥……,都與美濃土地有著緊密的羈絆。而在村人的故事裡,也嗅出農村變化的端倪,鋪上紅毛泥的院子、蚯蚓沒辦法鑽地的水泥地、柏油水蛭般開進村裡的縣道一八四,還有「把人從土地上解開」、「把人從農地上支開」的各種農業擠壓政策,都預示著農村的轉變。
青春期的的鍾永豐,透過崇尚「阿美仔」的二叔開始接觸西方民謠、搖滾,這對於農村來說過於「新潮」,對於農村小孩來說卻是令人著迷的豐富世界。作者像是騎著野狼一二五,踏上狂飆的青春,從Bob Dylan、Leonard Cohen、Woody Guthrie等席捲全球的音樂人,認識動盪的世界局勢,以及音樂所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鍾永豐與樂隊朋友,澆灌土地的歌,投下「文化原子彈」。一邊唱歌、一邊運動,將「以農養工」政策下,劇烈變化、扭曲的農村──夜晚開日光燈養菊花的歪曲景象,透過歌曲表露無遺;也將北上抗議反水庫的末代老農,在立法院前唱山歌的堅毅神情,用他生猛有力的文字記錄下來。
循著鍾永豐的散文,我們彷彿聆聽一曲又一曲農村變遷民謠。一位農村出身的青年,走向反抗者、創作者、政治工作,仍掛心鄉土,這是一本引領讀者反思土地、自我與全球化的散文集。
【封面設計說明】
一隻鯨魚的死亡,不是終點,而是滋生。牠的屍體緩緩落下,沉至海底,在這緩慢的──「鯨落」過程中,形成孕育其他生命的生態系統。牠的滋養可長達百年,如同一場文化運動起滅的尺度。
由夜行軍的菊花所勾勒出的鯨魚,逐漸沉落,也綻放新生,好似作者描繪的臺灣農民與農村風貌,隨著農業擠壓而消逝,卻仍是這塊土地厚實的底蘊,指引人們一條穿越深海迷途的航道。
美術設計:萬向欣
作者簡介
鍾永豐
出生於美濃菸農家族,為詩人、作詞人、音樂製作人及文化工作者。曾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高雄縣水利局長、嘉義縣文化局長、臺北市客委會主委及臺北市文化局長,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主祕。曾獲二○○○年金曲獎最佳製作人獎,二○○五、○七年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二○一四年入圍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二○一七年以《圍庄》專輯獲金音獎及金曲獎評審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