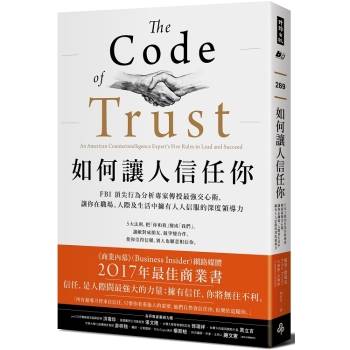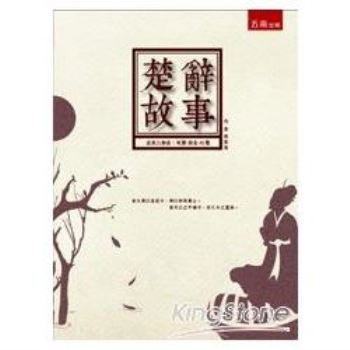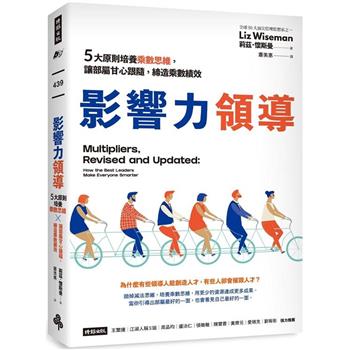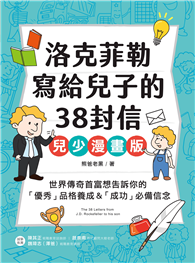推薦序一
Metameric
蕭詒徽(寫作者∕編輯)
人類是三色視覺動物。意思是,我們擁有三種類型的視錐細胞,分別感應藍、綠、紅色,並藉此感知由它們所構成的一切顏色。
所以,紅綠色盲矯正眼鏡的原理是這樣的:鏡片濾除紅綠色光譜之間一部分重疊的波段,讓射進眼睛裡的紅綠色光對比加劇,使色盲患者的紅綠視錐細胞得以因為程度更大的差異來分辨兩者。
上述說明並非為了與書中的一篇〈色盲〉呼應,而是為了展示我們有多麽容易落入一種多數決的敍事之中──為什麼是「色盲矯正眼鏡」? 因為多數人可以分辨紅綠,所以不能者需要矯正;再往上一點,為什麼「人類是三色視覺動物」?因為多數人的三種視錐細胞都能有所區別地自然運作。以多數人的自然運作代言全人類,這是概念建立時的盲點,一種溝通上的權宜之計,其實無可厚非。
我知道多數人,包括我,閱讀前兩段時並不會思及這種敍事的危險,遑論在意。然而,子齊恰恰是會的那種人。無論思及,或者在意。
不幸的是世界將永遠分為多數與少數。而身為多數人的特權,是可以隨時而從容地動用統計數字上所謂「常態」來輔佐關於自身的敍事。這份從容,多數時候來自於一種「不知」──並不是無知,而是「不需要知道,所以不知道」的,占盡優勢的天眞──我以此理解《還不是我的時代》這個書名,它與「我」已經多麽成熟、多麽懂得無關,而是指在此刻「我」與「我的同類」都仍是少數。
誰是「我」的同類? 如果必須分類,這部作品無疑是同志文學。但我特別喜歡子齊將看似與性傾向處境無關的職場書寫放在全書輯一。看似無關,其實作為新聞工作者時他關注被報導者中的少數、同時對媒體「必須」取用所謂「多數人的語境」來進行「溝通」的這份質疑,其透露的敍事者性格已經幽微地暗示輯一之後的同志書寫,並成功地在此之上,建立了一個十分帶有個人特徵的作者形象:一個不太擅長「辨識」,或者說,對自身的辨識能力感到沒有自信的人。
無論是不是眞的色盲,子齊常常懷疑自己是色盲。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有些人會想像同志身上帶有敏銳發現同類的感知能力,彷彿其他人才是色盲而他們擁有眼鏡;《還不是我的時代》裡的敍事者卻永遠處在辨識結果將明未明的邊界。於是,在摸索性格建立歷程的輯二「靑春的死法」與瞄準性向處境的輯三「愛如此孤獨」,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敍事者將某個對象誤認為同類、並在發現結果錯誤之後對自己的一廂情願感到悵然與厭棄,並繼續維持沉默。這與以往被普遍描述的「異男忘」有所不同──常見的異男忘敍事裡,同志是對整體情況相對全知的一方,早已知道對方是異男,知道自己抒情的悲劇性建立在明知不能而行之的眞摯之上。但在《還不是我的時代》裡,敍事者卻完全沒有這種全知,他並不知道對方「是不是」,但在明確知道以前就預設對方是、並因此投注感情。
理解這點後回頭來看輯一「還不是我的時代」,身為寫作者與編輯的我便會讚歎其編排:子齊在職場中的「辨之難」,原來建構於自己的同志成長經驗;而在順序上將果之職場書寫放在因之同志書寫之前,讓作者自身對分辨的遲疑,擴張成讀者分辨這部作品的延遲。這種逆向發現的過程,構成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同時也讓這本書成為對讀者的試紙:你是看得懂的這一邊,還是看不懂的那一邊?
部分看似流水帳的篇章,一旦戴上眼鏡,就忽然看懂玄機。這樣的趣味不只在情節上,也在筆法上──你會在字裡行間忽然遇見老老實實地打出來,遇見是電是光是唯一的神話,甚至遇見「我深知板塊/卻迷信雨」──看得懂就看得懂,不懂就不,我只能說公關書應該要寄一本給炎P,只可惜美江已經先走。
相對於散體,書中收錄的詩作比較敢於抒情,或許因為作者覺得詩本身的隱晦保護著自己,也可能因為知道詩不太會被讀者當成「正解」,而得以拋下對斷言的猶豫。順序愈後面的詩作程度愈好,我傾向認為這是子齊與編輯的有意編排,讓讀者能從生澀到純熟走一趟,也像是跟著作者自己一路的學習軌跡。
最後一輯「親愛的狐狸」的體裁與筆法,甚至一部分以軍營為背景的描述,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同樣出身自雄中的學長林達陽的作品《慢情書》。但放在上述的脈絡下閱讀,讀到全輯最後一篇提及離別,你會知道這份離別的意義非常不同:同樣是失去重要他人,但多數人的離別,是處於可以明確知道潛在的下一個重要他人的群體在哪裡、範圍在哪裡的狀態。但對辨識困難的子齊來說,離別意味的是拋廢了一次好不容易成功確定的辨識。
下一個他能夠辨識的人在哪裡? 他無法確定。一切都要重來,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他不只是和這個人分開,他是再次回到了色盲的狀態──容我又用這樣危險的說法比喻。
其實,如果和其他動物相比,全人類本就都是色盲。就算是健康的、分辨三色的眼睛,人們依然無法分辨同色異譜色(metamers)──構成光譜不同、但在人眼看來卻相同的顏色──我們無法分辨由紅光與綠光疊合的黃、和本來就是黃色的光之間的區別。上述說明,並非為了首尾對稱,而是為了展示這本書亦不只是只有同類才能讀得啟發的作品,而是所有人──所有嘗試捉摸自己與他人的尺度卻時常磕碰、雷達失準、辨色困難之人──《還不是我的時代》屬於這樣的人,而它並未試圖矯正你,只是認出了你。
推薦序二
已經是你的時代
羅毓嘉(詩人)
這是子齊的靑春之書──初出社會沒幾年的時間,正在經歷現實與理想的洗禮,信念依然熾熱,可因為碰觸到的現實世界如此赤裸而不堪,他自問「這還不是我的時代」。當然,我們都曾經這麼想,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都是「他們」的。都是「那些大人的」。我們被認為對現實運作一無所知,我們被貼上「天眞」的標籤。
像子齊的自況:「寬鬆世代,八年級生,九○後,社會給予我們的統稱。」
然而九○後,八年級生,正當要邁入三十歲的年紀,依然滿腔熱血想要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卻發現很多時候,他們連自己都無法拯救。
沒關係的──我很想這樣對子齊說,我們也是。不管在哪個年紀,我們都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感到無能為力。卻也因為這樣的無能為力,我們擁有建造的力氣。我們摧毀舊的,建立新的。修正應該毀棄的。而子齊這麼寫:「他們建造的時候,聽起來就像摧毀。」
當然。
子齊的記者之眼,文學之眼。使他對世界形成了獨特的觀點,那可以是批判的,「你想保護你的國家,可當你生病,國家要你離開。他們隔離你的餐具,在你無助的話語裡沾染惡意。你年輕,你愛你的國家,然後國家把你拋棄。」可以是抒情的,「就這樣向前開著,但來時的路樹,已經老了。我看得出來他們的姿態不再熱烈,沒有夾道歡迎,只在夜色中力盡所知的義務,無有認知繼續活著,把生存過成生活。」
這是我們寫作者全部的宿命嗎──我們總是在問著,「文學到底可以做什麼?」它只能是革命或社會運動號召的檄文嗎?是不是我們的能力還不足以透過文學去論辯,或思索社會主義。不足以讓我們在需要改變的時候推動任何的改變?
在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寫作者到底可以做什麼?
子齊有這樣的疑問。我也有。但我想對子齊說的是──我後來就接受了這件事,文學並沒有比較高尙,它只是一個媒介。如果有一部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偉大,必須是因為它所承載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痛苦。但反過來說如果要讓一部作品這麼偉大,也是因為它承載了這些苦痛。
像子齊寫的,「記者是這麼好的職業,你能夠提問,並且得到答案。」你的文學承擔了這些問題,並因此得以前進。
無論子齊希望或者不希望──這已經是他和他同代人的時代了。每一個我們都在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分子」,當「一分子」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希望有個救世主來幫你的生活做決定,領著一個還可以的薪水,發胖、睡覺跟上班。每天眼睛睜開就是上班,上完班想說累得跟狗一樣,就犒賞一下自己。
每天上班等下班,禮拜一等禮拜五,月初等月底的薪水,一年就過了,在這種物質無虞的地獄裡,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了。
你會甘於成為這樣的大人嗎?
我相信子齊不會──歷史沒有倘若,但是未來有。子齊想要改變自己的未來,讓時代成為他的時代,從這本書,他就已經開始了。
後記
一次又一次,掉進一樣的窟窿。忘懷不了的糗事,後知後覺的暗傷,每一次的痛苦沒有風化的跡象,反而在每一次回想之中,訓練出更敏銳的感知。關於悲憤,關於後悔。
時間並沒有用。回憶並非線性向前。人類學家獨自造訪孤島,發覺島上唯有一片樹林,且不依時序生長,紊亂圍困可能的去向,愈發濃烈的感受成為樹冠,遮蔽僅存的陽光。
是誰暗中煽動我推翻記憶的史觀,刺探每一回差錯,可能岔出的行蹤。有時我厭惡平行時空的說法:畫出不斷開枝散葉的路線,佐以圖庫裡每一次重大事件、乃至不重大事件的抉擇。煞有介事說著,每一次抉擇,都導向另一個世界。若眞是這樣,試問該如何計算選擇的次數?
曾經迷戀的電影結尾,準備搭上火車的男孩,已經在瞬間活過兩種可能,活過離去的,也活過留下的。最終他放任列車開動,奔向鐵道另一段,毫無邊際的荒原。可以放棄曾經握在手心的時間,奢侈在於已經活過兩種。因為過都過了,就能發出所有可以想及的抱怨,就可以放逐。
但那是因為活過了。我抄下那句詩,「可是我只有現在。」聲聲呼喚,在心裡喊到啞了,我卻在某天夢見那人歸來。這是美夢。但當他告訴我,我現在只要你了,我心的幕後告訴我,現正上演無間惡夢。
幸福得足以思索不幸,就是生活。一旦太過淸晰,太過氤氲,太過快樂,彷彿就會暗藏開始艱澀的笑話,崩潰這是不是眞的。前世今生我都不指望,亦不窺探。只要不揭露,就永遠是美麗新世界。
我得抵達那裡才行。這是我的行囊,複印、收折、劃去卻無法忘記,梳理毛邊過後的想望與失望,幾乎都在這裡。乾涸的火種、發潮的菸盒,不再雋永的至少都留下氣味。我用行走來等待,兜著圈子走在田野,或是迷惑的站前巷弄。背負活過的時間,兌成年歲,用現在超渡過去,卻不期盼未來。
凡存在的都消滅不了,只能與之共生。體內復辟之物,逐漸接受那是天生。說書之人掌握手法,不確定的事件可能,別太武斷,就說恐怕。恐怕還沒結束,恐怕才剛開始。恐怕不會輕易改變,恐怕沒有轉圜空間。
故事就這樣驚懼地結束了。其實不知要往哪裡去,並不眞的想動身。但隔天照常上班上課,塡充應有的靈魂,接受、對賭、或者反抗。你還有把空火柴盒拋向空中的力氣嗎?魯莽就在場上拋接。偶爾有人叫好。更多的蔑視你看不見。只記得靑睞,並為此又一次奮力做功。
冬天烈日下在草地打翻啤酒,誰也不浪費誰,誰也不欠。記得你曾為了追憶,弄濕一手,思忖該不該伸出舌頭去舔。你耳後的音樂廉價單薄,只有這過於華貴的汁液單一無二。你曾經這麼黏膩,這麼猶豫,像個愚人,有點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