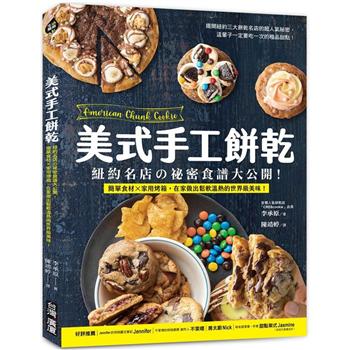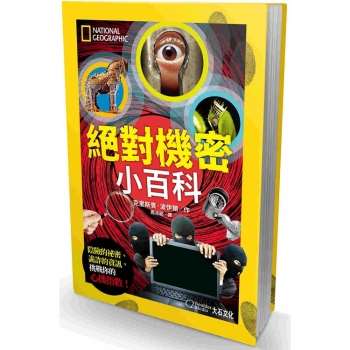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吉檀迦利》是泰戈爾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集,共103首。整部詩集,在情感與結構上都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是遭受現實困境的泰戈爾,借與"神"的對話,用充滿自然的意象,用極具韻律與音樂性的語言,融合古老印度精神傳統與現代西方精神,從自我中看到眾生和宇宙,傾訴了他的孤獨、掙紮、期望、愛和信仰等。
《吉檀迦利》熔哲理與抒情於一爐,具有深刻而稀有的靈性之美,是瞭解泰戈爾代表性的經典詩集。
本版本選用蕭興政的全新譯本,中英雙語,全錄美國藝術家馬克·麥金尼斯103幅精美插畫隨文彩插。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吉檀迦利的圖書 |
 |
吉檀迦利(中英對照精裝本;泰戈爾逝世八十週年,奠定其諾貝爾文學獎地位的詩之讚歌全新譯本) 作者: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 譯者:聞中 出版社:好人 出版日期:2022-02-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98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36 |
詩 |
$ 379 |
世界詩集 |
$ 379 |
Books |
$ 379 |
Books |
$ 408 |
小說/文學 |
$ 422 |
中文書 |
$ 43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吉檀迦利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泰戈爾(Rabin dranath Tagore)
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
印度詩人、文學家、哲學家,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他出身貴族,精通文學、音樂、繪畫等,從小濡染印度宗教經典。青年時留學西方,汲取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是一位具有宇宙意識的人道主義者。他的詩歌富有韻律美,充滿自然的意象,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氣息和哲思。1913年,泰戈爾因《吉檀迦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另有著名詩集《新月集》《飛鳥集》等。
泰戈爾的詩直接影響了中國20世紀的新詩運動以及葉芝、龐德等西方詩人。他一生寫了五十多部詩集,被尊為"詩聖",在世界文壇具有重要地位。
譯者簡介
蕭興政
中英雙語詩人,英文筆名X.Z.Shao,1964年生於福建省甯德市周寧縣。執教于廈門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主講"英文詩歌閱讀與創作"和"新聞英語聽力"等課程。多次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刊物EnglishToday上發表英文詩歌、散文和論文。
2004年,翻譯了《吉檀迦利》和《印度悲情曲》。2018年于臺灣出版中文詩集《幽谷迷思》。近期,翻譯完成紀伯倫的《先知》。
畫家簡介
馬克·麥金尼斯(Mark W. McGinnis)
美國藝術家、作家,生於1950年9月,在南達科他州亞伯丁北方州立大學擔任美術教授長達三十年。現住愛達荷州的博伊西。其藝術創作跨越多個領域,包括繪畫、雕塑、影像等;此外,他還以研究為導向,創作了對不同主題進行探索的作品,包括物種滅絕,印度和日本的文學,科學與哲學等。
2001年始,他圍繞《吉檀迦利》的103首詩創作了103幅精美畫作,榮獲盛讚。
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
印度詩人、文學家、哲學家,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他出身貴族,精通文學、音樂、繪畫等,從小濡染印度宗教經典。青年時留學西方,汲取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是一位具有宇宙意識的人道主義者。他的詩歌富有韻律美,充滿自然的意象,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氣息和哲思。1913年,泰戈爾因《吉檀迦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另有著名詩集《新月集》《飛鳥集》等。
泰戈爾的詩直接影響了中國20世紀的新詩運動以及葉芝、龐德等西方詩人。他一生寫了五十多部詩集,被尊為"詩聖",在世界文壇具有重要地位。
譯者簡介
蕭興政
中英雙語詩人,英文筆名X.Z.Shao,1964年生於福建省甯德市周寧縣。執教于廈門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主講"英文詩歌閱讀與創作"和"新聞英語聽力"等課程。多次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刊物EnglishToday上發表英文詩歌、散文和論文。
2004年,翻譯了《吉檀迦利》和《印度悲情曲》。2018年于臺灣出版中文詩集《幽谷迷思》。近期,翻譯完成紀伯倫的《先知》。
畫家簡介
馬克·麥金尼斯(Mark W. McGinnis)
美國藝術家、作家,生於1950年9月,在南達科他州亞伯丁北方州立大學擔任美術教授長達三十年。現住愛達荷州的博伊西。其藝術創作跨越多個領域,包括繪畫、雕塑、影像等;此外,他還以研究為導向,創作了對不同主題進行探索的作品,包括物種滅絕,印度和日本的文學,科學與哲學等。
2001年始,他圍繞《吉檀迦利》的103首詩創作了103幅精美畫作,榮獲盛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