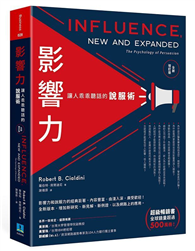序
藏在句讀裡的如歌行板──秀實《幽暗之地:止微室談詩》序言
姜豐
讀秀實詩文,時而會有台灣詩人瘂弦詩歌〈如歌的行板〉感覺:「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秀實的內心大概還是有一個溫柔敦厚詩教下的自我,詩思所及,無所不包,然而又總點到即止,使人回味,如歌的、行板一樣的,輕輕揭開欲表達之物,又輕輕放下。
一口氣讀完他的最新評論集,想洋洋灑灑寫下剖析他一生為詩、行止的宏文,腦中浮現的卻是他評詩人林鴻年〈法中有我,詩以載道〉的文字:「我祖籍番禺,每次回省城,得與鴻年相聚,均以詩佐酒,浮一大白,而不知地老天荒……於鴻年而言,詩當是解酒之藥,他獨醒於混濁之詩壇,我倆互惜互重,乃為文以記。」這段話是評論林鴻年的〈詩歌,我的前世〉,該詩中有句:「我的今生/常自詡是位清流另類之人/隱於市 隱於朝/不見詩人/不談詩。」秀實大概是很想發揮一番的,最後也只是談到了與詩人的交情,詩的「解酒之藥」功效。或者如筆者插言,詩歌也像昊天中的微塵,藉著雨水而幻成扶搖天地的彩虹,藉著地形又變為滋育萬有的大塊,「其情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經》)。秀實大概也會服膺詩歌的求真氣質之重要,詩歌的求真意志是流淌在文化血脈中的,完全逾越體裁、風格、國族、性別等等的束縛;只是「真」,然而不足為人道,是善於隱遁的自然,是一個就算去反覆揭示也依然隱遁的祕密,於是又是美的──一種貫穿人類精神史的美感。秀實的詩文,讀之亦是這樣地美的,時而有舉重若輕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飲酒‧其五〉)。他既然自己在詩文中都不怎麼深入及點明,為什麼別人要看到和說出呢?秀實自己的詩文世界都是清雅的,帶著隱密高貴意念的書寫,也如林鴻年詩中所敘,是一位「清流另類之人」吧!
然而我還是開始寫秀實這本評論集的序言了。一開始就對他戲言:「這不就是評論的評論嗎?」然後隨手一番評論集,翻到也是他評林鴻年詩風中「清愁」時候所引用北宋楊萬里〈紅葉〉:「詩人滿腹著清愁,吐作千詩未肯休。」秀實也有他的「清愁」,那與千古而下的楊萬里又如何相通的呢?筆者的加入又有沒有清愁呢?這無盡祕密的談話是共生於一個心靈烏托邦的存在的。話語、語言、詩共生的世界,若是非要「一言以蔽之」,大概是他在〈我的理想國〉一文中提到的:「河流穿越兩岸有樹葉小如點子枝丫瘦削的樹木,我立著,樹游走。」長長的句子,配以兩個初讀違反直覺的短句,而依然有一氣呵成之感。此文是他的夫子自道,自然不必筆者再贅言;想補充的是他的詩學理念,如他在〈隱藏與悖論─談語凡詩〈父親與查無此人〉〉中的一段話:
詩題〈父親與查無此人〉這個題目充滿悖論(paradox)。美國新批評家克利安思.布魯克斯說:「科學家的真理要求其語言清除悖論的一切痕跡,詩人要表達的只能用悖論的語言。」語凡深明為詩之道,則以〈父親與查無此人〉為題。「父親」是個有溫度的詞,標示了血緣與脈絡,帶有強烈感情的色彩。而「查無此人」則是冷酷的片語,指向斷絕與失望。向一個至親的人喊「查無此人」,自是心懷悲愴。而此人於此,僅僅成了一個無宗族姓氏的符號。「查」字表示此人確實存在,只因線索斷落或與自己關係疏離,以致在生命中,恍若不曾存在過。而這種父子疏離的現實,與動亂的時代息息相關。
筆者不禁聯想到禪宗名詩:「蘭那行自周,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留。」(宋釋印肅《金剛隨機無盡頌‧一相無相分第九》)悖逆詩語不僅可以是秀實那樣的美文體句子,也可以用來剖讀詩友的詩文,甚至可以如這首禪詩講解存在感的基本經驗。而這所有的經驗(里爾克說「詩是經驗」)又藏在哪裡呢?那應該是藏在一個個漫長句子的句讀、換氣、沉思的靈韻當中吧!
而如果沒有或者消解了悖論詩語呢?秀實常在詩友前自詡:「我是一個知道自己為什麼寫詩的人。」筆者想,他更多非悖論的詩語表達的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世界將在獨有的述說中誕生」(〈黛色一生中的四月〉),也就是「詩歌的藝術在語言的述說」(同上)。秀實由此重塑和再造了一個與現實平行的詩語世界,他安居於中,一個詞與物與他者獲得某種微妙、銷魂同一的藝術世界,這也就是他的寫詩重要緣由了吧!
比較起秀實為了曲終奏雅而說的「理想國」,大概「異托邦」更符合他對自身詩文、詩人生活狀態的總體看法,譬如他在〈語言之外的孤單─蘇榮超詩集《奶與茶的一次偶遇》裡的疾病詩〉中談的:「香港詩歌大略而言,均欠缺來自土地的『熱度』。過客視香港為橋樑,掘金者視香港為礦山。兩者均把這個城市看作『暫留地』,這是一個時代的現象。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異鄉,所有的故鄉都杳無人跡』。或者,這正正是香港詩人的處境。」拈看此語,倒也可以看出秀實對自己身為香港詩人的身分認同之反思,似乎在呼喚一種詩友同道的認同與寂寞籲告。評論集中更有秀實藉著論詩友席地時談論詩之為「理解」橋樑之功用,大致來講是把詩歌當成津梁處渡人之舟,只要讀者沒有「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就可以把此一玩,找到心靈幽祕之地的共震、心底隱密火焰的共續。此「異托邦」自有風物萬千,可以流浪異域、久歷繁華,再回首,看到先將來時的當下世界不同的風景。
年來秀實又作起小說,讀他的〈敘事之必要──文榕散文詩略議〉、〈語言與隱喻─讀陳德錦詩集《疑問》中的幾篇作品〉,可見他對這兩位作者的熟悉和細讀文本的剖白入微;除卻我讀他倆作品的感受,只看秀實,我卻更多是分別感到秀實秉有的話語、語言本體經驗的深入,詩語的感通、澄明的純藝術傾向。讀者細讀這兩篇評論,當可看出詩人感知方式轉小說家、轉戲劇性敘述的趣致,此不贅言。
評論集中也有序詩人招小波詩集《提燈──我寫清流詩人100家》的〈幽暗之地,提燈之人〉,筆者這裡再評說,便是「評論的評論」的評論了,話語場化為詩語流水般,滾滾而來,不擇地而流,詩的汪洋大海於焉而成。而這「評論的評論」的評論想提到的,是其中議及的詩歌的「毒」,好詩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等天空下刀子的時候,我們就有用不完的鐵了」等金句。好詩往往擺脫了作者,孤懸於虛空當中,等待有緣人看到它的意旨、價值。同為評論中人,我也要仿效秀實那樣更多看到詩語觸及的世界奧義,然後回到祕密的沉默當中吧!但是,「評論的評論的評論」實在還是需要的,是這樣的吧?至少它加入了秀實與眾多詩人合奏的聲部,幽暗、隱密、深入又宏大,構成一闕藏在句讀裡的如歌行板。
這本評論集中還有許多涉及到秀實思考詩歌、散文詩文體界線及創作發揮的動力機制等的議題,間中提到他對他的個體詩學「婕體詩」的發揮,可以看到他用「婕體詩」寫作、論詩的進境,識者自取。至於他是怎樣做的?趕緊翻開這本評論集吧!集中開頭幾個評論都首要涉及這些議題。
(2022年4月28日於香港)
(姜豐,新港派作家。香港創意寫作研究生畢業,作家、詩人、詩歌和藝術評論者、拉康派非執業心理諮詢師。著有《遠去的浪漫派的夕陽》、《極速心城》等。做過數十位著名詩人和藝術家的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