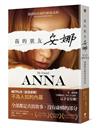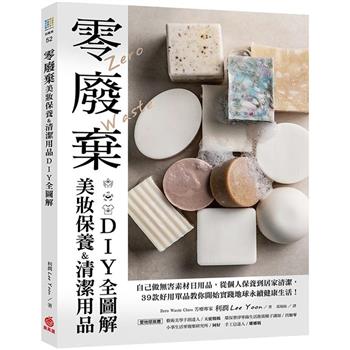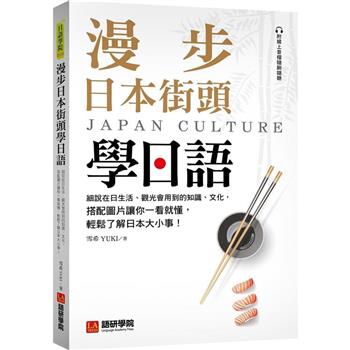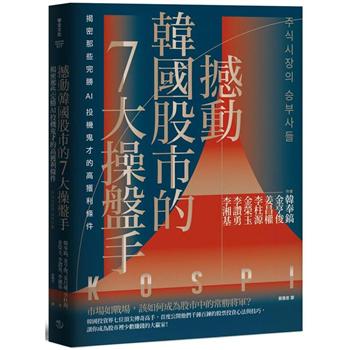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渴望更像安娜。
══ NETFLIX《創造安娜》不為人知的內幕 ══
※ 全部都是真實故事,沒有虛構的部分
★ 《時代雜誌》年度百大好書
★ 《紐約時報》暢銷書、亞馬遜第一暢銷書
★ 第一手揭密!安娜.德爾維(Anna Delvey)驚動全球的大騙局
▊ 真人真事,《慾望城市》、《惡血》加上《神鬼交鋒》
安娜是25歲的德國富家女,剛來到紐約,自稱有6,000萬歐元的信託基金,目標是創立價值4,000萬美元的藝術基金會。她全身精品、長住五星級酒店、天天吃米其林餐廳,甚至搭私人包機,周旋在政商名流之間。然而,就連安娜最親近的人也猜不到,她竟然是個身無分文的騙子……。
「從一開始,安娜就有一種獨特的氣場,一種神祕且難以捉摸的特質。我是在朋友的聚會上遇見她的。就是這個夜晚,遮蔽了我看清騙局的機會。」──《我的朋友安娜》
▊ 揭發「安娜騙局」的第一人告訴你:這才是安娜!
本書作者瑞秋曾是安娜最親密的好友,也是其中一個受害者。她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安娜,之後不斷收到安娜邀約,兩人於是成為最要好的朋友。隨著友誼漸漸深入,她卻發現安娜越來越像個陌生人。
在本書中,瑞秋完整描述被好友背叛、被迫欠下巨額債務的真相,以及揭開謎團的一步步真實過程。你將從中看見安娜的真實一面,包括她的日常生活、價值觀、詐欺手法等細節,以及讓她一路暢行無阻的那種「天性」。
▊ 最迷人的,往往也最危險
安娜「前閨蜜」的調查記錄──
►《時代雜誌》年度100大好書,《紐約時報》暢銷書
► 第一視角揭發「安娜騙局」,完整寫出事件真相
► 誰都可能是受害者!引發無數人共鳴,Amazon排行榜No.1
► 安娜是罪犯、還是夢想家?掀起國外激烈論戰的「警世故事」
一個關於 #金錢 #權力 #友誼 #背叛 的真實故事
半真半假,有時比謊言更可怕……
好評推薦
「讀這本書的享受,讓人不太好意思說出口。」──Entertainment Weekly
「寫出了安娜騙局的幕後真相,包括她如何逍遙法外……直到她被抓。本書不是虛構的,但感覺太失控了,有點不真實。」——Skimm
▊ 國際媒體.極度好評!──
「安娜騙局擁有一切題材:魅力、貪婪、權力慾望、奢華打扮、富人剝削,客串了年輕一代的騙子,包含大量精彩的紐約上流圈老故事。」──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你關注安娜出庭的所有細節(誰不是呢?),本書就是讓你上癮的夏日沙灘讀物。」──New York Post
「難以置信,令人難忘又愛不釋手:這就是《我的朋友安娜》。」──Book Riot
「安娜登上頭條之後,《我的朋友安娜》就是你想看的誘人故事……講述了被騙的痛苦滋味。」——Refinery29
「《我的朋友安娜》太棒了。」—─Bustle
「最早只是《浮華世界》的一篇文章,最後卻讓全美國人癡迷。讀這本書,你將深入紐約的精英階層,也會發現人並不總是表裡一致。」——Skimm
「在沙灘上閱讀應該是輕鬆、有趣的,而且令人食慾大增。《我的朋友安娜》絕對是夏季閱讀清單的第一名。」——Town & Country
「作者堅韌不拔、閃閃發亮的故事,定義了騙局之夏。」——Bustle
「一部激勵人心的大揭祕,無疑是今夏最受關注的一本書!」——Audible.com
「本書有力地描述了安娜的生活和罪行,更深入描繪藝術家和詐騙犯的無邊自信,以及他們眼中非常脆弱的另一群人。」──CrimeReads.com
「瑞秋詳細講述了她的經歷,遠遠超出了她在《浮華世界》的最早文章。」──Insider
▊ Amazon #Bestseller 讀者五星好評推薦!──
「是《創造安娜》絕佳的後續讀物,很有趣。」
「對安娜這種人來說,其他人只是機會與手段。他們對友誼一無所知,不曾對人投入過感情。我同意瑞秋也有點問題,但這本書揭開了騙子如何耍手段,又如何博取他人信任。我從本書得到的心得是:如果有個人看起來好到難以置信,那就該快點逃開!!」
「讀這本書很開心,給《創造安娜》與安娜的真實生活一些新見解。推薦給喜歡犯罪、操縱題材的人。」
「這本書棒極了。我認同瑞秋幫助警方做的一切。」
「引人入勝,而且都是真實的。」
「現在有些年輕人很崇拜安娜,或許他們的生活也少了一些東西。」
「迷人的第一手資料!這是真實故事,安娜自稱是有錢的德國富家女,一開始很慷慨。安娜提議去摩洛哥度假,但她的信用卡失效後,瑞秋才發現自己不得不付完帳單。瑞秋的債務超過了全年收入,但安娜一直哄騙、推遲。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可以看見年紀輕輕的安娜如何不付錢,還可以在紐約的酒店住好幾個月,以及她如何蒙騙所有人,甚至是銀行家。我很同情瑞秋。貼標籤很容易,但誰不會想跟這個特別、古怪又奢侈的富家女一起出去玩呢?」
「我看《創造安娜》之前先讀了《我的朋友安娜》,幫助我理解安娜.德爾維這個人。她是一個邪惡的、有反社會人格的騙子。她對瑞秋與那些名流所做的一切,其實都可能發生在我們任何人身上。」
「老實說,我不是很喜歡這本書的開頭……但她出人意料的堅韌創造出這個好看的故事。值得一讀!」
「總之,安娜是一個自戀者,這個事實不需要美化。Netflix則滿足了自戀者想看到的:一種自己比其他人特別的感覺。自戀人格是社會上的絕症,感染的人會用力傷害更多人,而且一點悔意都沒有。」
「精彩的警世故事,寫得非常好,一次就讀完。騙子跟反社會人格者無時無刻都在找尋目標,瑞秋,感謝妳挺身而出,如此誠實地將故事說出來。」
「比《創造安娜》更多細節。我很喜歡。」
「太吸引人了,我一口氣讀完。怕錯過任何一句話,所以連眼睛都幾乎沒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