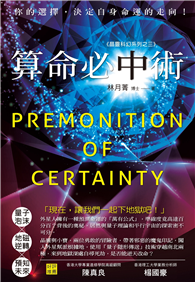導讀
是起點,不是句點:讀狂想劇場劇本《逆旅》有感
郝譽翔(《逆旅》原著小說作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我還記得多年以前,俊凱和瑞蘭特地來到我家拜訪,而那是我們初次見面,俊凱說想要把我的小說《逆旅》改編成舞台劇。
我是一個劇痴,多年下來大江南北看過的戲劇也不算少了,再加上自己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主題都是儀式戲劇,即使後來改研究現代文學,但也應該算得上是半個戲劇專家。一聽到自己的作品可以搬上舞台,真的是又驚又喜,而且俊凱和瑞蘭又是如此一對才華洋溢、充滿了戲劇熱忱的青年,我當然是毫不猶豫地一口就答應了。
然而應允的當下,我卻也不免感到憂心,在十多年前的台灣,本土論述雖然已經興起,但關於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的課題,卻遠遠不如今天受到大眾的矚目,更不及此時此刻論述的深刻和周延,更不要說,我的《逆旅》寫的是1949年發生在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慘案,也是台灣第一起外省人受難的白色恐怖,但除了相關人士的後代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和關心。
我很擔心這會是一個吃力又不討好的題材,再加上整個事件的脈絡頗為複雜,而我也不甘於只是描寫一樁白色恐怖案而已,因此《逆旅》之中既有我外省的山東父親,又有本省的澎湖母親,乃至於解嚴之後開放兩岸探親,導致台灣的國族認同產生的種種劇烈轉變。而這些複雜的前因後果,乃至於我私人對於父親愛恨糾結的情感,都使得《逆旅》這本小說不只是一個線性的故事而已,而更像是多重面向、蜂巢式的組合,這無疑更添加了俊凱將它改編成為劇本,甚至搬上戲劇舞台的困難。
但是俊凱居然做到了,而且成果令人驚艷,也獲得當年台新藝術大獎提名的肯定。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當《逆旅》上演那天,國家戲劇院的實驗劇場座無虛席,觀眾們一致屏氣凝神注視著黑暗中的舞台,呈長條狀,就位在場中央,當燈光一打,年輕的男主角提著一只皮箱,緩緩步上舞台,我的眼眶竟不禁一熱,他的身影迅速和我的父親重疊在一起,頓時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湧上我的心。
我非常感謝俊凱的改編,因為當我在寫《逆旅》之時,可以說是私密而主觀地耽溺在其中,然而在觀看《逆旅》舞台劇的演出時,我才終於得以抽離出自己的故事,客觀地看待它。尤其劇本可以說是原著的拆解和重組,對於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我彷彿得以更清楚地走這趟歷史一回,並且更深刻地感到我並不只是在寫自己的家族故事而已,而是台灣社會一個活生生的切片,甚至隱喻。
這也是《逆旅》劇本選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出版的意義了。當海峽兩岸在這些年來已經交流頻繁,不再對彼此感到新鮮好奇,甚至存在著某些盲點和成見的時候,回頭再看我書寫《逆旅》的最初動機,也就是1991年的夏天,竟和現在的社會局勢是如此地不同。當時台灣剛開放返鄉探親,對於我們而言,大陸仍然是一塊只能夠從教科書上學來、因此存在著許多不切實際想像的土地,所以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實非今日所能想像。當我一知道父親準備要回山東平度縣官莊鄉南坦坡村的老家省親時,便抱著一種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嚷著一定要跟。
然而等到我真正踏上了那塊土地之後,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原初是為了追尋新奇和刺激,到後來,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愕然和悵惘;而在歷經這一趟啟蒙之旅後,我也才知道歷史太大、個人太小,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
我還記得那個夏天大陸的北方酷熱高溫,逼近四十度。我每天望著農村四處漠漠的黃土地和高梁田,在強烈的豔陽照耀之下,彷彿蒙著一層海市蜃樓般夢幻的光。如今回想起來,也確實就像是一場夢一樣。
而我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又何嘗不像是夢呢?從我才剛開始懂事的時候,父親就反覆告訴我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年幼的我老是瞪大眼睛聽著,嘴吃驚地微張,一面喃喃說:真有這樣的事情嗎?太不可思議了。但吃驚歸吃驚,我心裡卻總懷疑是父親思鄉心切,難免要把記憶竄改渲染一番,所以這段故事不過是湮沒在歲月裡的傳奇野史,並且在那個戒嚴的年代之中,被有意無意製造出來的傳奇又何可勝數?!
直到有一天,父親又對我們說起這段往事,說著說著他就流下了眼淚。我屈指算算,距離1949年已經事隔將近五十年了,但他心中的哀傷卻是如此巨大,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就在那一刻,我才忽然在他的身上看見了歷史,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傷口、歷史的深度,也因此我決定要寫下我所看見的東西,即使這僅存在父親那被渲染誇大的記憶裡,即使我誤以為,那僅只是他自己的渲染和虛構。
當年的我是多麼的無知啊,完全不知道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像今日,關於山東流亡學生慘案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和書籍可以參考,而發生事件的地點澎湖漁翁島,也就是今日的西嶼,更已有豐富的史蹟可供查證。然而當我在2000年寫作《逆旅》時,卻僅有王志信、陶英惠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台北:山東文獻雜誌社,1996)以及陳芸娟的《山東流亡學生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六二)》(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等少數論著。我必須透過有限的文獻、父親的口述回憶和自己的想像,一點點地拼湊起這段陌生的歷史,這已耗費了我甚多的想像力。但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還是,我要如何把它們轉化成為文學作品?
在閱讀資料的時候,我深為那愚昧、黑暗而殘酷的年代感到震撼,以致我幾乎無法以小說的筆法去剝解它,甚至以為,那些赤裸裸而樸素的當事者之回憶告白,竟比起任何文學作品都還要來得更強悍有力。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文學的無用,但卻又不甘心就此放棄,總希望可以藉由我的筆,來為它們找一條不同的出路吧。所以我不直接書寫歷史,而希望通過比較跳躍的筆法,來安頓那些因而漂泊無所歸依的靈魂。
或曰是安頓我的歷史。
因為我無法漠視下列這一長串的疑問:我是如何誕生在這個島嶼上的、假如1949年我的父親沒有搭南下廣州的火車、假如國民黨不是如此昏庸腐敗、假如台灣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假如假如……。
我的父親不曾回答我的疑問,對於他而言,事情就是如此如此的發生了,沒有別的答案,而人生也不可能重來。1949年,近萬名山東流亡學生在校長張敏之的率領下,從廣州到澎湖漁翁島。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強行下令,將這群流亡學生收編入軍伍,而其中甚至包括許多未成年的孩子,凡是有不從者,就以尖刀當場刺死。聯中的校長張敏之與分校長鄒鑑援救學生不成,反而被誣指為匪諜,雙雙於十二月十一日台北的走馬町刑場遭到槍決,而前後因此喪生的學生更逾百人以上。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宗白色恐怖案,也是牽連人數最多最廣的「澎湖冤案」。
我在2000年出版《逆旅》的〈後記〉中寫道:「這段歷史幾乎未曾公諸於世。直到1999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校長夫人和子女,以及當年是山東流亡學生,包括中研院院士張玉法、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等數十名六、七十歲的白髮老人,聚集在台北市靈糧堂,一齊追悼於五十年前冤死的亡魂。在這麼長久的時光裡,他們從不曾遺忘過去,仍然在等待平反日子的到來。」
「除了他們,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在等待,例如守在電視機前的我的父親,在市場炸臭豆腐的伯伯,在捏水餃的,在煮牛肉麵的,在榮民之家角落裡殺死自己室友又自殺的。他們不但被畢生信仰的政權所放逐,又被台灣這塊島嶼所放逐,然而歷史就預備這樣子悄悄地把他們遺忘了。」
不過在2023年底的今天,我卻很高興當年我所言並沒有成真,因為歷史並沒有將他們遺忘,不僅出現了澎湖案許多相關的調查和報導,為冤者平反,還他們該有的清白,而政府單位也舉辦過多次的特展,讓一般民眾都能瞭解這段被淹沒在時光之中的過往。這讓我樂觀地相信,原來公理正義真的有到來的一天。
但故事不應該就此畫下句點。我想這是狂想劇場出版《逆旅》劇作的重大意義,身為一個創作者,永遠可以看穿事物的表象,而發現其中潛藏著更多更多的可能。我但願是一個起點,而不是句點。當然,更要感謝我們的父母輩、乃至祖父母輩們,若不是我們的命運和他們憂戚相關,又何以能讀見了人生的這一本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