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國家暴力底下的「一貫叛亂犯意」——為狂想劇場的《非常上訴》而寫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刑罰,是合法的暴力。日常生活中,殺人、拘禁、侵佔,都是不被允許的;但是,經過一定的訴訟程序,判決定讞之後,國家可以對被告處以死刑、有期徒刑、沒收或科以罰金――既殺人,又拘禁,還侵占。為什麼我們允許國家對個別人民擁有施加暴力的可能性?典型的說法是,這是社會生活所必須,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例外地允許國家獨佔刑罰權,對「犯罪」的人民施加暴力。
不過,法律是國家制定的,什麼情形構成犯罪,也是國家定義的。這似乎形成一個奇怪的狀況:國家可以自己決定在什麼條件下對人民施加暴力,而人民只能遵守法律、服從判決。如果人民不認同那些法律,也不打算遵守,就會被國家「繩之以法」。假設國家法律規定盜獵兔子、偷鹿、撿拾林中木材,都處以死刑,人民好像只能遵守,無法反抗。但問題在於,「好像」遵守法律和「願意」遵守法律之間有一段蠻大的差距。
人民如果只是基於畏懼失去生命、自由和財產,而遵守法律,那就是「好像只能遵守」,也就是在沒有選擇的狀況下,遵守法律。但沉默地不違抗法律,算是「願意」遵守法律嗎?比較常見的提問是:「惡法亦法,所以人民還是必須遵守惡法嗎?」
遵守法律如果無法帶來正義的實現,人民遵守法律的意義何在?到什麼程度,人民可以違抗法律呢?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戰後曾經指出:「法律與正義並非立法者所得任意處置。『德國的納粹政權時期正表明了,立法者也可能制定不正義的法律』。因此聯邦憲法法院肯認有可能否定納粹『法律』規定的法效力,因為他們是如此明顯地抵觸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以致於想要適用這些規定或承認其法律效果的法官都將作出不法裁判而非依法裁判。」
台灣自從1949年五月十九日,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的戒嚴令之後,翌日即進入戒嚴狀態;再加上前一年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在第一次會議中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年五月十日公布),直到1987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1991年五月一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這段期間,長期處於國家權力極端擴張、欠缺制衡的統治結構。這種狀態持續長達三、四十年,因此,曾經有人認為如果遽爾認定當時的國家是屬於像納粹一樣的「不法國家」,將造成這段期間所通過的法律和法院作成的判決,都可能在民主化之後被推翻,這等於是徹底否定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於是,從終止萬年國會的大法官解釋第二六一號(1990)開始,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就沒有對那段時期進行過定義。再不然,就是用抽象的「非常時期」(如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第四七七號解釋)來描述。
但是,「非常時期」的法律應該如何予以評價?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六七號解釋(2003)中針對〈預防匪諜再犯辦法〉指出:「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之規定,亦不符合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以此宣告該規定違憲。換句話說,非常時期的法律也必須符合「最低限度的人權保障」。
「最低限度的人權保障」指的是什麼?大法官在這一號解釋裡面以思想自由為例,認為「最基本的人性尊嚴」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就是「最低限度的人權保障」。其實,自從民主化以後,大法官透過許多解釋已經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法秩序,有別於戒嚴時期和動員勘亂時期。這個新的法秩序一方面象徵了揮別過去陰霾,另方面也標舉了新的民主憲政價值。
這一套新的民主憲政價值後來就成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依據,例如《促轉條例》第六條就規定:「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立法者在此同時並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和「公平審判原則」,作為衡量判決是否撤銷的價值基準,並且強調司法平反的目的在於彰顯正義、導正法治和人權教育,促進社會和解。
然而,沒有徹底而全面的清查案件,進行實質調查,只是形式性地頒發撤銷判決證書,縱使總統和行政院院長到場觀禮,對於曾經蒙受不正審判的當事人而言,又能證明什麼呢?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就是要顛覆國民黨政權,因此拒絕被撤銷呢?
*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軍法判決,充滿各種類型: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案件(如李媽兜、簡吉或鹿窟事件的陳本江等),有些是外省籍的政治異議份子案件(如雷震、傅正、李敖),有些是台獨案件(如泰源事件),有些則是因為主張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如美麗島事件、八○年代的黨外運動)。
有些人如《非常上訴》的主角之一楊碧川,始終認為自己就是主張台獨,就算被扣上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和刑法第一百條的罪名,亦無懸念。有些人如本劇另外一位主角陳欽生,始終認為自己無辜、受到牽連,屈打成招,僅憑自白定罪。無論是冤假錯案或罪有應得,1987年解嚴前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早已限制了當初受到軍事審判的一般人民上訴,剩下的途徑就只有非常上訴和再審。而2017年通過的《促轉條例》再次不分案件,直接撤銷,事實真相恐怕就此沉埋。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非常上訴是針對法院的判決是否違背法令,進行救濟。過去長期以來的實務見解認為,非常上訴的功能在於「統一法令見解」,因此不用考慮被告、辯護人、自訴人或委任代理人的意見。而且所謂「判決違背法令」,排除了不同法院或法官之間所持的法律見解不同,最高法院曾有判例認為:「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判決有隨時搖動之虞,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反足以阻遏運用法律之精神,故就統一法令解釋之效果而言,自不能因後判決之見解不同,而使前之判決效力受其影響。」
如果貫徹這種見解,即便解嚴後的法官認為刑法第一百條的「著手實行」應該要達到強暴脅迫的程度,也不構成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的理由。因為這可能只是法律見解不一致而已,不可以用後來的見解去「動搖」已經作成的確定判決。類似這種想法,也可見於大法官第二七二號解釋,其中提到:「(國安法第九條限制)於解嚴後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係基於此次戒嚴與解嚴時間相隔三十餘年之特殊情況,並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所謂的「裁判之安定」,是以犧牲人民基本權利和案件真相為代價,維持戒嚴體制不受動搖(或者可以稱為「不法的安定性」)。
如果我們陷在一條一條法律和一個一個案件當中,很可能也得到相同於上述的結論,畢竟那些規範和判決都曾維繫了威權時期的國家運作。所以,我們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評價當時的統治正當性。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曾經以「憲法破棄」和「不法國家」來定性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前的統治狀態,但真實的憲法法庭在釋字第七九三號(2020)當中依照既有的歷史研究,指出當時延續了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因為「中國國民黨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從而原應隨憲法施行而結束之黨國體制,得以事實上延續」。這段話點出了台灣轉型正義的關鍵因素:黨國體制。當一個政黨打算長期壟斷政治權力,就可能凍結憲法條文、停止民主選舉、擴張政治刑法、採用速審速決的軍事審判、罔顧基本人權。而這正是戒嚴體制和動員戡亂體制的由來,也是以一代又一代的白骨累積出來的政治奇蹟。
在此情形下,在陳欽生或楊碧川的判決中都可以看到的軍法判決常用套語:「基於一貫叛亂犯意」,這其實隱喻了「人民不可挑戰獨裁者的權威」,否則你的一言一行都會是「一貫」的、隨時可以抓去關的「叛亂犯意」。無論你是擁抱新中國的地下共產黨員,要求實施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編輯,認為戒嚴令無效、應該廢除萬年國會的《美麗島》成員,或是主張成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運動成員,通通都是「基於一貫叛亂犯意」,挑戰獨裁者和黨國體制的權威。《非常上訴》以紀錄劇場的形式,不斷提示、挑戰觀眾,究竟為何人民要遵守這樣的國家制定出來的法律?除了那些真的被國家暴力「繩之以法」的政治受難者以外,那些看起來「好像」默默在遵守法律的人們,他們內心在想什麼?沉默的多數,是否心中就沒有想法?沒有「一貫」的意思?
時至今日,如何考掘當時的集體意識,已經成為歷史公案。但透過劇場觀眾的參與,也許可以知道未來再次遭遇到類似的情境時,今天的觀眾將如何選擇:我們為何允許國家取走性命?我們為何「願意」遵守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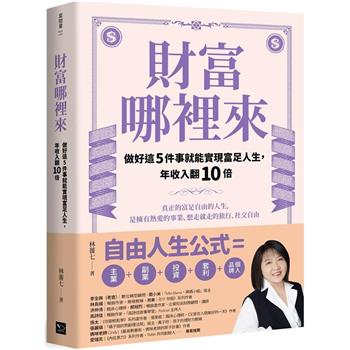




 2026【圖表整理+最新法規】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看這本就夠了[十六版](初等考試/五等特考)](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4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