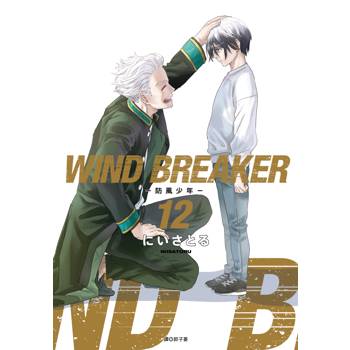先說一個典型離散,在日朝鮮人作家的故事。
多年前在東京聆聽在日朝鮮人金石範述說以日語寫作的經驗,尤其提及寫作本身是個屈辱的過程,後來才明白金石範利用曾是帝國語言的日語,藉以克服自己內部殖民性的方式來尋找自由,而以日語寫作也是他和年輕一代的在日朝鮮人的溝通方式。從金石範的談話,深刻感受作家和語言的抗爭。在日本國民文學裏,無論是在日朝鮮人文學或是沖繩文學,皆處於邊緣位置。在日朝鮮人用日語創作的日本文學,促使日本文學概念的重新界定。通過「在日」,被迫反思的不僅是日本文學的定義與概念,當下的韓國文學亦然。
作家與語言的關係,如此微妙、複雜。語言在國家體制結構的權力,亦形成文學書寫的權力意識,這當中具有歷史時間的刻度。但是不是必須進入到強勢語言或主導的文學語言,才真正能轉化或重新定義語言於文學的中介和作用?文學語言的選擇一般是有明確的意向考量,這樣熟悉的論調,也是馬華文學恆久面對的處境。但或許仍缺乏像金石範用他極力克服的語言,寫出不能讓人忽視如《火山島》等小說,才能撼動原有的文學(史)邊界。不過金石範所在意的不是由國境建構起的文學,而是個人的主體經驗如何被看見。
在很長一段時間,馬華文學仍無法擺脫語言政治與認同的糾葛 ,用「華語」寫作這回事被賦予某種抵抗的意義。當李永平在小說課上說「我要懺悔」,似乎是人生中有關語言的最後的告解──關於那怪怪的南洋華語、南洋腔,在多年以後驀然回首,領悟那是珍貴的創作資源,卻終究無法跨過正統中文的樊籬,對方塊字的虔誠信仰。語言的懺悔,並非含有抗衡的用意,事後的反思更顯現回歸創作的在地語言特色。王德威認為馬華文學作為一種「小文學」,來自馬華族羣對華文文化存亡續絕的危機感。語言是文化傳承的命脈,作為語言最精粹的表徵,文學是文化意識交會或交鋒的所在。 無論是張貴興語言彰顯的暴力美學、黃錦樹的「怨毒著書」(王德威語),甚至是黎紫書《流俗地》中回歸寫實的「流俗」書寫,語言作為書寫的中介,便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政治性的操練而已。一旦文學大於政治,語言本身便有能力消解其政治性,轉化出文學自身的力量。
不僅是語言的困擾,馬華文學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如輪迴鎖鏈般的拉鋸中,消耗不少寫作者的精力,也讓讀者感覺「後論爭時期」的認知與理解疲勞。這樣的文學論爭雖並非毫無意義,卻須追問它所累積的文學思想資源是甚麼,而非僅剩迷濛的煙硝。倘若以韓國文學為例,同樣長期被放在對立位置的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論爭火藥庫中,韓國文學評論家崔元植曾指出「文學論爭就是包括了政治社會層次的思想論爭及實踐論爭」,並論及二者的「會通」可能性,是個有趣的視角。 崔元植以韓國詩人金洙暎的詩作為例,指其超越一般性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創作批評意識,把握與包容二者的差異作為反思與創作實踐基礎,後來作家在批判性繼承與否定的文學遺產中,獲得超越兩分法的機遇。雖說在之後的文學發展中,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再次築起高牆,但在累積的相關討論中,關於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與韓國文學界中的「近代」與「現代」意識,以及如何形成「反左」、「反右」的支配性文學意識型態等,獲得細緻的歷史性梳理。換言之,「歷史化」文學論爭,正是把握「主義」發展的現實條件,審視美學觀念的歷史演變,以及不同時期文學主體的建構。這有助於從概念先行中解套,避免把二者作為牢固不可撼動的標準,稀釋了二者的對話空間。
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論爭,受制於文化冷戰諸因素的影響。但在前冷戰時期,南洋的文化場域實流動著不同的思潮,包括一九一○年起已踏足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一九三○年代之後逐漸佔據文學中心話語的左翼革命思想等,可知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前,仍未形成鮮明分判的左翼與現代陣營。後來《蕉風》與《浪花》文學雜誌掀起的文學論戰,逐漸成為兩大陣營作家的角力場。
如何重訪這一些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與思想遺產,重新建立馬華文學的「近代」與「現代」意識,以貼近語境與時代脈動方式考掘與馬華文學相關的議題,考驗著我們對於馬華文學的認識論與知識論的視角。這一本論文集,以「亞際南方」為出發點,一來是藉此思考馬華文學的「南方」意義,無論是從文化、語系或文學地理想像,有意在全球南方思維下辨識所謂屬於「南方的聲音」。另則帶著期待一種亞際間的相互看見與理解,重新思考馬華文學與亞際(之間)文學的參照,尤其是比較不同的亞際地域如何通過文學進行現實的探索,各自的文學論爭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學史框架等問題。無論是通過創作或批評、研究的交流,實是十分有限。過去較少把馬華文學放到亞際(之間)的文學場域,她與中、臺、港之間已形成牢固共構關係的「縱的思考」,因此如何打開亞際小文學場域之間的「橫的參照」,生產出不同的文學批評與研究景觀,或是有待嘗試與努力的方向。縱然這當中仍需要克服不同的文學歷史經驗以及文學翻譯的中介,也唯有這樣,才能擴大真正意義上的「南方視野」。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15 |
小說/文學 |
$ 333 |
大學出版品 |
$ 333 |
中文書 |
$ 333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
本論文集以「亞際南方」為出發點,一來是藉此思考馬華文學的「南方」意義,無論是從文化、語系或文學地理想像,有意在全球南方思維下辨識所謂屬於「南方的聲音」。另則帶著期待一種亞際間的互相看見與理解,重新思考馬華文學與亞際(之間)文學的參照,尤其是比較不同的亞際地域如何通過文學進行現實的探索,各自的文學爭論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學史框架等問題。
作者簡介:
◎張錦忠
生於馬來西亞,一九八○年代初來臺。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近作有短篇集《壁虎》、詩集《像河那樣他是自己的靜默》、短論集《查爾斯河畔的雁聲:隨筆馬華文學二集 》。
◎魏月萍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現為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副教授。研究關懷為中國思想史、馬新文學與歷史。著有《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2016)、《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魏月萍》(2019);與朴素晶合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儒學建構與實踐》(2017) ,與蘇穎欣合編《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2017),Revisiting Malaya: Uncover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Nusantara (2020)。
作者序
先說一個典型離散,在日朝鮮人作家的故事。
多年前在東京聆聽在日朝鮮人金石範述說以日語寫作的經驗,尤其提及寫作本身是個屈辱的過程,後來才明白金石範利用曾是帝國語言的日語,藉以克服自己內部殖民性的方式來尋找自由,而以日語寫作也是他和年輕一代的在日朝鮮人的溝通方式。從金石範的談話,深刻感受作家和語言的抗爭。在日本國民文學裏,無論是在日朝鮮人文學或是沖繩文學,皆處於邊緣位置。在日朝鮮人用日語創作的日本文學,促使日本文學概念的重新界定。通過「在日」,被迫反思的不僅是日本文學的定義與概念,當下的韓國文學亦然。...
多年前在東京聆聽在日朝鮮人金石範述說以日語寫作的經驗,尤其提及寫作本身是個屈辱的過程,後來才明白金石範利用曾是帝國語言的日語,藉以克服自己內部殖民性的方式來尋找自由,而以日語寫作也是他和年輕一代的在日朝鮮人的溝通方式。從金石範的談話,深刻感受作家和語言的抗爭。在日本國民文學裏,無論是在日朝鮮人文學或是沖繩文學,皆處於邊緣位置。在日朝鮮人用日語創作的日本文學,促使日本文學概念的重新界定。通過「在日」,被迫反思的不僅是日本文學的定義與概念,當下的韓國文學亦然。...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001 魏月萍|緒論:南方的「亞際想像」
卷壹 ◎ 民國、冷戰、共同體
011 黃錦樹|馬華身後有一個民國的影子:試論馬華文學的民國向度
029 王梅香|自由世界的文化長城:馬來亞學友會的社群想像與認同形構 (1955-1969)
065 林春美|黃崖與一九六○年代馬華新文學體制之建立
089 黃琦旺|星座詩社與六○年代馬華文學的現代主義
125 張錦忠|動盪的一九七〇年代:馬華文學之為「無為共同體」
卷貳 ◎ 前冷戰、跨界、文學史
141 許德發|一九二○年代泰戈爾來訪與馬來亞華人的社會反響:兼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前左翼」場域
...
卷壹 ◎ 民國、冷戰、共同體
011 黃錦樹|馬華身後有一個民國的影子:試論馬華文學的民國向度
029 王梅香|自由世界的文化長城:馬來亞學友會的社群想像與認同形構 (1955-1969)
065 林春美|黃崖與一九六○年代馬華新文學體制之建立
089 黃琦旺|星座詩社與六○年代馬華文學的現代主義
125 張錦忠|動盪的一九七〇年代:馬華文學之為「無為共同體」
卷貳 ◎ 前冷戰、跨界、文學史
141 許德發|一九二○年代泰戈爾來訪與馬來亞華人的社會反響:兼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前左翼」場域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