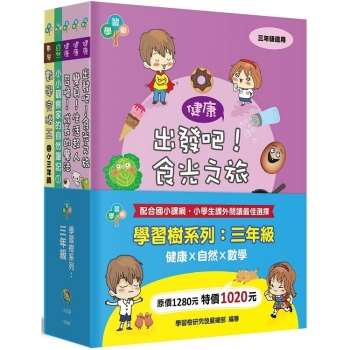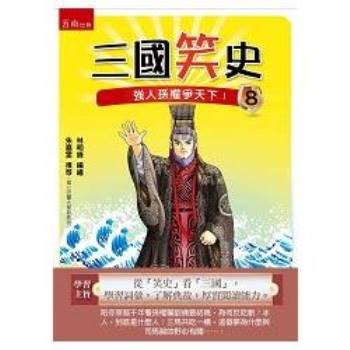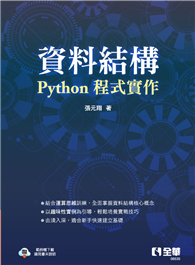菁英王牌律師 X 清冷外科醫生
現實白色巨塔底下的甜寵救贖
POPO站上讀者口碑爆棚
現實白色巨塔底下的甜寵救贖
POPO站上讀者口碑爆棚
這人太奪目了──耀眼到幾乎刺痛他的雙眼。
「我大概把前半生的運氣都攢起來了,才能遇到你。」
★特別收錄全新番外〈戒指〉
紀項秋的那份溫柔,將明琛自我保護的外殼,摧毀得體無完膚。
於是他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濟世愛人,希望常明。
常明醫院,是整形外科主治醫師明琛工作的地方。
世人以為絕對中立、仁愛,旨在救人的醫院,其實從來都沒有那麼乾淨,
三年前,無權無勢的明琛甚至被逼著擔下了一起醫療糾紛的黑鍋。
因為一樁案件,明琛和律師紀項秋在法庭上初次見面,
真正相識卻是在當晚,一間群魔亂舞的酒吧裡。
明琛滿心傷痕、借酒澆愁,而紀項秋恰巧出現在了這個時候。
「你還好嗎?」
「不好又怎麼辦,你要安慰我嗎?也可以啊。」
「你不要後悔。」
「我有什麼能後悔?」
他們之間由一夜情展開,未曾言及情愛與承諾,
然而紀項秋執拗的溫柔,卻又那麼引人沉淪。
握住紀項秋伸來的手,明琛終於逐漸從那一片漆黑泥沼中抽身,
走向屬於他的、那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