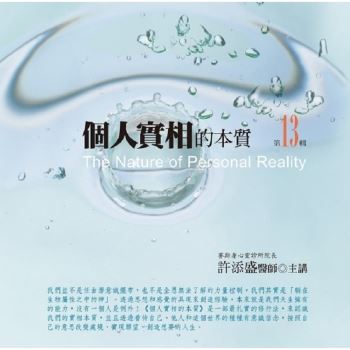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相遇,
也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有美好結局……
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這麼多年》!
同名電影即將改編開拍!
她不懂什麼是愛,
直到傷得體無完膚才明白,
一絲絲的甜,就足以腐蝕她易碎的心……
一直以來,見夏就夢想著要離開家,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如今她來到了繁華的省城,擠進象徵成功的明星高中,
她卻盼望著時間越慢越好,和李燃的距離越近越好,
因為他們之間,隔著一條像是永遠也走不完的長廊,
她在課堂裡讀書考試,他在操場上揮霍青春;
她為學業成績焦慮,他卻忙著和隔壁班女生玩樂打鬧……
她是優秀的好學生,他是成天惹事的不良少年,
見夏可以輕鬆解出艱深的數學題,卻算不出李燃的心裡究竟有沒有她。
或許正如大人們所說,她和他,從來就不是「他們」。
而隨著兩人的「秘密」曝光,見夏一瞬間跌入地獄,
曾經,李燃是一張溫暖柔韌的網,總能緊緊接住她所有的脆弱,
現在,他不接電話、不讀訊息,人間蒸發。
她,又再次變回自己一個人了嗎?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這麼多年(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8 |
愛情小說 |
電子書 |
$ 225 |
現代言情 |
$ 236 |
Books |
$ 236 |
Books |
$ 236 |
大眾文學 |
$ 263 |
中文書 |
$ 263 |
大眾文學 |
$ 269 |
華文愛情小說 |
$ 26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這麼多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