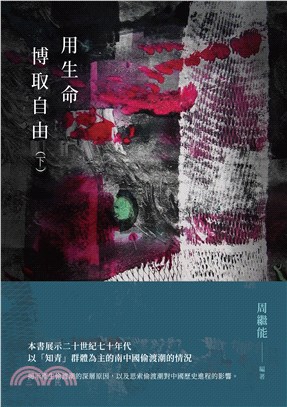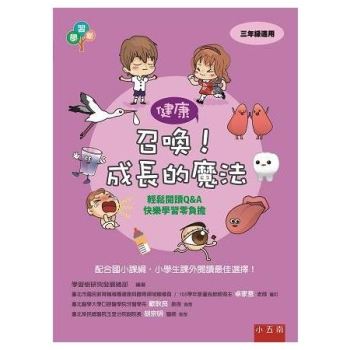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感慨繫之話「起錨」/黃東漢
(一)希望能喚起一代人的記憶
在香港的知青相當一部分是當年的「起錨」客,「起錨」本指船舶開航的意思,但在那瘋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廣東知青)中,卻有另外一個意思,在廣東當年一提起這一專有名詞,人們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錨」是一種賭博,參與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與生命,那時參與這個「賭博」的廣東知青為數不少,有的贏了,有的輸了。
人生如夢,幾十年後回顧一下,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們「起錨」的一群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留下來到了今天,我們或許也會有不錯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享受了幾十年的那種自由,這裡會有麼?當局雖然在1979年以「非法探親」的名義對我們從輕發落,但是,對於當年廣東知青大量偷渡的歷史,官方諱莫如深。縱觀現今國內外的文藝作品以及網站,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幾乎沒有。可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你不提不等於沒有發生,中國的知青史如果缺了廣東知青大「起錨」這一段就不完整。隨著時間的流逝,「起錨」和全國的知青史一樣,快要從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消失了。我在這裡把我所知的有關「起錨」的往事整理一下寫出來,雖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喚起一代人的記憶,以警醒後世。
(二)我的「民兵」身份
我的下鄉地點是寶安縣南頭公社南山大隊,出門就是後海灣,海灣對面就是香港,生產作業養蠔經常在後海灣進行,那麼香港對於我來說就是伸手可及了。
當年由於我下鄉的地方是在最前沿的海邊,所以一來馬上成了民兵,晚上要站崗放哨。站崗放哨不是為了防「帝國主義入侵」,而是「反偷渡」—防止外逃。由於人手少,放哨時都是單個的在海邊躲起來放暗哨。我第一次半夜裡放哨,當地的民兵隊長就對我說:「如果看到集體偷渡,你一人一槍要注意安全,在這裡夜間集體逃亡是常有的事。」我隊的民兵從不抓人,白天開工時,經常聽到他們說昨夜又看到幾十人從××地方下海了。當地不少人常說:「都是鄉里鄉親的,大家都說同一方言,下不了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們過去就算了,說不定不知什麼時候自己也會走上這一條路。」我在海邊站了不少次崗,幸運的是我從沒遇上大規模的集體「起錨」,但遇到一次的事卻令我畢生難忘。
那是一天晚上,我一個人放哨,我正在打瞌睡,忽然一個濕漉漉的傢伙在我面前站起來,那傢伙問我這裡是香港的什麼地方?這個蠢東西竟然把我們這裡當成是香港新界了,更令我吃驚的是在手電筒光的照射下,那傢伙竟然是個我認識的人,一個同校下放到相鄰大隊的知青,一個昔日在學校球場上的球友。他也認得我,雙方驚呆了幾秒鐘,鑒於往日球場上的友誼,我把他帶到我住的屋子。第二天一早對人說他是來探我的,然後就把他送走了。當然也少不了罵他一頓「以後聰明點,哪兒燈光亮往哪兒游,別再栽到老子手裡。」
當地鄰村有一個農村姑娘,20歲長得胖胖的,喜歡穿白衣裳,當地人都喜歡叫她「肥妹」。幾個月前她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走了,她身邊的朋友、同學、親人越來越少,一天夜裡為了追尋親情與愛情,一個不會游泳的姑娘單獨抱著一個球下了海。第二天早上八、九點我們在海邊開工的時候,突然有人在高呼「肥妹在海裡!」所有人馬上向遠處望去,果然見到一個小白點在遠處漂浮。也許是她運氣好,天明時她已經漂過了中間線,中方的炮艇沒有開過去捕撈,不久岸上的人看到一艘香港漁船開過去把她救起了,幾天後從香港傳過來的消息說肥妹平安與香港家人團聚了。
雖然「階級鬥爭」將人性泯滅,但在鄉民中人情味還是存在的,我的鄰村有一對林姓的知青兄弟,第一次「起錨」失敗了,給五花大綁的綁在公社大門口,由於那兩兄弟平時表現不錯,人緣也好,當地駐軍的指導員經過一看見,馬上把他們擔保了出來,理由是交給我們帶回去進行再教育,免去了那兩兄弟進「大倉」、食四兩米之苦。「大倉」是當年關押逃亡者的拘留所,據進去過的人說:「人多的時候,別說躺下,就連站著也覺擠迫。」至於四兩米就是當年對進「大倉」的人的「伙食」標準,一天四兩米,半個月下來,人自動瘦了一圈。林氏兄弟雖然給保了出來,回到生產隊裡過一過堂還是免不了的。當年我們那裡經常舉行對偷渡失敗者進行「再教育」的批鬥會。開會的時候,失敗者站在臺上先作一輪「深刻」的思想檢查,然後是幹部和社員發言,對其進行再教育。這樣的批鬥會剛開始的時候還比較認真,但到後來,「起錨」成功的人越來越多,來開會的人越來越少,大家開會的興趣越來越低,漸漸地批鬥會就有點變了質,變成好像是歡迎失敗者重新回來的歡迎會。主持批鬥會的幹部一般都很有分寸和技巧,因為他們也知道世事如棋,「今日留一線,它日好相見」。如果今天對人狠,難保它日站在臺上挨鬥的不會是自己。如果被鬥者是知青,那就更加多幾分同情分,這些遠離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太難為他們了。
據一位多次被批鬥的人回憶說,在批鬥會上他們最喜歡高喊的毛語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每當臺上臺下都高叫這一口號時,有些人會笑出來,因為他們知道,此時此刻,那句語錄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批鬥會通常都會在嬉笑怒罵、亦莊亦諧的氣氛中結束。對於挨過批鬥會的知青來說,這一回是挺過去了,但從今以後,他們將自動成為新的階級敵人,新的專政對象,今後入黨,入團,提幹,回城,升學等好事將會永沒他們的份,在今後的日子裡,在新的運動中他們將會不斷的挨鬥。為了前途,他們必須不斷的「起錨」下去,直到成功為止。
當年當局為了堵截內地其他地方的人「起錨」,在東莞縣和寶安縣交界處,即樟木頭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鎖線。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在封鎖線以南的寶安縣境內,是路路設卡,村村設防,經常有真槍實彈的軍警和民兵搜捕逃亡者。「起錨」者一進入了寶安縣,就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間翻山越嶺。在寶安縣境內大部份地方都是丘陵小山,由封鎖線起到邊境這幾十里山路,今天開著小轎車在高速公路半小時就過去了。但當年「起錨」的大多數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生活經驗不足,手中只有簡單的地圖,指南針及小量乾糧,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的草叢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緩慢的前進,往往一個晚上走不了幾里路,這幾十里山路「起錨」者們往往要走一個星期左右,好運的才能到達邊境。逃亡者在這幾十里山路中既要趕路,又要躲避軍警的追捕,還要遭受蚊叮蟲咬、毒蛇野狗的襲擊,再加上饑渴,運氣不好的遇上軍警被捕,前功盡廢。好運的遇上那些好心的上山砍柴的農民,好心人看到這些筋疲力盡,饑腸轆轆的小青年,多數都會給他們指明方向,教他們如何繞過軍警。「起錨」者多數會結隊同行,由那些有多次「起錨」經驗的識途老馬帶路。在夜間,一幫人在山裡很容易失散,但不要緊,很容易又會遇上另一幫人,一個眼神,幾句說話就能重新形成新的組合繼續上路。那年頭生活在封鎖線內的知青和原居民都有邊防證,出入都要帶上,當時的邊防證一證難求,擁有一張邊防證真的羨煞旁人,因為在封鎖線內生活的人「起錨」時比外面的人方便得多,成功的機會大得多。
下鄉一年零三個月後,我也「起錨」去了香港,我從反偷渡的「民兵」,變成了偷渡者,也算是一種角色轉換了。
(三)令人唏噓的悲喜劇
好運氣的到了邊境,也不一定成功。當年過境的路線主要有三條,中間那條由福田到沙頭角這20公里左右是陸路,翻過鐵絲網就成(中、英各一道噢)。但這一路防守最嚴密,現代化的鐵絲網加上林立的崗哨及警犬,逃亡者很難從這裡過去,但也有少數成功的例子。東線沙頭角以東是大鵬灣,這裡風大浪急,又有鯊魚,風浪和鯊魚常常令到逃亡者葬身大海或魚腹,因此這裡防守要松一些。西線從福田一直到蛇口是後海灣,這裡因為靠近珠江口,海水淡些,所以沒有鯊魚,海面雖寬,但有些地方水很淺,遇上大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間一條小水道。但水淺並不好走,一旦陷在泥灘裡寸步難行,踏到了蠔田更加會遍體鱗傷。但由於風浪較小,加上軍警防守比中央陸路要松些,所以後海灣是「起錨」者越境的熱門地點。
千辛萬苦到了海邊,還要面對茫茫大海,要在黑夜裡游過海峽,才算成功,這就要求每一個「起錨」者要有高強的游泳技術和體力。當年為了能成功「起錨」,倒流回廣州的知青都會到當時為數不多的泳池裡去練水,一下池就是一千米、二千米,一小時、兩小時不靠池邊地苦練。1969年夏天我倒流回廣州時,在泳池裡就有三小時不靠邊的記錄。為了提高實戰訓練水準,不少人還會到珠江裡去游長途。老一輩的廣州人都應該記得在60年代尾至70年代末在廣州西村水廠到「石門返照」的一段十公里左右河面上,經常有準備「起錨」的人在實練。他們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塑膠袋,用繩子捆好拖著游,潮漲時去,潮退時返,這樣的實練比在泳池裡練更加有效用。
一個人怕不怕死,夠不夠朋友,不能只聽他說的,真要到了生死關頭,才能看得出來。而在生死關頭,一瞬間的錯誤,將會悔恨終生。下面兩個事例,都是我身邊朋友的真人真事,聽落都會令人感慨萬分。
第一個是臨危搶球膽,悔疚一生。主角是我的小學同學,一姓胡,一姓董,本來胡、董兩家是親家,姓胡的姐姐嫁給了姓董的哥哥。在那年頭,姓胡的因為父親是廣州一間中學的校長,他自然的就成了「黑七類」而下鄉去了,而姓董的也當了知青。由於感到前途無望,他們相約一起「起錨」,同行還有一個姓張的。千辛萬苦他們到了大鵬灣,夜裡下了海,由於風浪大,他們的水性又不那麼好,在風浪中姓胡的球膽破了,喝了不少海水,在生死一線的時刻,在求生的欲望中他本能的把在旁邊姓董的球膽搶了去。姓董的沒了球膽,很快就沉下去了。而這一切都看在附近姓張的眼裡,姓胡和姓張的最後上了岸,但因為姓胡的搶了姓董的球膽而令其身亡,姓張的從此看不起他,兩人成了寃家。噩耗傳回廣州,姓董的母親哭哭啼啼的拿著一把菜刀到親家胡家去斬人,為兒子報仇。這斬人的一幕給我另一個同學看到,從此傳了開來。姓胡的因為自己害死了姓董的,從此也永遠活在痛苦的陰影裡,悔疚一生。一上岸就以難民的身份移民加拿大,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我們都已經回廣州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愧對親友,一直躲在加拿大不敢回來。九十年代初,他姐姐一家移民加拿大,姓胡的把自己經營的餐廳送給姐夫,但仍然得不到董家的原諒。
另一個例子就剛剛相反,一對周姓姐弟,一繩牽生死。姐姐身形纖瘦,弟弟略胖,姐弟二人千辛萬苦在1973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來到了後海灣的海邊。一到海邊就立刻躲進紅樹林水中,他們剛到的那一晚,一個強大的颱風剛好在後海灣登陸,海面上波濤洶湧,兩姐弟不敢此時渡海。為了不被大浪沖散,姐弟二人用一條長繩一人一端捆好,兩人通過一條繩子連在一起。夜裡風浪越來越大,學過物理的人都知道,波浪到達岸邊的時候,由於地形的改變會變得更高。半夜裡小山一樣的大浪把身形纖瘦的姐姐無數次的舉起,欲將其吞噬,弟弟一手抓住紅樹林的樹枝,一手死死的拉著拴著姐姐的繩子不放,即使巨浪也把他吞沒了,他也不放手,一次又一次把將被卷走的姐姐拉回身邊。和巨浪搏鬥了整整一夜的姐弟倆終於捱到了天明,颱風漸漸遠去,海面平靜了一些,但白天不能行動,兩姐弟必須在水裡再浸一天,晚上才能行動。到了晚上,已經在水裡浸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餓筋疲力盡的兩姐弟用僅余的體力開始游泳。在大海中泳術較好、身形纖瘦的姐姐游得較快,弟弟泳術較差游得慢,加上體力所餘無幾,在海中幾次沉了下去,但姐姐絕不放手,雖然她知道如果不解開繩子,最終可能會兩人都同歸於盡。在危難中姐姐也沒有放棄弟弟,她也一次次把弟弟拉回身邊。最後他們勝利了,天明的時候,筋疲力竭的姐姐把奄奄一息的弟弟拖過大海,爬上了香港新界的沙灘。這兩姐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姐弟情深,生死一繩牽的事蹟在我們知青「起錨」者的一群中流傳很廣,成為大家的美談。那兩姐弟經過了這次生死劫難後,在以後的幾十年人生中,姐弟情維繫得非常好,即使後來各自婚嫁成了家,兩個家庭的聯繫比起很多家庭都親密,是我們一群人的典範。
節錄自 感慨繫之話「起錨」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用生命博取自由(下)(POD)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用生命博取自由(下)(POD)
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南中國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迴避的痛史,也是一項可歌可泣的壯舉,更蘊含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契因。
1、反映了中國知青運動中被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慘的一段痛史。
2、代表了十年浩劫中人民爭取人權的壯舉。
3、體現了中國歷史的正確進步方向。
——引自本書阿陀先生〈南中國知青偷渡潮〉一文
本書力圖反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知青」這個群體為主的南中國偷渡潮的情况,揭示產生偷渡潮的深層原因,以及思索偷渡潮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作者簡介:
▌周繼能編著
作者1947年生,66屆高三畢業生,1969年留城入工廠,沒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亦沒有「起錨」偷渡的經歷。
作者近年結識了眾多當年的偷渡者,訝然於自己對同代人當年的苦難情仇茫無所知,被這個群體歷經的各種苦難艱辛、他們與命運抗爭的精神所震懾,心靈顫動,覺得有責任將這一切記錄下來,勉力為歷史留住一筆。
由於力薄筆拙,本書未能達成初願於萬一,僅係綿力略盡而已。
章節試閱
▌感慨繫之話「起錨」/黃東漢
(一)希望能喚起一代人的記憶
在香港的知青相當一部分是當年的「起錨」客,「起錨」本指船舶開航的意思,但在那瘋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廣東知青)中,卻有另外一個意思,在廣東當年一提起這一專有名詞,人們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錨」是一種賭博,參與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與生命,那時參與這個「賭博」的廣東知青為數不少,有的贏了,有的輸了。
人生如夢,幾十年後回顧一下,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們「起錨」的一群到底是贏了還是輸...
(一)希望能喚起一代人的記憶
在香港的知青相當一部分是當年的「起錨」客,「起錨」本指船舶開航的意思,但在那瘋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廣東知青)中,卻有另外一個意思,在廣東當年一提起這一專有名詞,人們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錨」是一種賭博,參與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與生命,那時參與這個「賭博」的廣東知青為數不少,有的贏了,有的輸了。
人生如夢,幾十年後回顧一下,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們「起錨」的一群到底是贏了還是輸...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代序 關於南中國知青偷渡潮的思考/阿陀
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南中國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迴避的痛史,也是一項可歌可泣的壯舉,更蘊含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契因。
1、 反映了中國知青運動中被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慘的一段痛史
當年南中國知青共有多少人捲入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罹難死於非命?筆者只是一個身居海外的業餘研究者,慚愧自己沒有能力調查出確實的數字,只能提供隨機調查的結果。
迄今為止,詢查過的廣州三十多位不同學校或同校不同班級的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級都...
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南中國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迴避的痛史,也是一項可歌可泣的壯舉,更蘊含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契因。
1、 反映了中國知青運動中被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慘的一段痛史
當年南中國知青共有多少人捲入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罹難死於非命?筆者只是一個身居海外的業餘研究者,慚愧自己沒有能力調查出確實的數字,只能提供隨機調查的結果。
迄今為止,詢查過的廣州三十多位不同學校或同校不同班級的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級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回眸與沉思
阿 陀 南中國的知青偷渡潮—廣州培英中學老三屆調查
黃東漢 感慨繫之話「起錨」
陳克治 逃港知青五,一拜祭活動的起源(外一篇)
黃東漢 偷渡死難者紀念碑拜祭紀事
阿 陀 越界者訪談錄
國華阿茵 心香一瓣悼親人(兩篇)
兩則官方數據—來自《廣州年鑑》
射殺偷渡者(兩則)
周繼能 一份當年的偷渡地圖
佘傑明 收容雜憶
周繼能 你聽說過「逃港費」嗎?
周繼能 石門訪「古」
佘傑明 我的雙通紅棉大單車
卒友心聲
陳克治 「大圈仔」
陳克治 問過阿媽先
袁家倫 初到...
阿 陀 南中國的知青偷渡潮—廣州培英中學老三屆調查
黃東漢 感慨繫之話「起錨」
陳克治 逃港知青五,一拜祭活動的起源(外一篇)
黃東漢 偷渡死難者紀念碑拜祭紀事
阿 陀 越界者訪談錄
國華阿茵 心香一瓣悼親人(兩篇)
兩則官方數據—來自《廣州年鑑》
射殺偷渡者(兩則)
周繼能 一份當年的偷渡地圖
佘傑明 收容雜憶
周繼能 你聽說過「逃港費」嗎?
周繼能 石門訪「古」
佘傑明 我的雙通紅棉大單車
卒友心聲
陳克治 「大圈仔」
陳克治 問過阿媽先
袁家倫 初到...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