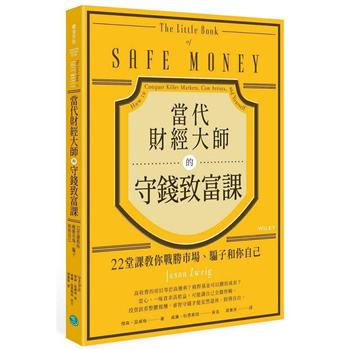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金恆煒
「胰臟癌 • 探戈」,什麼東東?先破題。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探戈發源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文化,也是阿根廷的精神代表,或說是阿根廷的 legacy。阿根廷文學巨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用詩的語言賦予探戈此一舞步的雙重意義:「既是打鬥也是歡慶」。探戈的本身具有雙元的關係;這就是本書使用「探戈」的寓意。
第一支探戈,是我們被迫與胰臟癌周旋、捉對打鬥。結果呢?文翊在《有情世界渡死劫》所說的生死故事,可供癌病患者及家人的療癒之用,此書同時追索我們在媒體的工作,可以當史料看,也可當掌故看。她的文筆含著感情,帶讀者進入我們的悠悠世界,值得一讀。從胰臟癌猝不及防來襲伊始、開刀、化療、電療及復原,然後,不到三年,淋巴癌又不請自來。癌細胞的攻城掠地,一再肆意的以我的身體為殖民地,微弱的身軀只有莫可奈何的承受。胰臟癌即使沒能沒收我的生存權,卻澈底碾壓了我們的生活,正像《世說新語》所說「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病前與病後恍如隔世。
我沒有宗教信仰,不必像基督教徒一樣,有「原罪—救贖」的焦慮,也沒有佛家「業/劫—圓滿無上」的追求;我不能說「看破生死」,但達觀是我的天性,是不是助我渡過劫難?可能。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都認為是奇蹟,也有一位海洋科學家說我們家積了陰德,而且是很大的陰德。我長期不懈為台灣的民主努力奮鬥,即使受到四面八方打擊,我還是一往無前;我得胰臟癌,認識的與素昧平生的都伸出援手,精神上、治療上以及物質上的幫助源源不絕,感激之外還是感激,不禁想起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美德的最好報答就是美德本身。」經過兩次癌病,文翊與我都有不同的生死體驗,內在心靈與外在生活的曲折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講明白;病患的我與病家的文翊各自書寫不同的心靈與身體過程,當然不是醫學研究報告那樣的科學,卻是我們切膚的體驗。面臨生死關頭進而思考我們的走過的來時路。
第二支探戈是我們人生的共舞,從結婚前後到駐美到回台編副刊、辦雜誌,曲曲折折但義無反顧;同一段生活的紀錄,透過兩個人的心眼,展露的是不同的風景。文翊開筆動手先寫,我後來才加入,我們的後半生固然同步而行,回憶錄卻不可能一色,形成雙重奏也必然。文翊寫我們共同的內在世界,我們的家庭、工作以及牽引的朋友及文壇、文化界的交往與現象。我則着力於我們所處的外在世界、外在大環境,尤其側重於戒嚴到解嚴政治體制變遷之下與媒體人我們的碰撞,透過我們親身的經歷,鉤勒白色恐怖的魔爪的無所不在;即使第一民營大報的《中國時報》、高居黨國中常委的報老闆也必須伏首貼耳,何況區區記者、編緝,甚至作者,甚至我們?報社不能蔭庇旗下的工作人員也是當年的常態。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死記」是我與死亡的擦肩,「史記」則是我與歷史的擦肩,從而揭露兩蔣統治的本質,也回答了「誰關了美洲《中時》」的公案,追索那隻「看不見得手」。我以自己的經歷參酌研究後的資料,穿透兩蔣時代的鐵壁,揭示台灣黨國政治力的運作。史學研究者常自誇「發千古之覆」,我的「發覆」,至少有史料佐證,當或不當, 聽憑讀者諸君發落。文翊偏重在我們編「人間」副刊的種種,我則揭出「人間」副刊與《當代》在編輯精神上的內在邏輯,同時也鏤刻七○到九○年代之後的政治、文化界走向與「本土化」的必然。我們兩本書敘述牽手留下的屐痕,從而也彰顯了我們走過以及現還在走的台灣。
第三支探戈就是文翊的書與我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我雖知道有此編排的形式,但要感謝允晨廖志峰社長的提議讓我們有這個嚐試。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的我們,也看以從小局的我們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小題可以大作,大題也可以小作。至於何為「大」以及何為「小」?小大之辯以及正反之分,在哲學上都各有理據;好在這只是兩個人的回憶錄,「我們書寫故我們存在」,如此而已。當然,我們還可以有更多支的「探戈」可表述,比如患者與家人等等,這就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生何嘗不是這樣。
《有情世界渡死劫》與《是「死記」也是「史記」》合為《胰臟癌探戈》,需要一個總序 。文翊是《當代》發行人,是我的頂頭老闆;上司有令,我奉命執筆,欣然接受是為卷首語。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醫療保健 |
$ 300 |
醫學總論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現代散文 |
$ 342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金恆煒
本書是金恆煒、張文翊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也看以從小局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
作者簡介:
張文翊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曾任
中國時報副刊編輯
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
金恆煒
輔仁大學歷史系
曾任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
《當代》總編輯
現任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自由時報》專欄作者
著作
《趙高與浮士德》
《民主內戰的必要》
《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的最後「神話」》
《我的正義法庭》等
章節試閱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金恆煒
「胰臟癌 • 探戈」,什麼東東?先破題。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探戈發源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文化,也是阿根廷的精神代表,或說是阿根廷的 legacy。阿根廷文學巨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用詩的語言賦予探戈此一舞步的雙...
「胰臟癌 • 探戈」,什麼東東?先破題。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探戈發源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文化,也是阿根廷的精神代表,或說是阿根廷的 legacy。阿根廷文學巨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用詩的語言賦予探戈此一舞步的雙...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是「史記」也是「死記」》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前言 :「死記」與「史記」(代序)
痛苦是不能夠回憶紀錄的
從編輯、記者到駐美特派員
駐美四年點滴在心頭
台灣七○年代到八○年代:「兩條路線」之爭、《中國時報》 與我們
接編「人間」副刊:自由主義 vs. 大中國民族主義
副刊 : 抵抗並擊破黨國的武器
創辦《當代》:十年辛苦不尋常
「復刊」再十年:建構台灣學、走向本土化
《當代》顛覆了《當代》
小結:挑戰我們一生中的「不可能的任務」
《有情世界渡死劫》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大禍這樣開...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前言 :「死記」與「史記」(代序)
痛苦是不能夠回憶紀錄的
從編輯、記者到駐美特派員
駐美四年點滴在心頭
台灣七○年代到八○年代:「兩條路線」之爭、《中國時報》 與我們
接編「人間」副刊:自由主義 vs. 大中國民族主義
副刊 : 抵抗並擊破黨國的武器
創辦《當代》:十年辛苦不尋常
「復刊」再十年:建構台灣學、走向本土化
《當代》顛覆了《當代》
小結:挑戰我們一生中的「不可能的任務」
《有情世界渡死劫》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大禍這樣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