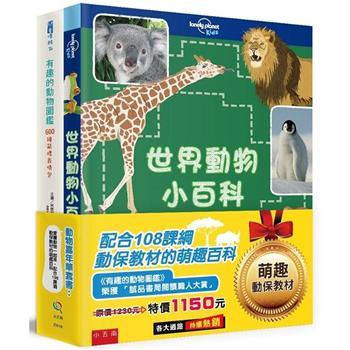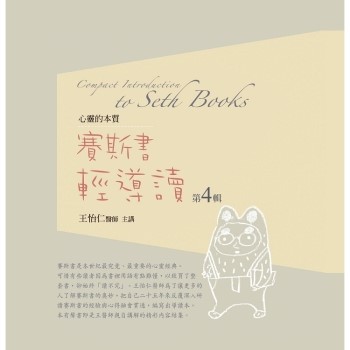海洋書寫作家栗光 全新力作──
探究海,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旅程。
每一次潛水,都召喚著下一次的,再潛一支氣瓶就好。
身處黑暗的人難免被光吸引,
逃避的人終究得面對課題,
有些人在陸上尋找自己,有些人則在海裡──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專文盛讚
張瀞仁Jill(暢銷作家)
楊澤(詩人)
劉家凱(音樂人‧魚丁糸吉他手)
真摯推薦
這本書,無疑是她償還給海的回報──
栗光是誠實的。她寫海,但不強調自己迷戀海。她寫潛水,但不誇大自己如何熱愛這項運動。廖鴻基曾經說,「為著魚是生活,為著海是心情」,若把這句話代換到栗光身上,她的版本顯然是,「為著魚是心情,為著海的部分……還是因為魚」。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說到底,我其實一直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愛我吧?
不論身處何處,總在尋找每份善意的原因,
從不相信自己可以就是那個原因。」
作家栗光繼首部散文集《潛水時不要講話》,再推全新海洋書寫散文集《再潛一支氣瓶就好》。她因為不擅人際而躲藏於水層中,卻在異類的世界裡收下最多同伴的愛。領悟不管是將手伸向他人,還是反握住伸來的手,都不單單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更在互相握持的過程中,納受了自己。潛過一支又一支氣瓶,如今她下水的理由不僅僅為了海洋生物,亦想把在海下尋得的中性浮力,一點一點帶上岸。
無論轉身面向大海或陸地,於她都是一次誕生。
輯一、「當潛季開始」:
海洋生物是她每次下潛的理由,不知道誰會出現,不知道他出現後會做些什麼。栗光觀察那些願意讓人觀察的動物,也在觀察中認識自己與他者。
輯二、「水面休息時間」:
水面休息時間,意指氣瓶與氣瓶間的休息時間,亦是她把頭從水中抬起來,正視夥伴的時候。許多與人有關的故事於此展開,並且不因著那趟潛水結束而畫上句點。
輯三、「回到陸地的潛水員」:
每一次的下潛,最終仍須回到陸地;這不單單是受限於生理,也有著心理層面的需要。海洋滋養日常,家庭與工作的陸地生活,則支持了她每一次的下潛。
作者簡介:
栗光
現任職於聯合報,執編繽紛版。為青輔會「青年壯遊台灣」實踐家、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海洋藝術創作類」得主。作品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曾獲桃園文藝創作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著有《潛水時不要講話》、《再潛一支氣瓶就好》。
粉絲頁|藤壺之志 www.facebook.com/T.cat0713/
章節試閱
【內文節選一】
海中的土匪、洋蔥與我(節錄)
洋蔥是我「看長大」的潛水教練。由於怕生,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終於成為一名會穩定參加店裡活動的潛水員,而在這同期間,洋蔥則正走著教練之路。
第一次相遇在美豔山入水口,我躲在帳篷不起眼的角落,把裝備從網袋裡一一取出,耳邊掃過其他潛水員笑鬧的聲音,心裡則滿是自己的聲音:不要怕,不要熱切地湊上去,只要再撐一下,再一下,等入水了就好了。
「還好嗎?」一名黑黑壯壯的男子把手揮進我的視線。
看上去很親切,不過仍是個陌生人,喉嚨不自覺收緊:「嗯,都好。」是認錯人?為什麼要跟我打招呼?
男子發出一陣乾笑;我想,我一定把心聲滿滿寫在臉上。
對話比氣泡上升速度還快地結束。基於禮貌,我等他完全轉身才收拾視線,卻在對方細微的動作裡,恍然領悟剛剛他是特意關心一個使盡全力隱匿自己的人。我盤算是否要朝還有一絲絲燃燒機會的火苗吹去,可是深吸一口氣,啟脣兩釐,又懷疑自己早已錯失機會,不如再次無聲潛入著裝的動作裡。
剛開始參加活動的夏天,我總是冷,總是在等大家都不說話的水下時光。唯一的例外,是約上一些對潛水感興趣的朋友──通常不是很熟,僅知道彼此為人良善的那種──前去體驗。那時的邏輯是這樣:陌生的潛水圈配上頗為陌生的朋友,恰恰能帶來正面效果,藉著對朋友說明等等會發生的事情,不但能很好地填補對話框的空白,還可以迴避教人倍感不適的團體氛圍。
與洋蔥初識的那天,是我第一次孤身赴會。謹慎記下男子的臉,於事後推理出他正在考或剛考到潛水長,即將成為一名教練。我們之間只有三個字,又好像遠遠超過那三個字,我很清楚自己是被照顧的,但為什麼呢?明明放在那不管也是可以的。
下一次遇見洋蔥,是潛水團春酒,我與後來入坑的好友、店家常客和兼職教練們分到一桌。同桌的洋蔥很快被隔壁桌喝得醉醺醺的老教練纏上,後者滔滔不絕分享自己的經驗,講古百年前;五分鐘過去,十五分鐘過去,三十五分鐘過去,沒有人知道怎麼解救他。最後是一位商場經驗豐富的潛伴出手,先喝兩杯向酒借氣,再對老教練說:「哎呀教練不好意思,換我們弄他了。」老教練呵呵呵地離開,洋蔥坐下,長舒一口氣,掏心掏肺地道謝。自此,我趁亂算上與他有些交情。
接下來我們常在海邊碰到,洋蔥多次帶我朋友體驗潛水。其中,有一位很熟悉野外活動的朋友,大概對他來說一下子跨入不同介質的挑戰太大,所以上岸就像被外星人綁架又放回來那樣眼神空洞、問答遲緩,講什麼都點頭,也都沒有正確回應;水位高時,他急著脫去面鏡,用熟悉的眼光看世界,水位低時,他堅持不脫去蛙鞋,緊捉每秒機會擺脫海洋。洋蔥注意到了,哄他戴好面鏡,請他站定,為他脫去兩腳蛙鞋,應對徐徐如風。
我偷偷觀察這一幕,心裡忍著羨慕。菜鳥時期,最怕岸潛結束過碎浪區,不論浪來時的拍打,或浪去時的抓力,對疲憊的潛水員而言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腿一軟便立刻滑落海中,沒滾三兩圈不會停。剛考到初階執照的第一次潛水,我對海的認識仍停留在海水浴場的程度,想不到水淺之處需要提防。等明白該出多大力氣對抗,人已墜入滾筒洗衣機,耳邊盡是教練氣急敗壞地吼叫:「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那位教練平時很溫和,因此我不是透過環境掌握當下情況的危急,而是經由他的語氣;等他冷靜下來,終於想起憤怒不能解決問題,意識到我不是覺得好玩才滾來滾去。此後,只要過碎浪區,腦中就會響起:「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如果說開車有所謂的車品,潛水可能也有潛品,而洋蔥就是表裡如一的那種。暈船的翌日,我吃了雙倍藥,在海面等大家集合時渾身輕飄飄的,一點也不怕浪。我喜孜孜地衝著洋蔥笑,正舉起相機要記錄,便從漂移的線圈驚覺自己太過急著下水,居然沒有穿好BCD,犯了一名有經驗的潛水員絕不該犯的錯。
臉上還是剛剛的笑容,眼神已轉為驚慌,著急地在身上摸索,「我忘記扣扣帶……」守在一側的洋蔥,忽然用非比尋常的溫和口吻對我說:「妳的BCD有跨帶,我不方便幫妳穿。妳慢慢來,我等妳。」我愣愣地看著他,彷彿被按下暫停鍵,腦海開始回放學過的處理步驟。
跨帶在浮力幫助下脫逃,好不容易捉住了又覺得扣得太鬆,怎麼調整都不滿意。我深知正與眾人共用一份時間,內心好急,也好氣。再度看向洋蔥,投諸懊悔,卻見他用雙手作水槍,朝我迸出噴水池的花樣,像在逗小孩。很奇妙的,這種平常絕對唬不到我的招式,驀地轉移了所有焦慮──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安慰了,當眼前的人對你放心到在玩水槍,還有什麼理由自我懷疑?
警報解除,那趟潛水很順利。問洋蔥怎麼想到這招,他說平時教國小生游泳,算是必備技能,「小孩很難保持專心,要想辦法吸引他們的目光。」我心中浮現初相識的場景,此刻的他,不僅進化到一個眼神、一個臉色,就能掌握其他潛水員需求,還能給予適當回應。
……為什麼要打招呼?明明放在那不管也是可以的。
曾經有過的困惑,跟著那段記憶一塊自沙底翻攪上來。我想,現在我能給出答案:「為什麼不呢?雖然可以不管,但明明也可以管、明明也可以成為朋友。」說到底,我其實一直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愛我吧?
不論身處何處,總在尋找每份善意的原因,從不相信自己可以就是那個原因。我是害怕同類才逃到海裡,卻在異類的世界裡收下最多同類的愛。所有以為的「不得不」,並非源自生理,而在校準心理。接過保溫瓶、遞出自己的手、反握住一雙手、回應他者眼神,不單單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且更需要接受那個需要的自己。
【內文節選二】
海錯圖(節錄)
●鈍額曲毛蟹
鈍額曲毛蟹很醜。
滿身一塊塊的東西看起來很像瘤,第一次相遇是在夜潛時,光一照,他衝得飛快,如一陣襲來的惡意;但是等我冷靜下來,才發現那是在閃躲。人很奇怪,第一眼覺得他毒胞脹滿全身又大又可怕,可一曉得他比我還恐懼,忽然就不怕了。
第二次再看見他,我刻意把光打偏,不想驚擾,只想細細看個分明。我好奇這傢伙究竟是怎麼樣的組成,為什麼東一塊西一塊突起,顏色又衝突得不得了?
那是海綿與海藻,參雜一些碎貝殼與沙礫。
鈍額曲毛蟹習慣把可以取得的材料全往身上放,不動時便能混入周圍環境,以偽裝躲避敵害,也藉著怪模怪樣讓人倒盡胃口。他並沒有我當初想像的那般神奇邪惡,就是很老實地在海裡混一口飯吃,所以也格外不想受到過多關注。
那就是一個生存的模樣,看懂了,便沒有誰很醜了。
●綿蟹
會往身上放裝飾的動物不少,而綿蟹做起這件事來,似乎比誰都有心。
我在潮池碰過他們幾次,指甲片大小,穿著自己精心剪裁的海綿斗篷,有一種綿蟹的挺拔俊朗。儘管外貌看上去都差不多,性子卻很不相同。有些隨浪擺盪,不輕易教人看出真實身分,擁有最高等級的易容術;有些按捺不住,多瞧兩眼便驚得慌,也不管有沒有水流有沒有風,說走就走,移動起來像一塊鬼海綿,萬分可疑;有些則底氣不足,稍感不對勁,立刻斗篷一拋,面具一撕,哪裡有縫哪裡鑽。
在這些綿蟹之中,有一隻特別令我難忘。那時不知怎麼碰掉了他的斗篷,害他在月光下赤裸身子,整隻蟹頓時僵住了。我滿懷歉意地以指尖夾起那外衣,悄然放置他身旁。本來不敢心存希望,沒想到他真的接收到這份心意,下一秒就毫不遲疑地穿回去,緩緩步行離開。
望著他小小的背影,把所有月光都積存在迷你斗篷內裡,我驀地好想喊住那位綿蟹。除了真心誠意地說一句對不起,還有「欸,你衣服穿反了」。
【內文節選一】
海中的土匪、洋蔥與我(節錄)
洋蔥是我「看長大」的潛水教練。由於怕生,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終於成為一名會穩定參加店裡活動的潛水員,而在這同期間,洋蔥則正走著教練之路。
第一次相遇在美豔山入水口,我躲在帳篷不起眼的角落,把裝備從網袋裡一一取出,耳邊掃過其他潛水員笑鬧的聲音,心裡則滿是自己的聲音:不要怕,不要熱切地湊上去,只要再撐一下,再一下,等入水了就好了。
「還好嗎?」一名黑黑壯壯的男子把手揮進我的視線。
看上去很親切,不過仍是個陌生人,喉嚨不自覺收緊:「嗯,都好。」是認錯人?為...
推薦序
【推薦序】
推薦序 背著隱形氣瓶的呼吸與練習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那是二○一○年的三月,我收到一封名為「課程之外的問題」的信,來信的學生署名「譚立安」。她在吳明益老師的課堂上完成了一份以松鼠為主題的壯遊企畫書,在進一步思考執行方式時,卻遇到難解的困惑。我對「譚立安」這名字是有印象的,但其實我們在課堂外並沒有交集。然而那封信立刻打動了我,因為她說:「我希望自己在生命之前可以更謹慎一點。」沒有強調自己多喜歡動物或多想幫助動物,而是誠惶誠恐地斟酌拿捏著敘事的分寸,希望透過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讓更多人去認識松鼠這群城市中的精靈。這份對生命與文字的謹慎態度,在畢業之後延續到職場與寫作中,累積成如今我們看到的栗光。
栗光是誠實的。她寫海,但不強調自己迷戀海。她寫潛水,但不誇大自己如何熱愛這項運動。廖鴻基曾經說,「為著魚是生活,為著海是心情」,若把這句話代換到栗光身上,她的版本顯然是,「為著魚是心情,為著海的部分……還是因為魚」。她說:「我想我並不真的喜歡潛水,我只是喜歡海洋生物。」但她把這份「喜歡」,切切實實地轉化為生活的實踐和反思,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栗光細膩的心思,在前作《潛水時不要講話》已俯拾即是。她在下潛的過程中,以每一支氣瓶換取一個新課題:學習何時該放棄;學習信任與錯過;體會動物有時並不願意「交出牠們的眼睛」給鏡頭,或有時僅僅是因為,自己有一對太過遲鈍的眼睛……她在水底學習和魚在同一介質中呼吸,重新拿捏人與海、人與魚的距離。《再潛一支氣瓶就好》延續著這些有關潛水體驗與海洋生物的主題,卻又比前作潛得更深。
書中有關海的篇章,都能看出隨著浸潤在海洋的時日愈久,她的種種反思也愈趨細緻。她不再如同剛開始潛水時,執著於立刻尋求解答,總是急著將拍到的生物按圖索驥、上網求解,務求能一一指認牠們的名字。相反地,她丟出更多問題,並且容許這些問題沉澱在心裡。當她被宛如銀龍的白帶魚震懾,她自覺未來在餐桌上遇到白帶魚時,眼光必然不同;她也反省每一次的踩踏,都是對海洋生物的擾動,自己如何與為何能擁有這樣「蠻橫的力量」去介入海洋?我尤其喜歡她在〈跑掉的顏色〉一篇中的思索,在水下攝影課試圖將照片調整成「更接近珊瑚的顏色」時,她納悶著到底哪個版本才更接近「真實」?是在海中受限於自己的生理構造所感受到的顏色,還是上岸後用各種設備「補回來」的顏色?一如水滴魚之所以被形容為「如同鼻涕般醜陋」,是因為被撈捕上岸的牠,處在非日常的深度,但若我們能潛抵水滴魚的深度,「水滴魚看起來就是水滴魚」。我們用影像所留住的,永遠不會是海洋真正的顏色,而是用自己有限的視野,去想像出的「更接近海的顏色」。
栗光對海的顏色的思考,讓我想起約翰•葛林(John Green)在《人類事評論》中,對人們為了保護真正的拉斯科洞穴藝術而仿造的洞穴壁畫之評論。他說,「你會知道,這些畫作不是原物本身,而是影子。這是手印,但不是手。這是你無法重返的回憶。對我而言,這使得這座洞穴更像它所代表的過去。」某程度上,每一張海洋照片也都只是海洋的仿作與影子,是無法重返與重現的回憶。每一次的「截圖」聚焦,都只是更加揭示出圖象背後的無窮與深邃。探究海,是一場以有涯追無涯的,不會有終點的旅程。於是每一次的潛水,也都召喚著下一次的,「再潛一支氣瓶就好」。
而除了魚與海,這一次,栗光更順著洋流潛回自己的生命經驗,挖掘那擱淺在深處的記憶化石。某程度上來說,《再潛一支氣瓶就好》中這些「陸地上」的篇章,反而更能看出潛水或說海洋經驗對於栗光的影響。如同她在〈代序〉中回顧的,「把在陸地長成的身體帶到海裡」,才恍然當初對諮商師一句「敏感」的評語耿耿於懷的自己,確實是敏感的。但此刻,「敏感」對她而言不再是一個隱微帶有貶義的平板形容,而是一次又一次「再多發現一點」的過程。她發現過去如何將自己裹在有如「鸚哥魚夜寢的黏液繭」裡,拒絕愛、拒絕被幫助。海洋某程度上,逼她把自己交出來,繼而將這些一瓶瓶氣瓶換來的經驗帶回岸上,背著隱形的氣瓶,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練習。
於是,在編輯台上,她反思過去對投稿者的嚴苛要求,「人家就是寫了抒發,我強授蛙踢一百式,不就只是讓人家連踢都不想踢了呢?」;在面對無理又無禮的投稿電話時,她以鹽酸(刷洗化石)安頓身心;更重要的是,她開始謹慎下潛,宛如試探耳壓般地試探心理壓力可及的深度,碰觸父親與父親離開的記憶,讓收拾舊居揚起的灰塵宛如海底揚沙,去接納記憶也可能因塵沙的飛揚而顯得益發模糊混亂,但也唯有經歷這樣的過程,來路方能在「模糊之後,又清晰起來」。這是海洋的贈禮,而栗光並不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她說,「多情的人潛水,攪動了海,將以心償還」,這本書,無疑是她償還給海的回報。
【代序】
代序 兩種不說話的時光
「我注意到妳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她前傾的身子窩回了沙發。「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我抬頭,重複她的話,「除了帶來痛苦還有什麼?」十分不解裡藏著一分怒氣。
她疑惑地回望我,「這樣妳就能比一般人更注意到他者的情緒了呀。」表情好像「老師」,好像「大人」,好像「不然,妳希望怎麼樣呢」,好像我這麼大了卻還這麼不懂事。
結束那場不同頻率的對話,腦子轟隆隆地堵住了嘴巴。心底第一次冒出強烈的不甘,原來敏感就必須體察他人?那如果我想當的是一個被體察的人呢?
離開那個房間後,沒有再去過類似的空間,成長被敏感追得跌跌撞撞,但終究長大,並且在長大的過程裡逐漸對自己的敏感死心。死心後的很多天,三百六十五天,七百三十天,一千零九十五天……我在潛水的某一刻,驀地想起那段對話,想起那位面目模糊的心理師。
〇
第一次接觸潛水我就喜歡上它了,喜歡它沒有非得抵達的地方,沒有非得追求的速度,沒有頻繁的互動,只有一段長長的、靜靜的時光。不同於多數運動講求合作,身為一名休閒潛水員,實踐基礎的安全規範後,我給自己的初期目標,唯有「好好呼吸」一項。教練一再提醒,規律呼吸,切勿閉氣,以免水壓傷害了肺部。等「學會呼吸」,教練進一步以五指並攏、來回撥拂的手勢,提醒呼吸之外,頻率穩定也相當重要;新手常在緊張時過度吸吐,甚至緊張得無法覺察正在緊張。呼吸在海下如此重要,重要得幾乎簡化了一切,讓我不知不覺放下所有不必要的自我叮囑,放下我以為必須一直回應的外界。
我曾以為潛水就是這樣了,它是一件「讓活著變簡單」的事。但,當我想要在那樣的環境中更自在,「好好呼吸」就變了,像嬰兒誕生那一刻的哭泣,人人為之歡喜,可哭泣以後的時時刻刻,卻滿是困難。我得從走路開始學,從穿衣開始學,從一切我在陸地上覺得好簡單的事情開始學,既無法在誰面前逞能,也難以偷偷練習。自成為一名成年人、大學畢業、進入社會,幾乎沒有這樣狼狽過。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遇到的關卡,是把全部裝備安放於身。相較上手快的人,我對那些又黑又重的東西充滿陌生恐懼,弄不清名稱與步驟順序,想到它們與自己的性命攸關,還沒下水便有幾分驚慌。
後來我能喊出「大家」的名字,知道哪時候派誰上場,誰能助我完成什麼動作,偏偏行動趕不上心意,浮力於活在重力的我實在太陌生。教練觀察後,要我到旁邊踢一個小時的蛙踢,一小時,再一小時,因為在那個世界裡,我是不會走路的孩子。我喜歡用手划,會厚著臉皮說:「老天給我雙手是有道理的。」但潛水員拚命划是沒有道理的,所有資深潛水員都是用腳踢,一次蛙踢出去,順流向前,不慌不忙,只有我手足並用,前進有限,白白耗氣──潛水是運動,但這運動講究該動時動、該停時停,所以手划、過分腳踢,都是多餘的,浪費氣瓶裡的空氣,必須壓抑。
完成一趟潛水後,我依舊是不會走路的孩子。船潛時,我暈船,吐得要死;岸潛時,我過碎浪區,磕磕碰碰。我試著獨自擔下一切,未曾想過求救,直到別人幫了我一把,我道謝,一次又一次。道謝不可恥,需要幫助其實也不可恥,可我實在長得太大了,大得就快要相信自己天生不應該求助。比起求助,更擅長勉強自己,全然忘記誕生於世時,曾經那麼理直氣壯地哭泣,依舊被眾人們祝福。原來人長到一個年歲,會完全遺忘求助的模樣,不管在工作還是生活,全部一口吞下。
把在陸地長成的身體帶到海裡,吞的就是嗆入口鼻的海水,鹹得教人想起最後一次踏進諮商室,那位此生僅僅交集一小時的心理師,想起她說:我注意到妳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啊,竟是這個我千方百計欲從人格特質中割去的字眼,帶領自己一遍遍潛進情緒裡。通過敏感,我才曉得自己對於需要幫助懷抱罪惡感。通過敏感,我多餘地反覆地檢驗他者的舉動,學會比多心還要多心,擁有一層如鸚哥魚夜寢的黏液繭,在感覺受傷之前閃避慣性過度解讀的陷阱,也盡量拆除自己話語中的陷阱。
一千零九十五天後的一千零九十五天,潛了好多次好多次以後,我在陌生的潛水船上,聽見身旁女孩的氣瓶發出嘶嘶聲響。嘈雜中,我請教練為她做確認。女孩一邊等待,一邊問我,妳潛很久了是嗎?看起來好資深。我笑笑,坦白自己很緊張。她露出甜甜笑容,「可是,妳看起來很鎮定啊。」
「每一次,我都很緊張。」我鎮定的時候,就是緊張的時候。我必須全神貫注,才能勉強相信自己可以應付眼前的狀況。
那趟潛水結束,她的氣瓶沒有問題,但人暈船了。「妳要話梅嗎?」我問,她點點頭,接過我遞去的那包救命果和水。我們不再交談,一起看向遠遠的地方,那是潛水世界裡,另一種不說話的時光。原來,我兩種都喜歡,想在能力所及時,成為船上那樣看似寧靜的角色。
好好笑,那曾是我最不稀罕的溫柔,發現的時候,卻已經「敬重」能夠付出的自己;好好笑,能成為那樣的自己,源於過於細緻的沿路風景,看遍路上的蟲魚鳥獸,便能為陌生人指認。
【推薦序】
推薦序 背著隱形氣瓶的呼吸與練習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那是二○一○年的三月,我收到一封名為「課程之外的問題」的信,來信的學生署名「譚立安」。她在吳明益老師的課堂上完成了一份以松鼠為主題的壯遊企畫書,在進一步思考執行方式時,卻遇到難解的困惑。我對「譚立安」這名字是有印象的,但其實我們在課堂外並沒有交集。然而那封信立刻打動了我,因為她說:「我希望自己在生命之前可以更謹慎一點。」沒有強調自己多喜歡動物或多想幫助動物,而是誠惶誠恐地斟酌拿捏著敘事的分寸,希望透過自己微不足道...
目錄
【目次】
推薦序 背著隱形氣瓶的呼吸與練習◎黃宗潔
代序 兩種不說話的時光
輯一、當潛季開始
一切都從比基尼開始
海洋速寫
光下的異獸
深海無光帶
拿捏和你的距離
小醜人
海錯圖
當我們在水下生火
跑掉的顏色
輯二、水面休息時間
又是浪來了
海中的土匪、洋蔥與我
那些被我折騰的潛水教練
海陸護身術
頂尖中性浮力
完美倒踢
海下煙花
通往海的路上
欸,我們再來做一次耳壓平衡
迷失與逆向
輯三、回到陸地的潛水員
譚小姐
你好,平行時空
我的澳洲奶粉喪屍歲月
人在世上最大的敵人
離開編輯台後,我如何以鹽酸照顧身心
看一隻貓長大
逞英雄
水晶鈴鐺
咬人貓
家庭馬賽克
【目次】
推薦序 背著隱形氣瓶的呼吸與練習◎黃宗潔
代序 兩種不說話的時光
輯一、當潛季開始
一切都從比基尼開始
海洋速寫
光下的異獸
深海無光帶
拿捏和你的距離
小醜人
海錯圖
當我們在水下生火
跑掉的顏色
輯二、水面休息時間
又是浪來了
海中的土匪、洋蔥與我
那些被我折騰的潛水教練
海陸護身術
頂尖中性浮力
完美倒踢
海下煙花
通往海的路上
欸,我們再來做一次耳壓平衡
迷失與逆向
輯三、回到陸地的潛水員
譚小姐
你好,平行時空
我的澳洲奶粉喪屍歲月
人在世上最大的敵人
離開編輯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