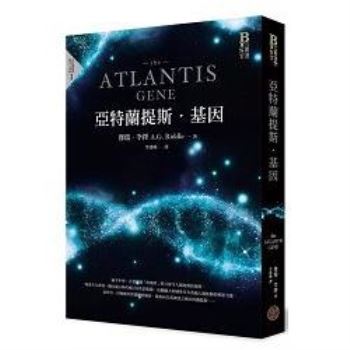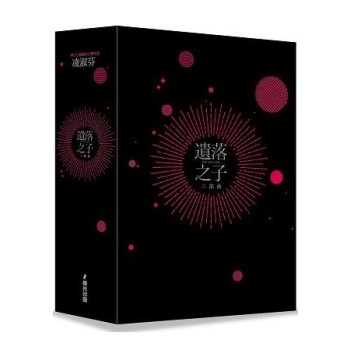一段愛情、欲望、夢想糾葛,撼動人心的炙熱旅程!
為了活出想要的人生,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直面禁忌.引爆國際熱議之作.隆重登場
丹麥二十世紀最重要獨特的女性之聲,首部直譯中文版領先全球上市
國民作家成長文學經典,已售全球25國版權,颳起托芙潮旋風首部曲《童年》榮獲誠品X博客來X金石堂X香港誠品當月選書
|後摺口附贈哥本哈根三部曲浪漫書籤,一式兩張可自行裁剪|
即使明知災難性的結局在等待,我都忍不住想要像她那樣活。
──鴻鴻(詩人)
★2021時代雜誌年度選書
★2021紐約時報年度選書
★2021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年度選書
★2021金融時報年度選書
紐約時報★衛報★紐約客★每日電訊報★波士頓環球報★華爾街日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觀察家報★每日郵報★電訊報★金融時報★新政治家★出版人周刊★巴黎評論★洛杉磯時報★書單——國際媒體共同推薦
★全球最大書評網站Goodreads著作累積近三萬則討論分享
★媒體譽為女性版《我的奮鬥》,丹麥版《那不勒斯四部曲》
★丹麥影視團隊改編拍攝影集中
「現在,我們是爸爸、媽媽,有了孩子,就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家庭。」
「為什麼,妳那麼想當一個正常的普通人?事實上,妳並不是啊。」
我無法回答他,但是,打從我有記憶以來,總是有著這樣的渴望。
──托芙.迪特萊弗森
來自丹麥的傳奇女作家托芙,近年以哥本哈根三部曲在國際間掀起熱潮。《毒藥》是真正點燃銷售狂潮的關鍵之作。她在書裡記錄下的歷程,也是當代女性的獨特聲音。被譽為自傳式寫作的先驅,筆下題材多取自真實體驗,哥本哈根三部曲引起的爭議尤甚。她曾在訪談說自己的創作皆是虛構,但在哥本哈根三部曲的第一人稱書寫當中,我們確實透過小說般的情節,窺見一位當代女作家的憂傷身影。
終曲《毒藥》的結局,托芙留下了開放式的伏筆,現實生活的她卻嘗試數次自殺,在本書出版五年後殞命——這是她最後,沒有告訴讀者的事,也讓書中對生命的提問更加真實。《毒藥》是哥本哈根三部曲的引爆點,在丹麥出版後點燃了銷售狂潮,虛實間的爭議也隨之而來。親友紛紛出面抗議,責備她「與生活太近」,她在書中卻自承「寫作時,我絕不為他人著想」。
★直面人性的解謎之作
繼《童年》裡回望原生家庭,《青春》描述繽紛多姿的年少階段,《毒藥》終於將讀者帶進了真正與現實對抗的生活。身為詩人,托芙為本書命名選用了別有寓意的雙關語。在丹麥語中,「已婚」這個字亦有「毒藥」之意。她在本書裡坦率且驚人地揭露了自己的生活,直面人性裡種種考驗:家庭、愛情、欲望、創作、藥物——最後成癮。
《毒藥》的開場裡,年輕的托芙儼然已經年少得志,嘗到了成功的滋味。她的著作陸續出版,另一半正是挖掘她出道的總編輯,人生幾乎一如所願。但是生命的考驗總是突如其來:寫作事業的成功蒙上利用年長丈夫的陰影。面對感情波折後,與第二任年輕丈夫的婚姻讓她體會了為人母的快樂,也得面對產後憂鬱症及家庭生活等問題,同時繼續為寫作燃燒。
★驚心動魄的真實生活
隨著歲月流逝,她的生活核心逐漸演變成為痛苦的來源:她想要愛情、想要家庭、想要孩子、更要創作。她在書中描述了女性兼顧多重角色的艱難:為了保住愛情與創作,她甚至選擇墮胎。擔任醫生的第三任丈夫讓她陷入成癮之苦,她沉浸在迷幻感帶來的靈思泉湧及創作欲裡,無法自拔。她在書中記錄了成癮及戒斷的過程,驚心動魄,幾乎讓人不忍直視。第四任丈夫則伴她走向光明,展開另一段人生。
她曾在書裡寫到,寫作是唯一令她感到快樂與平靜的事。她將自己生命裡的疑惑、苦痛、掙扎、快樂,誠實坦率地訴諸筆下。全書真實描繪了一個女人經歷愛情、友誼、野心和成癮的灼熱旅程。
★充滿既視感的當代文學經典
托芙.迪特萊弗森是丹麥的國寶級作家,《童年》《青春》《毒藥》分別詮釋一位女性的童年、青年、婚姻階段,可獨立亦可串連,被譽為哥本哈根三部曲,並公認為經典代表作。三部曲的主題圍繞在女性的經歷和生活,對複雜的女性友誼、家庭和成長世界的描繪動人而出色。
對於創作及實踐自我的熱情,點燃了她的靈魂與生命,一路支撐著她走向人生終點,也為她奠定了傳世作家的地位。三部曲即便只是屬於作家的人生故事,多年後卻仍能在國際間蔚為風潮,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也有濃厚既視感,毫無時空隔閡。
作者簡介:
托芙.迪特萊弗森(Tove Ditlevsen)
出生於一九一七年,丹麥知名詩人、作家,作品常見於丹麥音樂與電影,亦被選入丹麥小學教材中。出生於哥本哈根的工人階級家庭,童年經歷成為她作品的重心。二十出頭便出版首部詩集,一生著作近三十本,包括短篇及長篇小說、詩歌與回憶錄。女性身分、記憶、童年是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勇於書寫自己的憂傷和痛苦,刻劃人性最深處的禁忌及掙扎。曾獲丹麥文壇最高榮耀金桂冠文學獎(De Gyldne Laurbær)等多種獎項肯定。成年後,反覆與酒精、毒癮對抗,多次進出精神病院,這些經歷則成為她晚期作品的重心。一生經歷四段婚姻,於一九七六年服用過量安眠藥身亡。
她在去世前就已深受丹麥人喜愛,卻直到近年哥本哈根三部曲於國際間出版才引爆全球「托芙潮」(Tove fever),各家媒體大幅報導,更被文學評論家稱為「世界遺忘的珍寶」。由於作品皆帶著強烈的個人自傳色彩,也被視為自傳式寫作的先驅。作品《童年的街》(Barndommens Gade,暫譯)曾被改編為電影,《童年》《青春》《毒藥》則是首度被引進華文世界的經典代表作。
譯者簡介:
吳岫穎
馬來西亞華人,出生於馬來西亞馬六甲州,在馬來西亞完成基礎教育及二專。1999年畢業於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2001年隨丹麥籍先生移居丹麥。2009年畢業於哥本哈根Gladesaxe幼教學院。目前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托育機構任職。曾在大馬華文報章撰寫專欄。2008年出版《丹麥,生活旅行》,另有譯作《惡童》(Intet)。
章節試閱
第一部
1·
客廳裡的一切都是綠色的——綠色的牆、綠色的地毯、綠色的窗簾,而我總是身在其中,如畫一般。每天清晨五點左右,我醒來,坐在床緣書寫著,寒意讓我不禁蜷縮著腳趾;時值五月中旬,暖氣已經關了。我獨自睡在客廳,因為維果.F.莫勒爾(Viggo F. Møller)獨居多年,一時間無法習慣身旁睡著另一個人。我理解,也覺得完全沒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清晨的時間就完完全全只屬於我了。我正寫著我的第一部小說,而維果.F並不知情。我有預感,如果他知道了,絕對會給我許多的意見和指正,正如他對待為《野麥子》(Hvid Hvede)撰稿的那些年輕人一樣。如此一來,一整天在我腦海裡蠢蠢欲動的句子都會被截斷。我在廉價的黃色草稿紙上書寫,因為如果我使用他那台聒噪的打字機來打字——那台古舊,應當屬於國家博物館展覽品的打字機,絕對會吵醒他。他睡在面朝後院的臥房裡,早上八點鐘才需要叫醒他。他起床後會穿著白色繡紅邊的睡衣,擺著一張令人厭惡的臉,去洗手間。我開始泡咖啡,在四片麵包上塗抹奶油。我會在其中兩片麵包塗著厚厚一層奶油,因為他喜歡一切油膩的事物。我盡我所能逗他歡喜,因為我始終對他充滿感激之心:他娶了我。我知道這一切都有點不對勁,然而我還是小心翼翼地不進一步去思考這件事。維果.F從來不曾用手挽過我,這讓我有些不舒服,就像鞋子裡藏著一顆石頭那樣。我感到不自在,認為問題出在自己,或許我在某種程度上,沒有達到他的期望。當我們面對面坐著喝咖啡時,他讀報,也不允許我和他說話。而我的勇氣,開始如沙漏裡的沙子一般,莫名地流瀉。我瞪著他,看著他的雙下巴如何從襯衫的衣領邊際漫溢出來,並且持微微震動。我望著他纖小的雙手如何急促、焦慮地擺動;以及他那一頭厚重得宛如假髮般的灰髮,因為他那張紅潤、毫無皺紋的臉,比較像是一個禿子。當我們終於展開對話時,卻常是討論他晚餐想吃什麼或我們該如何縫補遮陽窗簾裂縫等,無關痛癢的瑣事。只有他在報紙找到一些讓人振奮的消息,我才會覺得高興,例如那天新聞報導占領軍在禁止酒精交易一星期後終於解禁、我們能再次購買酒精飲料的時候。當他張開只剩下一顆牙的嘴巴對我微笑、出門時拍拍我的手說再見的時候,我也會覺得高興。他不想裝假牙。他說,他家族裡的男人們都只能活到五十六歲,所以他大約只剩下三年的壽命,何必花這筆錢。他的小氣過於明顯,我的母親當時對他維持生計能力的高評價,完全是錯估了。他從來沒有送過我一件衣服。當我們傍晚出門拜訪一些名流時,他搭乘電車,我則騎著腳踏車以極快的速度與電車平行,好讓他想要看見我的時候能在車外向他揮手。他讓我負責家裡的開銷預算,當他查看時卻認為每樣東西都太貴。帳目無法平衡時,我就會寫上「綜合開銷」,這會讓他非常生氣,因此我總是小心翼翼地不忽視任何一項開銷。他也總是抱怨我請傭人來家裡幫忙,認為我反正在家也無所事事。但是我不能也不願意處理家務,這點他不得不讓步。當我看見他越過一片綠色草坪,前往停在警察局外的電車時,我也會覺得高興。我向他揮揮手,轉身背向窗子,便把他徹底遺忘了,直到他再次出現為止。我淋浴,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心想,我才不過二十歲,但是我們彷彿已經結了一輩子的婚。我才二十歲,而我覺得在這綠色客廳以外的人們都過著疾速奔馳的人生,就如定音鼓和鼓的聲響般急促;與此同時,日子卻如塵埃般不知不覺地掉落在我身上,日日重複著。
穿好衣服,我跟顏森(Fru Jensen)太太討論晚餐,並擬了一張購物單。顏森太太沉默寡言,個性內向,她覺得有點委屈,因為她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單獨待在這裡。「算了,」她喃喃自語,「這把年紀的男人居然娶了一個年輕女孩。」她聲量很小,我無需回她,而且我也不能被她干擾。因為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我的小說,我已經擬了題目,但還不知道這將會是怎樣的一部作品。我只是寫,或許這將是一部好小說,或許不是。最重要的是,書寫的時候,我感到快樂,這是我一向以來的感覺。我感到快樂,並且遺忘了周遭的一切,直到我提起褐色的斜肩包出外逛街為止。當我走在街上,就會再次陷入早晨的愁雲慘霧,因為我眼裡只看見那一對對陷入愛河中的情侶們,手牽著手,互相凝視彼此。我幾乎無法承受這樣的畫面。我明白了,原來我至今根本不曾戀愛過,除了兩年前,那一天,我從奧林匹亞(Olympia)酒吧裡把柯特(Kurt)帶回家。隔天他就出發去西班牙參加內戰。或許他已經戰亡沙場,或許他平安歸來,娶了一個女孩。或許我根本沒有必要為了達到任何成就而和維果.F結婚。或許嫁給他,僅僅因為母親熱切的期待。我把手指插入肉裡,看看肉是否軟嫩,母親是這樣教我的。我將價錢寫在小紙條上,否則回到家,我就會忘了。當採買結束,顏森太太回家後,我再次遺忘一切,敲著打字機,此刻,不會打擾任何人。
母親經常來看我,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會做些蠢事。婚後幾天,母親打開衣櫃,一一翻看維果.F的衣物。她叫他「維果兒」,和其他人一樣,沒辦法僅僅稱呼他「維果」。我也沒辦法,因為這名字感覺就像是一個孩子的名字,用在成年男子身上顯得有點蠢。她把他所有的綠色衣物對著光線查看,找到一套已經相當破爛的,她覺得他不會再穿了,建議拿去讓布朗太太(Fru Brun)改成一條洋裝給她。當母親做出這種決定,我從來沒能動搖過她,於是我毫無反抗,讓她帶著衣服離開,只希望維果.F不會提起這件衣服。過了一陣子,我們去拜訪父母。我們不太常這樣做,因為我無法忍受維果.F對我父母說話的方式。他拉大嗓子,緩慢地說話,彷彿面對的是無能的小孩,他小心翼翼地製造一些他認為能引起他們興趣的話題。我們去拜訪他們時,他忽然間悄悄用手肘戳了我一下。「這太怪了,」他說,同時用大拇指和食指捻弄著鬍子,「妳有沒有發現,妳媽身上那條裙子,布料跟我掛在我們家櫃子裡的那套衣服一模一樣?」於是我和母親快速地躲到廚房裡大笑。
這段時期,我覺得我和母親非常要好。對她,我不再有深切痛苦的情感。她比她女婿年輕兩歲,他們兩人之間的話題僅限於我的童年。當母親提起她記憶中兒時的我,我完全沒有任何印象,彷彿她說的是另一個小孩。母親來的時候,我會把小說藏在維果.F書桌屬於我的抽屜裡,鎖好。我泡好咖啡,和她邊喝著咖啡邊悠閒地聊著天。我們聊著父親終於在奧雷斯塔德發電廠(Ørstedsværket)找到穩定工作的好消息。我們說起艾特文(Edvin)的咳嗽,我們也聊到自從羅莎莉亞(Rosalia)阿姨過世後,母親內臟開始發出的各種緊急訊號。我覺得母親還是非常漂亮與年輕的。她嬌小苗條,臉龐和維果.F一樣,幾乎沒有任何皺紋。她那一頭燙過的頭髮濃密得猶如洋娃娃。她總是端正地坐在椅子的邊緣,挺直著背,雙手放在手提包的提把上。她和羅莎莉亞阿姨一樣,總是正襟危坐,打算只逗留「片刻」,卻在幾個小時以後才離開。母親會在維果.F從任職的保險公司回家前離開,因為他總是心情很差,不希望家裡有其他人。他厭惡自己的辦公室工作,他討厭每日圍繞在他身邊的人。我覺得,除了藝術家以外,基本上,他討厭全人類。
用餐完畢,我們會審查家裡的開銷帳目,接著,他會問我《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讀到哪裡了。他要求我打好藝術文化的知識基礎,所以我盡量每天都讀幾頁新的內容。當我把盤子都端去廚房時,他會躺在長沙發上小憩,我看了一眼警察局前那顆藍色地球儀,以耀眼的玻璃光映照著空蕩的廣場。我把窗簾拉下,坐下來閱讀卡萊爾(Carlyle),直到維果.F醒來跟我要咖啡。當我們喝著咖啡的時候,如果當天不必出門拜訪任何名流,便會有一股莫名的沉默在我們兩人間蔓延開來。彷彿我們已在婚前說盡了所有的話語,以光的速度用盡了接下來二十五年可以和對方說的所有詞句;因為我不相信他三年後就會死去。我滿腦子都是我的小說創作,所以如果不談論這個,也不知道還可以跟他說些什麼。
約一個月前,丹麥被德國占領之後,維果.F相當害怕,他認為德國人會逮捕他,因為他曾經在《社會民主報》(Social-Demokraten)的專欄撰寫有關集中營的文章。我們經常討論這個可能性。傍晚,他那群跟他同樣驚慌的朋友過來,他們心裡多少有點類似的擔憂。但是目前看起來他們好像忘了這回事,因為什麼事都沒發生。我每天都在擔心他會問我是否已經讀了他新小說的初稿,他打算將初稿投給金谷出版社(Gyldendal)。初稿就擱在他的書桌上,我曾試著閱讀,但是那實在是太無趣、太冗長了,句子結構都非常拗口以及充滿錯誤,我覺得自己應該沒辦法讀完。這件事導致我們之間的氣氛更緊張,我不喜歡他的作品。雖然我從未大聲說出來,但是我也從來沒有給予他任何好評。我只說,我對文學懂得不多。
儘管我們的傍晚是如此悲哀單調,也勝過那些和名流們耗在一起的傍晚。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被羞澀感和尷尬所籠罩。我的嘴裡彷彿塞滿木屑,無法迅速回應他們所有歡快的話語。他們談論著彼此的畫作、展覽以及出版的書,並高聲朗誦他們新寫的詩。對我來說,寫作就像童年時做過的一些祕密的、被禁止的事,是一件充滿羞恥,必須躲到角落、在沒人看見時才做的事。他們問我近來在寫些什麼,我回答說:沒有。維果.F替我解圍。他說,「她最近在專心閱讀。一定要非常大量地閱讀,之後才能書寫散文,這會是下一步。」他談起我的模樣彷彿我的人並不在現場,而當我們終於可以離開,我才高興了起來。和名流們在一起的時候,維果.F完全是另一個人,他開朗、自信、機智,就像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那樣。
一個晚上,在畫家阿爾訥.翁爾曼(Arne Ungermann)家裡,他們提起應該把那些在《野麥子》上發表文章的年輕人召集起來,他們散布在哥本哈根城裡的各個角落,肯定都非常寂寞。「如果能夠互相認識,一定會給他們帶來歡樂。而托芙可以當這個協會的主席。」維果.F說,然後給我一個友善的微笑。這想法讓我覺得快樂,我只有在少數年輕人帶著作品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同齡人,而他們幾乎都不敢看我,因為我嫁給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男人。這樣的快樂讓我忽然間敢說些什麼,所以我說可以把這個聚會叫做「青年藝術家俱樂部」(Unge kunstneres klub)。這個點子引起了大家的掌聲。
隔天,我在維果.F的筆記本上找到了所有人的地址,寫了一封非常正式的信給他們,我簡要地在信中建議大家在不久後的某個晚上來我們家聚聚。當我把信件都投入警察局旁的郵箱裡時,想像著他們會有多高興,我相信他們和不久之前的我一樣,貧窮而寂寞,並且孤獨地坐在城裡各個角落租來的寒冷公寓裡。我想,維果.F對我畢竟是相當了解的。他知道我厭倦了總是被老年人圍繞著。他知道,在他那綠色客廳裡的生活經常讓我感到窒息,而我也無法耗盡青春去閱讀法國大革命。
第一部
1·
客廳裡的一切都是綠色的——綠色的牆、綠色的地毯、綠色的窗簾,而我總是身在其中,如畫一般。每天清晨五點左右,我醒來,坐在床緣書寫著,寒意讓我不禁蜷縮著腳趾;時值五月中旬,暖氣已經關了。我獨自睡在客廳,因為維果.F.莫勒爾(Viggo F. Møller)獨居多年,一時間無法習慣身旁睡著另一個人。我理解,也覺得完全沒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清晨的時間就完完全全只屬於我了。我正寫著我的第一部小說,而維果.F並不知情。我有預感,如果他知道了,絕對會給我許多的意見和指正,正如他對待為《野麥子》(Hvid Hvede)撰稿的...
推薦序
{特別收錄}【寫作是唯一永恆的愛與動力】
——黛.普蘭貝克(Dy Plambeck)
我認為,《毒藥》是托芙.迪特萊弗森的主要代表作品。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一位優秀的作家面貌:她肆無忌憚卻又脆弱,幽默卻也殘酷,坦率且充滿了愛。在《毒藥》中,作為一個小女孩和一位堅韌的獨立女性,托芙.迪特萊弗森抵達了創作高峰。對於成癮、墮胎、不必要的耳疾手術以及對婚姻的不忠,托芙.迪特萊弗森那種坦率、輕佻的輕描淡寫,在讓人驚訝之餘,同時也讓人感受到她其實傷痕累累,甚至能感受到針頭是如何刺入她的體內、刺入所有男人、女人,以及托芙.迪特萊弗森極度渴望卻又無法忍受的人生。
有一種作家,其人生和作品是融為一體的,托芙.迪特萊弗森便是這類作家的代表人物。《毒藥》是回憶錄。這本書在一九七一出版時,所引發的傳聞及媒體熱議,也連帶讓本掀起銷售熱潮。這本回憶錄也激起了托芙.迪特萊弗森的兩位前夫——艾博.蒙克(Ebbe Munck )及卡爾.里伯(Carl Ryberg)——家人的強烈抗議。但是這類事情,托芙.迪特萊弗森已經習慣了。在她整個寫作生涯中,她經常被家人或朋友責備,覺得她和他們的生活「靠得太近」。「寫作時,我絕不為他人著想」,《毒藥》裡那一個無名的主人翁這樣說,這,也是托芙.迪特萊弗森所秉持的寫作原則。
《毒藥》寫的僅僅是托芙.迪特萊弗森自己的人生嗎?或許並不完全如此。「一切都是杜撰的,包括報導文學」,托芙.迪特萊弗森曾在一次訪問中這樣說。這本回憶錄,其實也是一個普通人的故事,關於一個女人如何被男人、藥物及寫作而分裂的故事。
當我閱讀《毒藥》時,我無法理解現代主義的批評,他們認為托芙.迪特萊弗森的寫作方式並不成熟,過於老派。但是在出版四十年後(本篇文章完成日期為二〇一二年)的今天,無論是本書的主題——對於基本生存條件面臨分裂的描寫,本書的衝突——關於事業與家庭如何結合的描述,還有本書的寫作風格,都是如此當代且合乎時宜。對於讀者來說,《毒藥》不是一本七十年代的懺悔文學,而是類似後現代主義之後盛行的表演舞台:一部帶著面具和身分、涵括真相和語言圖像的戲劇。
同時,《毒藥》也是以一種巨大的勇氣而完成,我不曾在任何其他文學作品裡有過類似的體驗——從本書的第一頁開始,便以極高的說服力緊緊吸引讀者。那是文學的力量,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會讓我們忘了作品的虛構性,忘了書中的角色是出於杜撰。《毒藥》便是這樣一部作品。那些以為托芙.迪特萊弗森僅僅是為了女性而書寫關於女性課題的男人,應該都從這本書開始閱讀。當主角描寫到她的手臂再也找不到任何沒有阻塞的血管,因此只能在腳上尋找時,讀到這個段落卻不為此感到反感的人——無論男人或女人,我都想見見。這段描繪雖然讓人震驚,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肯定了人生。
本書的書名有三層意義。描寫了一個女人的婚姻——一段正常的婚姻關係、書中讓主角上癮的針筒裡的毒藥及婚姻裡的寫作。這三種元素都有致命的危險。
《毒藥》描寫了一個女人同時身為母親及職業女性所面臨的分裂、她對正常人生幸福的渴望,以及對自由和自毀的慾望之間的拉鋸。這樣的分裂,托芙.迪特萊弗森早在她第一本詩集《少女心》(一九三九年)所收錄的一首詩作裡即已表現出來,那首詩名為〈認知〉(Erkendelse)。她描寫一個女人摔破了童年家裡一個美麗的花瓶,只因為無法抗拒自身那種想破壞的慾望,她在結論這樣寫著:
「人們所託付於我的一切,皆從我手中殞落
因此,為了我們巨大的幸福
我的朋友,請別對我寄予關心」
《毒藥》裡的主人翁,被一種毀滅的慾望驅使,這種慾望不是作為一切的結束,而是為了生命的開始。她透過達到迷幻的狀態,來完成自己想超越僅僅身為一個人類的想望,而這種迷幻的狀態是如此迷人且強烈,能為她帶來在寫作時同等的沉醉及幸福感。她那無數次的婚姻、無數次的墮胎,以及無數次的藥物注射,都是為了達到這種狀態。
對於《毒藥》的主人翁來說,寫作是她唯一永恆的愛和驅動力。作為一個讀者,我們第一次遇見她時便能發現,在她寫作的同時,她週遭的世界正逐漸淡出。那是一個清晨,她的丈夫維果.F還在睡夢中,而她在寫小說。寫作是她一生的愛情,也是她渴望與男人們的關係裡能得到的那種愛情。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只有在寫作時,她才覺得幸福。為了寫作,她在清晨五點鐘起床。因為在那個時間裡,她可以對週遭的世界毫不關心,她可以把孩子擱置一旁。也是因為想起那些尚未被寫就的著作、那些總是浮現在她腦海裡的句子,把她從床上拉起來,打電話向醫生求救,住進療養院展開戒毒的旅程。寫作讓她有了抗戰和生存下去的毅力。
在書中主人翁的現實世界裡,她渴望能找到一生的摯愛,她想成為主婦和母親,卻無法嚴肅地對待這些角色。她可以在心裡揣著一個孩子及對其深深的愛意,書寫有關孩子們的一切。她可以書寫她在童年時如何被辜負,及她與母親間充滿問題的關係,卻無法好好成為她孩子的母親。
《毒藥》借用了傳統教養小說(Bildungsroman)(亦被稱為成長小說)的結構——以個人為中心,主人翁決定要尋找幸福,了解恐懼,走向世界,並且經歷各種事情,只為了最後再次找到歸宿。《毒藥》裡的主人翁在小說的結尾,並沒有找到她的歸宿,但是她和維克多找到了一個家的可能性,是開放的結局。維克多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可以把主人翁從毒癮深淵拯救出來的浮板,但危機早已潛伏在他們熱情幸福的愛情之間。「我們有相愛的權利」,小說中的維克多這樣說,有關這點,書中主人翁這樣回答:「這個權利,也總是傷害他人的權利」。
愛情會傷人,小說主角和維克多將會互相傷害彼此,就如她和前幾任丈夫所經歷過的那樣:第一任丈夫,比她年長三十歲的編輯維果.F,她嫁給他是為了接近文壇;第二任丈夫,艾博,完成了她對普遍幸福人生夢想的渴求;第三任丈夫,醫生卡爾,和他之間那種毀滅性的關係,讓小說主角染上了毒癮。卡爾是她三任丈夫當中最憤世嫉俗的一個,因為他看穿了她。他知道如何能讓她和他建立關係,他知道他的首要任務是:他必須讓她無法寫作。而他的武器是注滿杜冷丁的針筒。
《毒藥》一書出版於七〇年代初期,也是女性運動展開的時期,然而,托芙.迪特萊弗森並不把自己視為女性運動的參與者。她將「紅襪子」(Rødstrømpe)比喻為鬥牛犬,而作為當時《家庭日記》(Familie-Journalen)的專欄作家,她不斷鼓勵女性讀者留在不幸的婚姻裡,鼓勵她們妥協與屈服。一名有了五個孩子的女讀者,因為愛上一個有著兩個孩子的有婦之夫而想離婚,托芙.迪特萊弗森冷酷地在回信裡寫道:「七個孩子,兩個女人和兩個男人,您不顧一切追隨己心而尋求的幸福,並不值得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理智一點,留在原地吧。」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毒藥》仍舊是屬於女性主義的故事。這個故事描寫了一個年輕的女人,以為她必須依靠婚姻才能獲得想要的社會地位,最終還是成為一位獨立女性,透過寫作創造了自己的人生及空間。她領悟到,她無須依靠男人維生。她自己就能做到。作為一個讀者,我們彷彿聽見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其女性主義著作《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裡的那個聲音,書裡表明,一位女性若想成為一名作家,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每年可以賺到五百英鎊。托芙.迪特萊弗森在寫給她的朋友艾絲特.納戈爾的信裡也有類似說法:「實際上,一個女人如果不是嫁給一名百萬富翁,根本不該生育,或是應該安排五十歲後才開始生小孩。」從她的內心,以及作為她個人的守護者,我們很難不把托芙.迪特萊弗森視為女權運動者,但是她從來不是任何政治組織的成員。據說,他們讓她感到噁心。
托芙.迪特萊弗森在和她的第四任丈夫——維克多.安德烈森——的婚姻出現問題時,開始書寫《毒藥》。她搬到夏日度假屋裡撰寫回憶錄,因為維克多的情人搬進了他們的房子裡,而他們在家的時候,她無法專心寫作。她以嘲諷的筆調把這段經歷寫進一九七五年出版的《關於自己》(Om sig selv)這本書裡。但,即使托芙.迪特萊弗森坐在愛情這顛覆的小船上、儘管她寫下了那一句「愛情的權利,就是傷害他人的權利」的警句,她還是堅決地寫出一個帶有希望的結局。一個相信關係可以維持的希望。一個相信愛情依然存在的希望。一個可以傳遞給讀者並且讓他們繼續懷抱著的,希望。
{特別收錄}【寫作是唯一永恆的愛與動力】
——黛.普蘭貝克(Dy Plambeck)
我認為,《毒藥》是托芙.迪特萊弗森的主要代表作品。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一位優秀的作家面貌:她肆無忌憚卻又脆弱,幽默卻也殘酷,坦率且充滿了愛。在《毒藥》中,作為一個小女孩和一位堅韌的獨立女性,托芙.迪特萊弗森抵達了創作高峰。對於成癮、墮胎、不必要的耳疾手術以及對婚姻的不忠,托芙.迪特萊弗森那種坦率、輕佻的輕描淡寫,在讓人驚訝之餘,同時也讓人感受到她其實傷痕累累,甚至能感受到針頭是如何刺入她的體內、刺入所有男人、女人,以及...
目錄
|毒藥|
第一部
第二部
【特別收錄】寫作是唯一永恆的愛與動力
|毒藥|
第一部
第二部
【特別收錄】寫作是唯一永恆的愛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