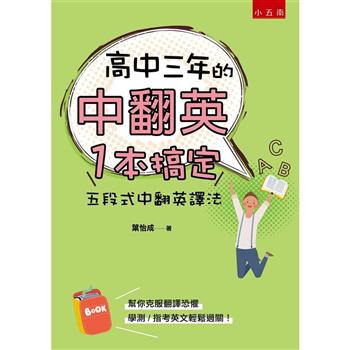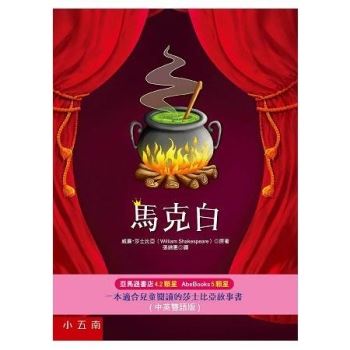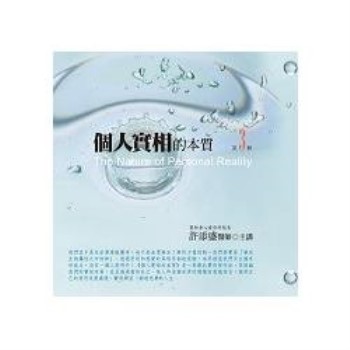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法國最高文學榮譽殿堂「不朽者」香塔勒·托瑪的自傳體散文。
◇法國世界報、L’Express 週刊等權威書評熱烈推薦。
◆師承羅蘭巴特,悠遊於學術與文學之間,交融知識與想像的獨特筆風。
◇在個人成長,思想啟蒙,女性覺醒、及68年5月學運等故事之外,一間間位在波爾多、巴黎的咖啡館也是書中主角。
◆法蘭西文學院院士香塔勒·托瑪作品選之四。
回憶咖啡館,是在回憶裡的咖啡館,也是在咖啡館裡的回憶。
2021年獲選為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成為法國最高文學榮譽殿堂「不朽者」的香塔勒·托瑪在這本自傳體的散文中,描繪她作為戰後嬰兒潮世代,所渡過鄉下海邊的童年、在高中哲學課受到的啟蒙、對於西蒙·波娃女性覺醒與思想自由的崇敬、1968年的社會動盪及5月學運的狂瀾,到她步入羅蘭·巴特門下的學思歷程。香塔勒·托瑪以其自成一家、優雅睿智的文筆,寫出她的成長、疑惑、年少輕狂......而這些回憶所蘊涵的哲思,勾勒在一幅動人的法國風情畫之上。精神與身體的綻放與休憩之處,人與人間悲歡離合的佈景,是一間間回憶咖啡館。
作者簡介:
作者 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生於1945年,法國當代傑出作家與十八世紀專家,香塔勒·托瑪悠遊於學術及文學創作間。深受早年師從羅蘭巴特的影響,她的書寫聯繫了知識與想像。
學術著作以關於薩德、瑪麗·安托奈特以及十八世紀自由精神之書寫最為知名。如《一代妖后:潑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奈特》(無境文化,第二版,2022),《薩德》(無境文化,2022)。
小說則多次被改編成電影與戲劇,如2002年獲得費米娜文學獎的《再見吾后》(無境文化,第二版,2022)。近年出版了多部半自傳體的散文,膾炙人口。如《我的老師羅蘭.巴特》(麥田,2019),《回憶咖啡館》(無境文化,2022),從二戰戰後海邊的童年,1968年5月學運,到與羅蘭.巴特的師生情誼......在含蓄的文字中具有詩性的韻味,細膩的描繪中處處顯露思辯的睿智,自成一家。
香塔勒·托瑪於2021年獲選為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成為法國最高文學榮譽殿堂的「不朽者」。
譯者簡介:
譯者 洪儀真
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社會學博士,主修藝術社會學。任教於大專院校,隱性從事翻譯和寫作。譯有《鋼琴師和她的情人》、《死去的男人》、《生死蓮花》、《什麼是道德案例》;合譯有《資本主義的先知:馬克思》。
章節試閱
【內文試閱】
我從聖約翰車站搭火車前往巴黎。單程車票。肩膀上輕輕揹著一只花布袋,裡面放著一些衣服,帆布鞋,橡膠鞋,同樣是花布料的長裙,外祖母編織的九重葛淡紫色披肩,波維爾(Pauvert)出版社的薩德書籍,黑金色的小冊子、思考遨翔的課本,和指尖一碰到就很快樂的教科書,還有我的自由精神聖經。西蒙給了我一份對他而言是有毒的禮物;對我來講則是純粹的喜悅。「茱麗葉,您喜愛聖豐(Saint-Fond)嗎?我一點也不喜歡他,我只是一時興起」。聖豐,聖安傑 (Saint-Ange),聖艾摩(Saint-Elme)…, 聖約翰(Saint-Jean),聖查理(Saint-Charles),聖拉札(Saint-Lazare),帕迪歐(la Part-Dieu)......。我暗自思量,車站常常以聖者命名,就像那些放蕩子(libertins),也像教堂和醫院一樣。這是要提醒我們,車站、教堂及醫院的建造是為了我們的益處,讓我們在人間的長途跋涉裡獲得幫助嗎?我們停下來,祈禱,接受治療,洗頭,換上乾淨的衣物,整理包袱,然後無論如何我們盡力再次踏上路程,一拐一拐地也得上路。咖啡館呢?不是比教堂、車站和醫院更值得聖徒之名嗎?因為如果有一個地方能讓我們呼吸和恢復精神,自我激勵,確認他的行李,查閱地圖,那就是咖啡館......。我提早抵達火車站,略過候車室走向車站食堂的酒吧。在我身旁有一位瘦小的男士筆直站著,他以一種含糊的嗓音點酒,與他的軍人氣質形成鮮明對比:「請給我一杯隆河谷(côte du Rhône)。白天,喝蘇維農(sauvignon)。晚上,喝隆河谷」。「好的」,服務生回答他,不是很認真。但這份許可對於喝酒的人來講已經足夠。男士重新挺直削瘦的身材,對著我微笑。我留意到即使他的袖口和衣領磨破了,衣著上堪稱端正得體。他指著我的背包:
——您要去旅行?
——對,我要去巴黎。
——來回還是久留?
——我不曉得。我要離開這裡,我只知道這一點。
——我去過一次巴黎。我忍受了四十八小時。啊!我並不羨慕您。他們的首都是恐怖的。我冷得要死,而且迷路。我快要不記得自己的名字了。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神經質的人們,而且脾氣暴躁。抱歉!你們不斷地道歉!抱歉!抱歉!幾乎不會克制自己撞到人!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巴黎周圍建造一座巨大的牆,超極巨大的牆,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窩在一起把所有的事情都變得越來越快速,並且互相謾罵。法國其他的地區從此得到安寧。尤其在夏天,巴黎人的神經質激怒了全世界。有些國家甚至無法復原。他們正在摧毀希臘,一個島接著一個島毀滅。希臘人看過這些裸露的外國女性之後,就很難面對自己的女人全身包裹著黑衣裳了。
——什麼事讓他們感到困難?
——很難再感到興奮了,當然。
——我知道希臘。連水底下都有偷窺者......然而應該這麼說,也許他們一飽眼福之後,就會趕緊和自己的妻子會合了。
——也許吧。無論如何,我堅持應該要把巴黎人監禁起來。
一位酒客抑揚頓挫地朗誦:巴黎仔,牛頭也,巴黎佬,狗頭也。我同意,應該把小牛頭圈起來。
——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嗎?我身旁的客人問服務生。
——白天喝蘇維農,晚上喝隆河谷?服務生回答。顯然他現在已經從談話線索裡脫鉤了。
——順道一提,來一杯隆河谷?既然現在是晚上。小姐,為了您的旅程,我能請您喝一杯嗎?
我們舉杯敬酒。在他眼中,我將前往不幸。不過,他覺得所有人都往同樣的方向迅速前進。
——我喜歡車站食堂的酒吧。沒有其他地方比這裡更能慢慢品嚐待在自家的幸福了。
他是僵直的,帶著尊嚴的束腰。唯有他眼神裡的某種含糊,以及措辭裡的一絲絲放任,指明他留意自己飲食的嚴格程度。早上......蘇維農,晚上......隆河谷?吧臺周圍關於監禁巴黎人的主意開始升溫。有一位反對者憂心於這樣的交談,他的孩子住在巴黎。
——所以您要離開了?您真的下定決心了嗎?
——真的,真的。
——您在此地欠缺什麼?留在波爾多不好嗎?
我沒有時間回答,我丟下一句「再見」,然後衝向火車。
——永別了。
他嚴肅的語氣讓我驚訝。我轉過身。他在那兒喝醉了,身體挺直,手裡緊握著他的紅酒杯。類似車站食堂的小圖騰保護者,更廣泛地說,是保護那些留在這裡的人,那些經常去車站而不想離開的人,他們喜愛靜止不動的出發。我愉快向他揮手。然而他並沒有回應。
我預訂了一個臥舖,但是幾乎沒有使用。空氣暖和,我和同車的女乘客一起靠在車窗,玩得很高興,閉上眼睛,讓勁風吹拂我們的臉。她懷有身孕,很難鑽進下鋪。風兒陣陣拂面之際,我倆談起等待我們的城市,巴黎。明日早晨我們抵達的終點站,也許會是我們整個人生的終點站。他的愛人應該會來接她。她帶著自信和愉悅,我也是。當她去躺下時,我留在列車走廊上,和其他乘客一起站著,以不同間距的排成一列。在一連串起伏的村莊景色和濕潤田園風景之後,這些失眠者將會是第一批看到告示牌的人:「巴黎,二十一公里」。
巴黎的里昂車站讓我驚愕。有廣播,有人在奔跑,有令人目瞪口呆的喧囂,還有鴿子在高聳的窗戶底下亂竄尋找出口。一個黑白的世界,有數百個用鉛筆描繪的小身影。我穿著鑲邊的裙子,微微戰慄。在1968年八月這個下雨的早晨,我立刻明白了,為什麼巴黎人要到其他地方去尋訪夏天,這件事整個八月都會重複發生。他們會翻越無論哪一座高牆......我的內心非常歡愉,然而從天空的顏色看來,我感覺亡靈節(le jour des Morts)已經到來。
由於我不知道地鐵路線的方向可以從終點站看出來,因此我漂流了很久,在車上一直被擠壓,觸碰,捏弄,亂摸:面對壓迫我胸部的傢伙,我使用我的袋子當作擋箭牌,但同時我的臀部被抓著。茱斯汀娜(Justine) 成為巴黎人淫蕩的題材,她秘密地向首都的聖母院祈禱,我仔細察看地鐵站的名稱,就像人們考察救贖的公式,也像我過去察看拉丁文多變的字詞,最後,經過一再犯錯,一再詢問,我還是成功地在正確的車站下車:田園聖母院(Notre-dame des champs),一個讓人心跳加速的名稱。我的地址以藍色簽字筆寫在一張折成四面的大紙上:聖迪維夫人(madame de Saint-Dyver),十七號之一。這是我的救星,是我的四瓣幸運草。我深信自己的好運,抬起頭來;我就在這裡!在自認為是我的房間的招牌底下,霓虹燈寫著:聖迪維。我進入屋內。一個男孩正使用吸塵器打掃陰暗而烏煙瘴氣的空間。我毫不遲疑地向他宣告這是我要居住的地方。他花了一些時間才弄明白(很少見到一位年輕女孩願意住在一間夜店裡),然後友善地對我解釋,是我搞錯了。他和我一起把對折的紙打開。我住的地方距離這裡幾公尺。女房東的名字跟這間夜店一模一樣,奇怪的巧合。
我住的地方還要再走過幾個門牌號碼,而且樓層比較高。位於六樓的傭人房。門房把鑰匙交給我,我遵循一面白底黑字的指示牌走去,沒有感到不滿:一個通往側梯(Escalier de service)的指示。我感覺到門房在我背後投以審訊的目光。他們不放過我。彷彿我可能會突然轉身,衝向正廳樓梯(Escalier des Maître),接著呢,——誰知道?也許我會扯掉紅毯,然後駐紮在樓梯的平臺。門房的丈夫也來了,他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平頂的頭髮猶如刷子。我盡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樓。
房間很完美。它不超過十五平方公尺。這個面積已足夠讓我漂浮其中,隔絕底下世界的煩惱。我將袋子放在紅色的地磚上,整個人躺在床上。一個可以看天空的房間,除了狹窄的床之外,這個天堂般的房間還有一張小桌子,一把椅子,以及門邊唯一真正的傢俱,一個質樸的紅木衣櫃。古樸的衣櫃裡隱藏著一處供水點,一個圓形的水槽,很適合醒來時用來濕潤你的臉。儘管我討厭波爾多女房東的五斗櫥,但我對偽裝成衣櫃的水源產生了立即的好感。我的房東住在院子對面的那棟樓裡。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門房指給我看她臥室的窗戶。夜裡,可以透過一盞恆常亮著的燈光辨識出她。
住在如此的高處,我覺得自己可以無限品味旅行者的輕盈,逍遙法外。我遙不可及:我的名字沒有在任何地方登記,沒有電話,我也沒有想過要申請電話。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意圖賴在一個地方不走。申請要花費好幾年。實際上,官方的等待時間是「超過一年」。過了很久以後,我終於決定向郵電部門申請電話,等我申請到電話,我早就出發去紐約了,在紐約幾個小時以內我就可以接上線……,我在一個介於庇護所和游牧生活之間的傭人房區域生存。有時,我會收到一個氣壓傳送信(pneumatique),為了一頓晚餐,一場約會。由於我的門從來不關,我不必從床上移動,我說了聲「進來」,然後走廊的陰影裡便會出現送信人員的身軀。通常他對於爬六層樓感到不悅。如果氣壓傳送信確實在強大的勁風速度裡穿越複雜管道而循環,那麼這些相較於密斯特拉風更強也定向更好的風力驅動者,在我的側梯樓下將徹底止步。沒有任何送信人員會通過窗戶來到我面前,輕鬆自在地帶著微笑,遞給我藍色的紙條或一束鮮花。不過,最常發生的情況是,送信人員的惡劣心情沒有持續下去。他會接受一杯飲料,開啟一段對話,聽一張唱片。我從不厭倦留聲機的神奇: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的非凡特權,藉此能夠召集一支室內管弦樂團來演奏他喜歡的曲目,這項特權我在任何時刻觸手可及。按照一般人的性情,在美麗的五月過後的寒冷夏日,沒有人想要工作。巴黎看起來並不像波爾多車站食堂裡的人向我預言的一般。焦躁不安和神經兮兮的人並沒有出現。地鐵,工作,睡覺(Métro, boulot, dodo),令人厭惡的行程,地鐵牆壁上憤怒的塗鴉不是為了任何人而展示。首先,我想到現在是八月,人人都在度假。
也許不是在度假,但肯定是銷聲匿跡。日復一日,都下著冰冷的雨。在塞納河畔,稀少的外國遊客看著透明包裝的書籍,就像看待其他物品一樣。沒有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更少,有幾個英國人,沒有美國人。他們沒有冒險進入歐洲。五月的事件已經足以讓他們害怕,八月十五日之後,隨著蘇聯坦克的闖入,布拉格之春被暴力終結,美國人確信我們再次進入冷戰。一個被遊客拋棄的巴黎,一個只屬於我的巴黎......
我沿著河堤散步,走到了水邊。塞納河暗綠色的水面上,雨滴被微小漣漪的同心圓暈染。日本人全神貫注盯著這個現象。他們把它拍了下來,像是異國情調的好奇心,若不把這影像帶回家,放在巴黎聖母院、艾菲爾鐵塔和洋蔥湯照片旁邊的話,那會產生罪惡感。我想起阿卡雄時期經歷的快樂,在雨水底下,在雨中游泳,那些淡水的水滴與鹽水混合在一起。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點,準備溶解在無邊無際。甚至是藉著這一點,藉著把自己完全交付於溶解,我得以最大限度地存在。巴黎對我產生了同樣的影響:無垠無涯,沉淪遇險,生命豐饒。
日本女性的雨傘有紅色、粉色、天藍色。它們擁有陽傘的精緻。我感到寒冷。我去買了一件長版翻領毛衣,長到可以變成連身裙。也買了一把彩色的雨傘。
聖日爾曼大道上,一個女孩以細緻的近距離視角繪製了蒙娜麗莎,身旁一個留長髮的男孩則用粉筆寫下異議:鋪石底下的沙灘,把你的慾望當成現實,佔領艾菲爾鐵塔,無政府狀態即秩序,不是機器人,也不是奴隸,消費社會必須死於非命......這傢伙索求一法郎:「團結的法郎」。
雨水將這些字沖刷殆盡,他重新開始寫。
佔領艾菲爾鐵塔,勝利在街頭,社會是一朵肉食性的花,學會唱國際歌,如果所有老人攜手共進,那就太荒謬了,......
隨著開學的到來,讓秩序擁護者安心的跡象增多了。學生表態要重新開啟學院,他們想參加考試。在焦慮之下,他們要求必須收到個人書面通知。與「激忿派」(Les Enragés)對抗的溫和派「南特爾學生運動」(Le Movement des Eudiant Nanterre)取得了上風,他們決心按照戴高樂將軍所言,戰勝「混亂之蛇」。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有些事情已經產生裂痕;舊秩序出了問題。學生的起義並沒有導致一場革命,然而它已經播種另一套思維模式、肆無忌憚的精神,以及對慾望說「是」的想望。它宣戰的敵人是:無聊。不過如果我們開始不知道如何感到無聊,世界將會崩塌,成為行屍走肉的世界。當然它會持續下去,而如果它顯得不畏打擊,那是因為它早已是行屍走肉。然而,禁令的重複以及對它們的屈從忍受,不會再是同樣平靜的明顯事實了。內政部長雷蒙‧馬塞蘭(Raymond Marcellin)重述:「有些人不放棄他們失去理智的希望,想要重燃火災」。他慎重警告那些「具破壞性的威脅」。
由於憂慮新的叛亂發生,巴黎索邦大學廣場的鋪石被移除了,就像今日對抗貧窮的戰爭手法一樣,地鐵站裡的長椅都被移走了。我坐在學生咖啡館裡面,因為室外正在進行移除廣場鋪石的工程,揚起大量的灰塵。我心想,這是多麼無謂的浪費力氣。六八年五月學運成功了。六八年五月學運改變了生活。就這麼簡單。
我度過了漫長的讀書之夜,其他讀者審慎的照明燈光陪伴著我,燈罩下微小的光線,是持久的清醒目光,也是夢想家的默契。彼此沒有見面的社會成員,卻各自為政地共享著對人說話的活躍文字之曼妙。我重讀《歲月的力量》:「我可以在黎明時刻回到家,或整晚在床上看書,在中午睡覺,連續二十四小時閉門幽居,心血來潮上街。我在多明尼克餐廳喝一碗羅宋湯當作午餐,在圓頂餐廳喝一杯巧克力作為晚餐。」我已經脫離考試與知識成就很久了。西蒙‧波娃對我而言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她為了讓自己不會閒下來,在準備學士證書考試之餘,還同時著手進行小說的書寫,她超越我太多了(遑論年少的沙特的文學英勇戰蹟,他在1914年十一歲時寫了一本戰爭小說,並且把手稿埋在阿卡雄的沙灘裡!)。不過,重讀這幾行文字時,我認為或許透過自由,透過這種簡單而基本的自由,隨心所欲地來去,整日漫步於巴黎,在破曉時手裡拿著一本書入睡,我的哲學探索可以重新開始......
我發現一間絕妙的賈斯汀咖啡廳-小酒館,位於一條名叫獨輪推車的死巷裡(impassse de La Brouette),我本來以為那不過是一間雜貨店。小酒館裡總是擠滿一群學生常客,一心只想和人民同一陣線,還有一個偽侯爵夫人,這女人臉頰上塗了白色粉撲,頭髮捲曲,髮型高聳,她小丑般的臉,剛好在髮髻頂端與細腰之間形成等距。侯爵夫人抱怨說她傷心欲絕,學生們友善地陪她喝酒,也帶點嘲笑的意味,不太相信她說的話,試圖要對她說教。這位受挫的戀人要求:「你們對我發誓,人民會知道如何愛我嗎?」學生說:「人民是至高無上的,我們無法代替它向您擔保。」侯爵夫人笑了。她沒有那麼悲傷了,特別是因為其中一位男孩請她喝酒,另一位則祝賀她,並且把一朵花別在她又濃又密的頭髮上。和侯爵夫人玩得過火是有些輕浮,也頗為令人瞧不起。然而那不過是順口說說,前提是,只要回到普羅階級掌權這個重要的主題上,就能得到原諒。這間咖啡酒吧成了我在巴黎聖母院街和聖日耳曼大道之間散步的必經休息站。我不敢進去花神咖啡館(Flore)或是雙叟咖啡館(Deux Magots),它們的歷史如此久遠,對我而言和法蘭西研究院的圖書館一樣高不可攀(此外,我也不知道兩者區別何在);不過聖日耳曼的Drugstore也嚇著我了,它閃爍著令人暈厥的現代性。這幾個地點讓我著迷,那些經常光顧的人們亦然。我坐在賈斯汀咖啡館喝著咖啡,漫不經心地琢磨這些人時髦與自然的揉合。我很熟悉賈斯汀這個地方優雅或不優雅的風格。這批學生我已經認識;至於侯爵夫人,雖然我因為陰沉的父母和參觀城堡的儀式而厭惡凡爾塞宮,然而侯爵夫人過時的優美引發我的同情。我早已透過我的娃娃與她相遇,她塗抹唇膏的嘴和紅色的指甲,她的眨眼,她的花邊腰帶,以及她的假髮。
某天下午,那是我在巴黎居留之初,當我進入賈斯汀咖啡館,侯爵夫人還沒有起床,除了一個披著斗篷的老先生以外,只有幾個年輕人。兩個男孩,一個身穿藍色工作服,另一個穿著黑色木匠服,正在吧檯前交談。他們對一個戰略問題意見不合。「無產階級」是他們論述的關鍵字。我聆聽他們說話,看見了愛森斯坦電影中的影像。一股征服的力量。水手肌肉發達的身體或金髮的農婦坐在拖拉機的高處。我聽見一場不會停下來的賽跑飛奔的聲音。我在俄羅斯平原的麥田裡勞動,在古巴的甘蔗園裡栽種,在墨西哥的仙人掌裡工作......當我聽得更清楚的時候,我得知這部電影的背景發生在中國。男孩們一再重複「無產階級」、「革命」的字眼,就像我在波爾多聽到的那樣,不過他們想到的是毛澤東。兩人面前的咖啡杯旁擺著一份《人民事業報》(La Cause du Peuple),一法郎,標題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還有一本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 剛出版的《1968年法國的戰略與革命》(Stratégie et révolution en France 1968),他解釋法國社會如何透過其內部飽和的緊張,使得馬克思所描繪的社會革命得以臻於成熟 ; 當然,桌上還有《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我翻閱這本語錄:「如果沒有對立面,每個方面甚至會失去存在的條件」,「一切戰略的本質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要尋找真正的偉人,我們應該要看的是現在」。說得好!我同意,完全同意。只有現在是值得關注的。當我們歌詠革命之時,正是當下的氣息驅使著我們。在我們多疑的眼前矗立的現在,是無法重來的。我全然支持現代的英雄。我與紅衛兵一起行進。「喜見千浪黃金穗/英雄夜裡薄霧歸」,我行進,看到群眾歡騰揮舞小紅書,我眼前彷彿不斷有紅色的蝴蝶飛舞,我行進,經過湍流,懸崖,攀登山頂,扎營河岸。文化大革命的廣袤美麗在於它不僅是行進,也泅泳。聽聽毛澤東怎麼說:「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這是他在1956年時寫的詩。十年之後,毛澤東於1966年游泳橫渡長江十五公里。彼時他七十三歲,在老子的教導之下,他明白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我們怎麼會不想加入壯游?怎麼會不想得到寬餘?現在我游泳,現在人們游泳,所有人,像瘋子一樣,被巨大的紅太陽吸引至天際線。
——五月的時候你做了什麼?
——什麼?
我沉浸在長江水域,沒能清楚察覺這個提問。穿著黑色西裝的男生重複了他的問題。他們更想知道在五月我投入了什麼事,和誰一起在革命時並肩作戰。
——我在南部。
——妳應該要在巴黎。所有的革命都在那裡發生。妳沒有想過要北上巴黎嗎?妳還是可以搭便車啊。
——你忘了已經沒有汽車了,因為已經沒有汽油了。另一個男生糾正他。
——我那時候生病了。我去馬賽,為了參加瓊‧貝茲(Joan Baez)的演唱會,然後我病倒了。
這是事實,而且我很高興能夠糾正一下剛才隱隱針對我的苛刻批評。我的回答毫無光榮可言。至少,我有一個缺席的理由。
【內文試閱】
我從聖約翰車站搭火車前往巴黎。單程車票。肩膀上輕輕揹著一只花布袋,裡面放著一些衣服,帆布鞋,橡膠鞋,同樣是花布料的長裙,外祖母編織的九重葛淡紫色披肩,波維爾(Pauvert)出版社的薩德書籍,黑金色的小冊子、思考遨翔的課本,和指尖一碰到就很快樂的教科書,還有我的自由精神聖經。西蒙給了我一份對他而言是有毒的禮物;對我來講則是純粹的喜悅。「茱麗葉,您喜愛聖豐(Saint-Fond)嗎?我一點也不喜歡他,我只是一時興起」。聖豐,聖安傑 (Saint-Ange),聖艾摩(Saint-Elme)…, 聖約翰(Saint-Jean),聖查理(...
目錄
目錄
在一個下雪的嘉年華夜晚....../ 003
1. 櫥窗咖啡館和秘密咖啡館/ 041
2. 學院酒吧/ 131
3. 藝術家咖啡館/ 241
目錄
在一個下雪的嘉年華夜晚....../ 003
1. 櫥窗咖啡館和秘密咖啡館/ 041
2. 學院酒吧/ 131
3. 藝術家咖啡館/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