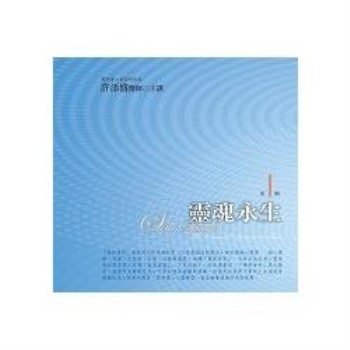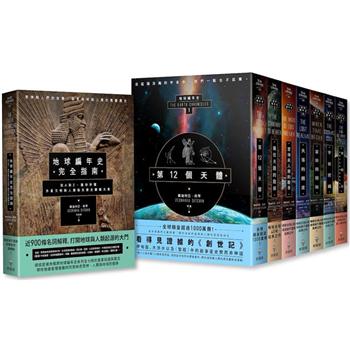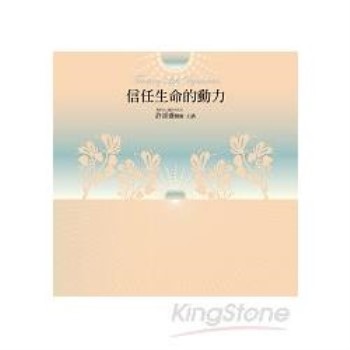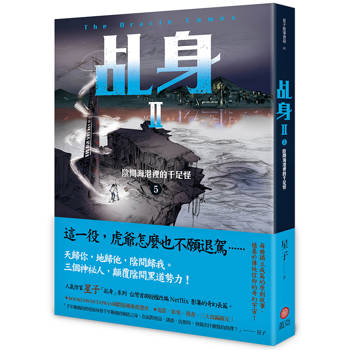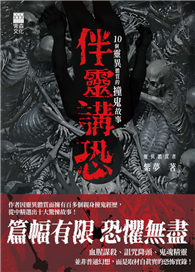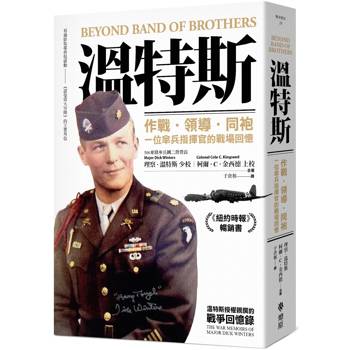英俄大博弈
歐洲地緣場域變遷本書所稱「西方」大致指的是「歐洲」,更嚴格來說,也可稱之「西歐」或者是「拉丁歐洲」;無論如何,由於歷史現實持續變遷所致,各時期討論關注之地理範圍或不一致,基本可從以下六個階段性演進來觀察。
第一階段乃四七六至八○○年的自然真空(natural vacuum)時期;自五世紀末西羅馬滅亡之後,原先羅馬帝國核心東移至君士坦丁堡,甚且在東西勢力消長與查士丁尼一世帶領下,東羅馬在五世紀中葉一度達到極盛,幾乎控制超過三分之二之地中海沿岸地區,相對地,此時法蘭克勢力則以部落聯盟形態在西歐建立了極其鬆散之封建秩序,衝突規模不大但不絕如縷,從而提供了本書指稱「歐洲例外主義」與近代思想家「自然狀態」想像之現實起點。
其次是八○○至一三○二年的二元對立(dual-centered)時期;隨著七世紀伊斯蘭勢力開始擴張,以及同時期東羅馬希拉略克王朝(Heraclian dynasty)內亂以致版圖大為縮減,加上接手墨洛溫王朝的加洛林王朝,在九世紀聯合羅馬教會確立某種教權封建體制(九六二年移交神聖羅馬帝國),整個地中海世界從而在表面上一分為四,除穆斯林與基督徒各據南北半壁之外,其內部又各自存在二元對立態勢(伊斯蘭世界為阿拔斯與北非地區後伍麥葉政權之對抗),此時,受限彼此敵視與交通動能,所謂「西歐」大致從伊比利北部的卡斯提爾往東延伸至易北河畔,向南則涵蓋義大利半島,與東羅馬之間形成某種「正統競爭」態勢。
接著是一三○二至一四九四年的大分裂(great division)時期;在此期間,即便有馬其頓王朝(Macedonian dynasty)一度中興,拜占庭勢力自十二世紀起幾乎侷限於巴爾幹半島至小亞細亞西側苟延殘喘,直到一四五三年遭鄂圖曼終結為止,至於西歐地區也因封建分權框架與黑死病來襲以致幾乎奄奄一息,不僅教會面臨分裂危機,從義大利到日耳曼邦國四處林立,讓整個歐洲的崩解離析在十四世紀臻於高峰。
無論如何,以大國為主之權力遊戲自十五世紀末正式登場,也在一四九四至一六四八年帶來一個兩極對抗(bipolar competition)時期;相較神聖羅馬帝國僅僅握有象徵性威望,中古時期地中海貿易霸主威尼斯已漸日薄西山,最早完成王權演化的法國與西班牙不啻是兩個具有爭霸意圖的一級國家。此時,歐洲地理場域首度包括了整個伊比利半島,然後向東延伸到與波蘭、匈牙利交界地帶,北方以瑞典為代表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也開始被納入,至於東羅馬則遭到邊緣化。以前述場域為主之法國與哈布斯堡(以西班牙系統為主)兩極爭霸,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共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是一四九四至一五五九年的義大利戰爭,雙方為爭奪半島商業利益與對教會控制權而持續混戰,最終奠定後來以「合縱」為主之權力平衡基本格局;至於第二部分其實和三十年戰爭最後一個階段重疊,起自一六三五年法國走出幕後正式參戰,最後以一六四八年終結西班牙哈布斯堡爭霸之旅結束。
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歐洲進入了法國獨強(French domineering)時期;路易十四統治的法國取代西班牙成為眾矢之的,西班牙、奧地利、英國(大不列顛)、瑞典與尼德蘭負責扮演「合縱」常客,威尼斯與波蘭在大國爭霸當中逐漸邊緣化,普魯士與俄羅斯則在一旁蠢蠢欲動並蓄勢待發。至於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與大北方戰爭分別在一七一五年與一七二一年結束帶來之變化,則讓法國、英國、奧地利、普魯士與俄羅斯的五強均勢(five-power balance)浮現成為歐洲政治新常態,西班牙自此徹底從大國棋盤之中出局,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成為次要地緣區域;在此必須指出,首先,俄羅斯真正具意義地成為五強之一,還是要等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其次則所謂五強格局在一八三○年代後由於隱然出現東西陣營分化以致些微變形,但大體持續至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加入世界大戰為止,至於其場域則大致與地理上的歐洲大陸重疊。
除此之外,就在最後的兩個階段當中,歐洲經歷了前述兩次對抗法國的普遍性同盟嘗試,從而讓國際關係「常態化」(國家之間互動頻繁)成為現實,並提供各國一個鍛鍊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絕佳舞台;其次,除了以歐陸為中心理清其地緣政策基礎,十六世紀起的地理大發現不啻提供歐洲一個「外延世界」(extended field),雖不可能排除其存在,但實則要到十九世紀後,海外殖民地之地緣政治意義(開始反饋歐洲國際關係)才會逐漸浮現出來。
俄羅斯作為新變數繼十五至十七世紀的鄂圖曼之後,自十九世紀迄今,俄羅斯絕對是影響歐洲之最大「外部地緣變數」之一;即便兩者均有強烈之「歐洲化」企圖(但目標不完全一致,鄂圖曼或為滿足重建帝國戰略與承接羅馬正統,俄羅斯雖與此部分類似但更著力爭取成為歐洲國際社會一員),如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輕易地組成一個反蘇聯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至直到冷戰結束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一九九五年《文明史綱》書末以一章「另一個歐洲」來提及俄羅斯,賈德(Tony Judt)在二○○五年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歷史的書中,卷首亦特別指出,此處歐洲「不包括俄羅斯、土耳其」等,俄羅斯在「歐洲」眼中的「他者」形象顯然牢不可破。
大體來說,近代俄羅斯源自於九至十二世紀位於波蘭以東歐陸深處的一個斯拉夫人群體「基輔羅斯」(Kievan Rus'),在擺脫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金帳汗國控制後,莫斯科公國自十五世紀崛起,伊凡三世(Ivan III)統一全境後自稱「全俄羅斯君主」並於一四七二年迎娶東羅馬君士坦丁十一世姪女,伊凡四世則在一五四七年將「沙皇」(凱撒之俄羅斯音轉)改為正式頭銜並自稱「第三羅馬」,最後由彼得大帝在一七二一年大北方戰爭勝利後自我加冕為「全俄羅斯皇帝」(Emperor of All Russia)。
由於一五六九年組成共治聯邦(condominium)之「波蘭‒立陶宛」的地理阻隔,俄羅斯無法直接與西歐政治互動,又因深處內陸腹地,不可能加入日漸甚囂塵上之大西洋貿易競爭浪潮,只好選擇大膽深入西伯利亞以控制在中國、中亞與歐洲都有著大量需求的奢侈商品,亦即有「黑金」之稱的貂皮;其實,皮草不只是俄羅斯增加貿易收入或分霑海洋經濟的唯一籌碼,在本土來源因長年濫捕逐漸枯竭的困境下,為了急於尋找補充貨源,早在一五五四年征服欽察汗國殘餘勢力喀山後,便沿著伏爾加河前進裏海與薩法維波斯取得聯繫,然後由葉爾馬克(Yermak)率領哥薩克騎兵探險隊,在一五八二年越過烏拉山隘口東進,一六○四年先在距離莫斯科三千五百公里的托木斯克設置了前哨基地,接著於一六三六年抵達鄂霍次克海濱後轉而南下接近黑龍江流域;據此,在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一個半世紀之後,非但俄羅斯領土面積從一六○○年到彼得大帝去世的一七二五年,由五百五十萬大幅增至一千五百二十萬平方公里,成功挑戰西伯利亞凍原帶也堪稱在傳統絲路之外打通另一條歐亞大道,從而為十七世紀全球地緣政治投下一大潛在變數。
必須強調,俄羅斯雖一度在十六至十七世紀踏上「東進」的漫長征途,但十八世紀起則聚焦「西進」,一方面自此開啟一段邁向「歐洲化」的歷程,並依此採取了兩線並進戰略:首先在西線鎖定波羅的海,關鍵是在一七○○至一七二一年的大北方戰爭中擊敗瑞典(後者曾迫於壓力向鄂圖曼請求支援夾擊),藉由《尼斯塔德條約》(Treaty of Nystad)取得今日愛沙尼亞附近,一七七二年再利用第一次瓜分波蘭取得現今白俄羅斯與拉脫維亞部分區域,至於南線則瞄準衰落中的鄂圖曼,自一六七六年爆發首度大規模衝突至一八二九年左右,俄羅斯在一個半世紀中先後對土耳其發起八次戰爭,尤其透過第四到六次戰爭拿下克里米亞作為橋頭堡,並將勢力伸入多瑙河流域後,黑海便成為莫斯科另一個戰略焦點。
當然,最重要的轉捩點乃瓜分波蘭與法國大革命後的反法同盟戰爭。
利用「波蘭‒立陶宛」逐漸式微契機,俄羅斯與普魯士、奧地利透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與一七九五年三次協議將其瓜分殆盡(奧地利未參與第二次),其中,俄羅斯不但囊括該國三分之二土地,在長期緩衝地帶消失後,也讓它首度在地緣上直接接觸歐洲均勢體系,特別是一七九八年在奧地利堅持邀請下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更使其踏出了「加入歐洲」的第一步,此後除一八○九年第五次同盟外,俄羅斯幾乎無役不與;莫斯科所以沒有加入前述同盟,主要乃因一八○七年《提爾西特條約》(Treaties of Tilsit)暫時轉與拿破崙結盟,並趁法國壓制歐洲機會四處擴張所致,其後仍利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失利,隨同盟反攻在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入巴黎,亞歷山大一世曾稱這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可見其象徵意義。為討論戰後國際秩序,幾乎歐洲所有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所主持,在一八一四年九月至翌年六月召開的維也納會議,亞歷山大一世乃唯一親自出席的國家元首,充分顯示他對俄羅斯在歐洲外交界「首度亮相」之重視。
在會議當中,為了在拿破崙戰爭後阻止法國再起,包括在東北方讓尼德蘭併吞比利時,在東方解散萊茵邦聯並改組成由奧地利領導之日耳曼邦聯,東南方則除了同意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讓奧地利重新控制北義大利並擴張薩丁尼亞領地等,都表明各國針對法國未來問題之地緣戰略思考;除此之外,普魯士獲得薩克森(Saxony)四成領地加上先前趁亂瓜分之波蘭國土,力量亦大為擴張。
回到俄羅斯;除了滿足擴張目標,為確保成為歐洲一員或至少不被輕易排除,亞歷山大一世首先透過瓜分波蘭並於戰後進一步取得華沙公國部分領地,徹底消除了過去與西歐之間的長期地理阻隔,其次,在一八一五年拉攏奧地利與普魯士組成鬆散的「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建立朋友圈後,更重要的舉措是支持由梅特涅推動的「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以及根據《第二次巴黎條約》第六條關於「推動大國定期磋商」建議而在一八一八年首度上演的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機制,從而藉由某種「制度化」途徑鞏固自身之國際地位與發言權。
自此,俄羅斯成為歐洲各國眼中,或正或反,但絕不能排除的一個戰略變數。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戰爭的年代:西方國際關係之歷史與理論爭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08 |
國際關係概論/國際組織 |
二手書 |
$ 360 |
二手中文書 |
$ 468 |
社會人文 |
$ 495 |
國際關係 |
$ 495 |
中文書 |
$ 495 |
政治 |
$ 495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550 |
軍事\戰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戰爭的年代:西方國際關係之歷史與理論爭辯
從古羅馬到中世紀歐洲
從地理發現到全世界
人類究竟如何走上戰爭不歸路
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
儘管在人類世界當中,沒有其他衝擊比戰爭更加殘酷,也沒有任何事件如同戰爭一般,往往伴隨難以抹滅之悲劇與創傷,更讓人無法釋懷的是,戰爭似乎已經被接受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而吸引無數研究者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心理與生物學角度,各自探索其來龍去脈與影響。
延續《瘋狂的年代》視角,本書作為「歷史與國際關係」系列二部曲,除繼續鎖定戰爭之起因與發展,依舊嘗試聚焦歐洲(西方)歷史,畢竟人類在這裡進行了最漫長且最難分難解的戰爭,也是在這裡形成了戰爭被日常化的出發點,同樣地,今日對於戰爭問題之正義思考、邏輯辯證、政策抉擇與未來無論樂觀或者悲觀之期待等討論,絕大多數也是由西方學者各憑己見,從歐洲歷史當中提煉出來的果實。
本書要談的不只是戰爭如何影響歷史進程,更希望瞭解戰爭如何形塑人們想法並形成有意義之思辨,包括:該如何看待甚至利用戰爭?如何加以界定並試圖限制?戰爭如何影響政治制度(國家)演進?人們如何在戰爭當中極盡爾虞我詐?尤其在大戰當中發展起來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如何反饋其源起並處理戰爭問題?由此衍生之理論又可能將人類帶往何方?
面對對峙陰霾揮之不去,甚至大戰看似又將一觸即發,站在充滿不確定性之歷史十字路口當中,我們究竟何以自處,又該如何應對?
作者簡介: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章節試閱
英俄大博弈
歐洲地緣場域變遷本書所稱「西方」大致指的是「歐洲」,更嚴格來說,也可稱之「西歐」或者是「拉丁歐洲」;無論如何,由於歷史現實持續變遷所致,各時期討論關注之地理範圍或不一致,基本可從以下六個階段性演進來觀察。
第一階段乃四七六至八○○年的自然真空(natural vacuum)時期;自五世紀末西羅馬滅亡之後,原先羅馬帝國核心東移至君士坦丁堡,甚且在東西勢力消長與查士丁尼一世帶領下,東羅馬在五世紀中葉一度達到極盛,幾乎控制超過三分之二之地中海沿岸地區,相對地,此時法蘭克勢力則以部落聯盟形態在西歐建立了...
歐洲地緣場域變遷本書所稱「西方」大致指的是「歐洲」,更嚴格來說,也可稱之「西歐」或者是「拉丁歐洲」;無論如何,由於歷史現實持續變遷所致,各時期討論關注之地理範圍或不一致,基本可從以下六個階段性演進來觀察。
第一階段乃四七六至八○○年的自然真空(natural vacuum)時期;自五世紀末西羅馬滅亡之後,原先羅馬帝國核心東移至君士坦丁堡,甚且在東西勢力消長與查士丁尼一世帶領下,東羅馬在五世紀中葉一度達到極盛,幾乎控制超過三分之二之地中海沿岸地區,相對地,此時法蘭克勢力則以部落聯盟形態在西歐建立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卷一 / 萌芽與啟蒙:現代國家的誕生
The Birth of Modern State
序幕:走出中世紀的歐洲 Prelude: Europe out of the Middle Age
另一場被忽略的大分流
北宋中國及其象徵 / 主流經濟視野下的歷史分歧 / 向帝國告別
黑暗中躑躅前行
後羅馬時期與新歐洲 / 戰爭與歐洲例外主義 / 本書寫作目的
戰爭作為日常 War as Daily Life
教權封建時期
羅馬與戰爭史 / 黑暗時代與上帝之城 / 封建主義與基督教會 / 準神權社會下的正當性
現代世界之形塑及其新秩序
新世界觀中的時間與空間 / 十字軍與西歐的擴張嘗試 / 最後的絕對理性時代
...
The Birth of Modern State
序幕:走出中世紀的歐洲 Prelude: Europe out of the Middle Age
另一場被忽略的大分流
北宋中國及其象徵 / 主流經濟視野下的歷史分歧 / 向帝國告別
黑暗中躑躅前行
後羅馬時期與新歐洲 / 戰爭與歐洲例外主義 / 本書寫作目的
戰爭作為日常 War as Daily Life
教權封建時期
羅馬與戰爭史 / 黑暗時代與上帝之城 / 封建主義與基督教會 / 準神權社會下的正當性
現代世界之形塑及其新秩序
新世界觀中的時間與空間 / 十字軍與西歐的擴張嘗試 / 最後的絕對理性時代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