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墓誌的演變史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
──宋.范仲淹〈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一、未定型前的演進
人類發明的墓誌銘,無論是西漢時代的中國文明,還是羅馬帝國時文明及其日後的基督教文明,都露於地表。但中國的墓誌銘到東漢以後即轉而埋入地下。相形之下,到第七世紀回教文明興起,阿拉伯人發明的墓誌銘同基督教文明一樣,也都露於地表。這是中、西墓誌銘相異的第一點。歐洲人和阿拉伯人自有墓誌銘以來,都以超簡短文句來表示。這點和長篇大論的中國墓誌有著極大的分野。這是中、西墓誌銘相異的第二點。中國的墓誌銘除非有特殊原由都是藏於地底下的。在第五世紀之前,墓誌的名稱、形制,以及書寫形式都未定制之前,墓誌尚在演變中的多元、歧出情形,筆者且舉數例來說明。
首先,東漢和帝永元四年(92)有位大官袁安去世,他的子孫給袁安做了一個墓誌銘。這個墓誌石是在民國初年被人發現在河南偃師縣一土地公祠中,當作擺設牲品的桌案,為了合用還被切了一角,以致每一句都去了句尾一個字。當時有識貨者趕緊將此石典藏於地方文物館中。到了抗戰期間,國軍為掘黃河堤以水淹日軍,乃奉命將此石帶走,並將它藏匿在熊耳山中,至今下落不明,但還好早有人做了拓片,我們今天仍有幸看到一千九百年前的情形。
這個墓誌只管詳述袁安的歷任官職,但不及生年和家世,只說了死年和葬日。在這裡,我們看到官歷成為一個人身分重要認證的憑藉,漸漸地,人們對於墓主的讚美之詞便出現在墓誌中。到了東漢晚年的第二世紀末,就有大文豪蔡邕出來指斥其事,認為是「諛墓之文」。有人認為,墓穴中藏誌石是為了方便辨認先人骸骨用的,這是擔心陵谷變遷影響地貌,使得人們在指認先墳或先人遺骸上有所困難的緣故。這個見解經常在歷代誌文於講完葬處後接著提到。
到了第三世紀,也就是西晉時代,人們對於墓誌其物的稱呼並不統一,有種種名目。這時字數略增,而且稱許墓主的話相當普及。像前此袁安的墓誌只記官歷,相形之下,那些沒有官歷的平民和婦女豈不存在可以製作墓誌的條件?從目前出土墓誌看,情形似乎是如此。但我們還是發現有女性墓誌。像大文豪左思的妹妹左棻,生前為皇妃,死後被葬於宮中,有關她誌文的誌作者於其誌文中明載其家世、父兄之事,並及其品行。這是一個女性可以擁有墓誌的一個例子。但畢竟是有身分的女性。這個誌石是一九三○年在河南偃城被人發現,因而擴大了我們的見聞。
在製作墓誌的實驗、摸索期間,西晉時代的樸素型除了存留北方的一系外,另一系隨漢人政權播遷到南方。
西晉永康元年(300)前述晉武帝的妃子左棻去世,享年四十五歲,由於無子嗣,故她的墓誌明載是由其姪兒具銜處理喪事的。本誌正可見出西晉樸素型墓誌的原委。誌石正面的文字共三十九字,誌作者以此再現了左棻的一生,如下:
左棻宇蘭芝,齊國臨淄人,晉武帝貴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二十五日葬峻陽陵西徼道內。
峻陽陵是晉武帝的葬所,徼道是帝陵的警備道路,左棻埋骨在路旁,可知不是陪葬帝陵的性質。該誌只交代墓主籍貫和身分,並及死日和葬處,如此而已,大有前述袁安誌文之遺緒。其所不同的是誌石背面,以比較拙稚的刻工刻出如下文字,共五十字,如下:
父熹字彥雍,大原相,弋陽大守。兄思,字泰冲。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惠芳。兄女嬡,宇紈素。兒子聰奇,字驃卿,奉貴人祭祀。嫂翟氏。
這是在明揭墓主娘家家族成員名單,奇特的是不分男女都出示名和字。而且,更重要地,指出左棻無子嗣,由姪兒代行祭祀。這讓人想起日後武則天欲傳位姪兒的大膽計畫,不是毫無根據的。這一出示家庭成員名單的項目在往後五、六世紀北魏墓誌中還看得到。
過江到南方的墓誌文化發展到了劉宋時代,墓誌才發展出以稍有傳記雛形的文本形式,出現在世人面前。到這一步,名稱、刻製工藝、形制,以及文體都確立下來了。劉宋元嘉十八年(441)名流顏延之為死者王求寫的墓誌,就叫作「墓誌」。但此一墓誌未見出土,顏延之本人及其後人並未保留原稿,所以,儘管我們獲知顏延之很可能是最早使用「墓誌」其名的人,但並無實物或原稿文可供證實。最早用墓誌其名的實物證據,是某人所寫的〈劉懷民墓誌〉,作於劉宋大明八年(464)。此誌在結構上,由墓主才性、年籍和死葬日,以及家人和官歷等三部分所構成。其中第一部分占有篇幅之半,全是浮泛的稱頌話語,像「笤笤玄緒,灼灼飛英」、「眩紫皇極,剖金連城」等等。這較之一百六十年前西晉的墓誌,增添了一些傳記書寫的材料。
由於南方新發展出的墓誌形式及其定名更回傳到北方,也受到北方人士的熱烈迴響,筆者據此得知原有西晉樸素型墓誌已遭揭棄。這點筆者尚可藉由北魏末至北齊時代近年出土墓誌加以證實。這樣一來,墓誌文化突破了南北政治分裂的格局走向普及化,這有助於五、六世紀中國死亡文化的整合。
成熟之前的墓誌,有各種各類的表達形式,茲舉二例於下。首先,有位燕國(按:即前燕)的遼東太守、幽州刺史□□鎮(按:姓名不明,只知名字中兩字的末字為「鎮」)在派駐朝鮮半島上後死於任上。時為高麗國好太王談德統治半島的時期,這位(前)燕國大官於談德永樂十八年(408)去世,享年七十七歲。他的後人和同僚為他做了一個墓誌(按:當時未有這個名稱)藏於墓穴中。筆者暫時稱它為「幽州刺史誌」。誌文本身共一五六字,包含籍員、歷官、卒年和享年、遷祔之日、祈願,以及遺願等部分。但之後尚有墓主一群僚吏共同寫的題記,合起來就有六百五十餘字。本誌與日後成熟之誌比較起來,特點有二:其一,不對墓主德行做任何吹噓,其二,多出同僚寫有題記,這種情形以後似乎未之一見。
本墓誌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被人掘起,它在藏身地下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後始被人發現。發現的地點是漢代殖民朝鮮的軍事據點的樂浪郡,今為北韓大安市德興里舞鶴山南麓丘陵上。樂浪郡有大批漢人遺民的大面積墓葬地。五世紀立國河北的諸燕國與朝鮮本地政權保有某種關係,似乎可從此誌中窺出。
輯於六世紀二○年代的《文選》,主編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特為「墓誌」文類(genre)選有一文。請注意,蕭統此時已將「墓誌」視為一大文類,但他所選的唯一一篇,是八字一句疑似有押韻、共十二句的文章,共有九十六字組成。誌作者憑此精簡文字再現一位婦女的一生,如下:
既稱萊婦,亦約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
蕪沒鄭鄉,寂寥楊家。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暫啟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這一墓誌文(按:下稱「劉夫人墓誌)是由名人任彥升執筆,是為劉瓛妻、王法施女(按:沒有名字)所寫。墓主王氏出身瑯琊王氏,其六代祖王遵曾為晉丞相,她死於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該墓誌由兩部分組成,前部八句,主要在講王氏的美德,以及王、劉兩家門風有多美好。後四句在講王氏的家墓狀況,包括外表和內裡。短短一文用盡典故,符合貴族文學的調調不說,它以稱許墓主作為書寫主題,就與朝鮮半島上那位燕國大官墓誌對於稱許不著一字的方式,判然大異其趣了。此誌上距成熟墓誌形成的第一批產品不過五十年,就顯現出日後墓誌書寫重心是在表彰墓主德行這一特點。但本誌與一些成熟的墓誌還是有點差別,那就是太過遷就美文的形式,使得許多人生經歷無法忠實傳達。誌作只能寫可以表達的部分,對於難以用文體表達的部分,只有割捨的分。本作即使比〈劉懷民誌〉晚三十九年,但筆者認為宜歸諸尚在多方嘗試的墓誌階段。本書將墓誌成熟伊始暫訂為西元四五○年只是大約的寬鬆說法。
蕭統不可能取讀埋入穴中的墓誌,如以上所舉的袁安誌、左棻誌、幽州刺史誌等而論,他毋寧遷就少數得之不易的墓誌——疑係他向名家求的——從中選了任彥升作的這一篇。
二、定型後的一些變化
墓誌定型之後,除非有些例外否則都一概稱「墓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傳記的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總是先從人物家世和籍貫說起,再及其品格和官歷(按:墓主如係女性則改講其夫或其子的官歷),末則說到臨終和喪葬情形。其情形就像讀者在第一章所見到的一九三三年〈吳雪樵誌〉一樣。
底下筆者舉的二則誌文,則違背上述常態,或套式。先說其中一誌。首先,它不稱誌,而稱碑,那是因不藏墓穴、反樹之於地表的緣故。其次,它的敘事結構和文體都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它不是私密性文本,而是公開性文本,它是有所寄託而寫,而且是有政治目的而寫的。也就是說,有公開之虞、從而顧忌大眾得知私人情事的墓誌,誌作者在表達上,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借題發揮,別有寄託。這通常是名家寫親人、或他人墓誌所顯現的一種特性。
這個墓誌講到一件事,關係到李唐中央與河北三鎮衝突的問題。話說河北三鎮於憲宗治下表示臣服之後,中央直接派遣官員統治其地,南邊的魏博鎮和北邊的盧龍鎮分別由親中央的將相,即李愬和張弘靖來治理,中間的鎮成鎮由原魏博帥田宏正來治理,結果都發生鎮軍或逐帥,或殺帥的事件。田宏正是被成德軍所加害,惡耗很快傳抵長安,中央領導班子的盤算是,田宏正的兒子田布,以歷任關隴各軍的資歷,再加上他是舊魏博軍的少帥,乃打定主意由他出任魏軍統帥。田布原是抵死不從的,無奈皇命難違,他只好辭妻、子、朋友,抱著有死無生的氣慨去赴任了。筆者從田布不敢接任魏師之職,即知他深知此事凶險,同時也暴露李唐中央對河北事務的無知。就這樣埋下悲劇的種籽。
田布到了魏地,便努力廣結善緣。「誌」作者庾承宣(貞元八年[七九二]進士,寫田布碑時間是八二二年,死於八三五年)於稱讚之餘,又跳出來解釋說,這些作為是枉費心力的,原因為何?據庾承宣說是:
魏之風俗久悖聲教,魏之將士素染狠戾。懷安自固,忽感激之勇節;積驕成惰,無戰鬥之剛腸。
就在這裡,「誌」作者將魏博鎮的鎮軍徹底污名化個夠,說他們違背教化很久了,而且早就染上「狠戾」的歪風。這意思是說魏軍是野蠻人。不過,此「誌」寫作時間上距魏地脫離唐中央統治已有五、六十年之久。此後,中央才直接統治其地幾年光景。以李唐中央觀點視之,魏軍不服從中央是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誌」文底下又說魏軍欠缺「勇節」和「剛腸」這兩樣軍人必備的武德。
當魏軍配合中央各軍出鎮去攻打盧龍和成德兩軍時,因碰上中央後勤補給作業不完善,魏軍是處在一種自費出兵的狀況,故而魏軍無意打這場仗。魏將出面向田布表示這場仗打不下去。這些將領向田布講的話,通通被「誌」作者再現如下:
頃常出軍,賴朝廷供給,優膽軍府,因以完濟。今者,瘠己肥國。尚書無乃太公忠乎?
這是說平時中央出錢,魏軍出力這樣的分工才是一個合理狀況。如今光由魏軍自費出兵,簡直是瘦了自己(軍府),而肥了國家(唐廷)。而且諸將認為田布笨得可以,只是他們不便講得如此露骨,換個方式說田布對國家過於「公忠」罷了。
「誌」作者竟然得知田布與諸將之間如此具體的對話,是很值得懷疑的。這是我說「再現」,而不說「記錄」的理由所在。其實說再現還是客氣了一點,應該說是想像。但此處「誌」作者指出魏軍過於地方本位主義,這倒是與當時「強地方、弱中央」的政治態勢相當吻合,因此,他模仿魏將向主帥田布的說話口氣,不能說毫無所據。
本「誌」底下還有一次田布和眾將之間的對話,值得我們玩味再三。在這場戰爭中。由於中央各軍在此遭遇阻滯,這麼一來影響到整個戰爭的勝負。魏軍無意一戰的態勢益趨明顯,最後他們還強迫田布退兵。魏軍一侯安抵魏博首府的魏州城,諸將先田布一步說出他們提的條件。根據「誌」作者的想像,這番說詞如下:
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賞禮樂皆自己出。近以保富貴,遠以貽子孫。苟能從眾之謀,則奉戴如舊。
當時諸將是否這麼說,按說「誌」作者於田布死後作此文,照理不在場當無所知才是。除非他事後問過在場諸將。但筆者相信,「誌」作者在遠離出事地點的長安寫作此文,絕對沒有花費從事實證調查的氣力。以上三句話中,前一句話在前述「誌」作者跳出來先污名化魏軍之時,已做如是表示。試想被污名化的魏軍會如此自污嗎?筆者不能無疑。再查其第二句話,是一種很現實、很勢利的態度。這不算罪惡,因為世俗大眾行為模式大都如此。第三句話是提條件的說話方式,無涉是非善惡,可以不論。
要之,「誌」作者模仿魏將語氣向主帥有所威脅的話,筆者認為,魏將不至自污若此。這只能說兩京士大夫對河北人有所偏見的投射。這是「誌」作者對河北人這個「異族」有所貶抑,就以此來想像河北人會如此認定自己。
到底魏軍如何脅迫田布,筆者雖未能清楚其底蘊,但田布自忖無力回天,倒是可以確定。否則他不會聽了屬下的話後就連忙自殺。田布死的時候才三十八歲。
關於這則人物傳記文的敘事結構是這樣的:
一、墓主品格的稱許
二、墓主慘死的始末
三、碑作者一番慨嘆的提出
四、墓主死後哀榮
五、墓主事功
六、碑作者另一番慨嘆
七、墓主上朝廷遺表的轉述
以上對於該「誌」作者所建構的三處關於河北人「他者化」的言說,是安排在上述第二部分。本「誌」寫法的奇特在墓誌成熟期的一千五百年間相當突出,它的突出點在於「誌」作者運用倒叙和插述的敘事筆法,從墓主之死說起,再倒回墓主生平種種。這不同於一般墓誌由生講到死這樣的直線敘述法。當然,倒敘筆法並非此誌才首開其例,之前也曾有過這種例子,只是鮮少人如此寫。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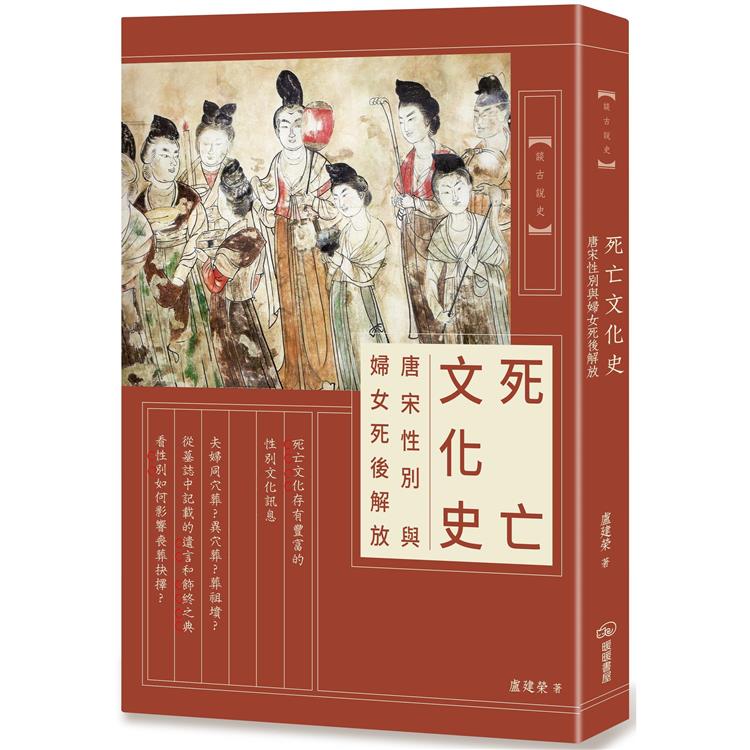 |
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盧建榮 出版社: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9-15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0 |
中華文化/民族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文化研究 |
$ 360 |
歷史 |
$ 360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4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
夫婦同穴葬?異穴葬?葬祖墳?
從墓誌中記載的遺言和飾終之典
看性別如何影響喪葬抉擇?
「本土死後世界信仰」與「異邦式死後世界信仰」
鰥夫、寡婦,死後是否選擇相約泉下?
本書主題是死亡文化,在方法上運用新文化史「再現」的概念,以記錄拼湊「過去」事件的一小部分。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在萌芽,傳世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
墓誌定型之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原是喪家至親好友看過後即被封存於墓中的私密文本。八世紀末葉以降,文體日益傾向散文化,這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有關,這是本書重大發現之一。墓誌另一演變是從私密性生出公開性一路,此緣於喪家找名家寫誌,而傳抄、出版流通更廣。於是私密性墓誌成為文學革命的場域所在,塵世的文學場域仍是駢文的天下。
誌作者為死者生平敘寫的墓誌,再現了瀕死者在臨終場景與探視者互動的狀況,以及交待遺言和飾終之典。東漢以前,中國漢人社會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迨進入到五世紀之後的六百年則有兩個死後世界,供瀕死者抉擇。佛教進入中土之後,有愈來愈多人放棄原本固有本土死後世界信仰,改採異邦式、即死後陪侍佛祖的選擇,這對於婦女,特別是守寡有年者,吸引力尤其大,且比男性多得多,這是為何?
在唐代,本土死後世界信仰畢竟仍居主流位置,講究的是夫妻合葬,以女子而論,最起碼要葬到夫家的家族墓園。要是子女依親長遺命,一不葬配偶墓旁、二不葬在家族祖墳所在,便會受到社會輿論壓力,令執行親長遺命的子女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女性是否於死後掙脫性別不平等加諸其身的桎梏?
作者簡介: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2021)、《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2021)、《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2021)、《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2021)、《誰在統治地方:唐宋地方治理文化打造史》(2022)等書。
章節試閱
第二章 墓誌的演變史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
──宋.范仲淹〈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一、未定型前的演進
人類發明的墓誌銘,無論是西漢時代的中國文明,還是羅馬帝國時文明及其日後的基督教文明,都露於地表。但中國的墓誌銘到東漢以後即轉而埋入地下。相形之下,到第七世紀回教文明興起,阿拉伯人發明的墓誌銘同基督教文明一樣,也都露於地表。這是中、西墓誌銘相異...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
──宋.范仲淹〈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一、未定型前的演進
人類發明的墓誌銘,無論是西漢時代的中國文明,還是羅馬帝國時文明及其日後的基督教文明,都露於地表。但中國的墓誌銘到東漢以後即轉而埋入地下。相形之下,到第七世紀回教文明興起,阿拉伯人發明的墓誌銘同基督教文明一樣,也都露於地表。這是中、西墓誌銘相異...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增補版序:
「命喪黃泉」與「送你上西天」──人生得意須盡歡
一
本書的再版,讓我想起童少年的一段往事。
還是小學生時,讀俗文學和漫畫,都會碰到書中人物死亡的情節,倘若講起某人去世,會說此人:「命喪黃泉」,要是結束對手生命,又會說:「送你上西天!」。小小年紀不解何以死亡會與「黃泉」和「西天」扯上關係,但從文脈上下文看,知道是與死亡相關物事。之後,年齡增長,這個童年心中小小疑惑一直銘記在心版,沒有忘卻。
原來中國人死後世界以為是在祖墳地底,由於掘地會掘到地下水,於是人們想像先人死後聚會所在,多半...
「命喪黃泉」與「送你上西天」──人生得意須盡歡
一
本書的再版,讓我想起童少年的一段往事。
還是小學生時,讀俗文學和漫畫,都會碰到書中人物死亡的情節,倘若講起某人去世,會說此人:「命喪黃泉」,要是結束對手生命,又會說:「送你上西天!」。小小年紀不解何以死亡會與「黃泉」和「西天」扯上關係,但從文脈上下文看,知道是與死亡相關物事。之後,年齡增長,這個童年心中小小疑惑一直銘記在心版,沒有忘卻。
原來中國人死後世界以為是在祖墳地底,由於掘地會掘到地下水,於是人們想像先人死後聚會所在,多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不斷出書乃專業史家的天職
增補版序:「命喪黃泉」與「送你上西天」──人生得意須盡歡
第一章 序曲
第二章 墓誌的演變史
一、未定型前的演進
二、定型後的一些變化
三、私密性墓誌率先發動古文運動
四、秘密與公關兩型墓誌並存於世
第三章 死後相約泉下
一、戰爭攪擾日常喪葬事宜
二、政爭高潮與返葬邙山運動陷入谷底
三、先塋、薄葬與合葬
四、鰥夫的喪葬文化餐點
五、鰥夫的另類喪葬文化餐點
六、平民的全套喪葬文化餐點
七、未亡者寡婦處理亡夫的喪葬餐點
八、臨死者寡婦的喪葬抉擇
九、歧出的死亡文...
增補版序:「命喪黃泉」與「送你上西天」──人生得意須盡歡
第一章 序曲
第二章 墓誌的演變史
一、未定型前的演進
二、定型後的一些變化
三、私密性墓誌率先發動古文運動
四、秘密與公關兩型墓誌並存於世
第三章 死後相約泉下
一、戰爭攪擾日常喪葬事宜
二、政爭高潮與返葬邙山運動陷入谷底
三、先塋、薄葬與合葬
四、鰥夫的喪葬文化餐點
五、鰥夫的另類喪葬文化餐點
六、平民的全套喪葬文化餐點
七、未亡者寡婦處理亡夫的喪葬餐點
八、臨死者寡婦的喪葬抉擇
九、歧出的死亡文...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