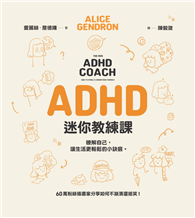序
吐盡心頭血句句為台灣
陳永興
邱垂亮教授是台灣出身,旅居澳洲布里斯本的知名政治學者,他除了在澳洲昆士蘭大學教過許多學生,其中出了不少重要的澳洲政壇人物;同時也是國際上知名的政論家,寫過不少政治評論文章,而在台灣一黨專政的戒嚴時期,他的文章經常觸犯威權統治者的敏感神經,屢遭查禁,當然他也成為黨外時期家喻戶曉的政論家。我就是在黨外時代投入反對運動,幫忙黨外政論雜誌時讀到他的作品,而心儀其人,之後有機會認識時,他已積極投入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經常返台與反對運動的重要政界人士有所接觸,其中康寧祥、陳水扁、呂秀蓮、張富美、彭明敏、李筱峰……等等是他較常接觸的人物。而我和他的交往可說是君子之交,互相認識彼此欣賞且有高度的默契。
一直到二○一四年我要創辦《民報》時,邀他擔任海外主筆,邱教授不但一口答應,還邀集布里斯本的熱心同鄉陳博文醫師和陳春龍藥師,共同加入《民報》成為股東表達支持,他向這兩位朋友說:「永興要辦報,我們非支持不可。」從此邱教授不僅成為《民報》重要的撰稿者,更可以說是《民報》的海外重量級主筆,幾乎每周都有他的大作,他從《民報》創刊一直到過世前夕,八年間都未停止供稿給《民報》,而且他知道《民報》的財務困難,所以都義務寫稿而不收取稿費。只有每次他回台灣時我會邀請他和其他主筆聚餐,他總是很高興的和其他為《民報》寫稿的朋友喝酒聊天,非常健談,充分展露了純真風趣的個性,是大家非常歡迎的志同道合戰友,也是博學多聞、熱愛台灣的海外學人。作為《民報》的創辦人,我內心對他充滿了感激和感動。
沒有想到,三年前我的女兒竟然自己申請到布里斯本的學校去進修碩士學位,當我陪同女兒去拜訪邱教授時,他高興地與夫人陪我們逛他一輩子教書的學校,又請我們吃飯,並交代我女兒,有事一定要找他,也因而在他過世的前三年,彼此來往密切了起來。有一次我去布里斯本時聽邱夫人抱怨說,邱教授身體不適卻不去看醫生,我就勸他去接受檢查才發現了他的癌症,之後在一連串就醫的過程中,我請和信醫院的醫師朋友提供邱夫人相關治療的不少意見,在邱教授走完人生旅程後,我義不容辭以《民報》的名義為邱教授主辦了台灣的追思活動,邀請邱教授生前好友,在台北舉行了隆重溫馨的追思活動,並出版了一本邱教授的追思文集。
邱教授過世已逾一年,而在這疫情當中,我的女兒也從研究所畢業了,開始在澳洲擔任社工師。今年四月因澳洲解除了入境管制,我才能再去探望女兒,同時也探訪了邱教授夫人,我向邱夫人提起希望能將過去邱教授在《民報》發表過的文章集結成書,邱夫人欣然表示同意,所以我回台灣後立即著手將這本書編輯完成,並請邱夫人寫一序文,邱夫人的序文詳細描述了邱教授生病期間受到的肉體煎熬,卻在病榻上不忘為《民報》撰稿與關心台灣的心境,又描寫了他們夫婦的結識和戀愛經過,夫妻情深令人感動。也請李筱峰兄寫一序文,深入介紹了邱教授文章的特質和功力,這樣子我們用「民報文化藝術叢書」的名義來為邱教授出版他的政論文集,也算是我們對他永遠的追思和懷念。
但願喜歡看邱教授政論的讀者們,都能擁有這本邱教授的紀念文集,從中可以體會這位令人懷念熱愛鄉土的旅澳學者,他一輩子最後的時間,所寫「句句為台灣吐盡心頭血」的結晶作品。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日於台北民報
序
「老頑童」春蠶吐絲
李筱峰
一九七四年,我因為在當時言論最前進的《大學》雜誌發表文章批評我當時就讀的政大教育系,遭政大勒令退學,轉學到淡江。但政治的高壓沒有遏止我對時局的關切。當時「黨外」民主運動正熱烈展開,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本「黨外」民主運動的政論雜誌《台灣政論》創刊。這本標舉「民間輿論的發言台」的月刊,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之後,「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象,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但是《台灣政論》只出刊五期,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
被國民黨當局拿來作為停刊「理由」的一篇文章叫做〈兩種心向〉,該文談論鋼琴家傅聰與一位中國出來的柳教授的談話,因觸及台海關係與台灣前途問題,國民黨當局以該文「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下令停刊。我身為關心台灣前途的「憤青」,每一期必讀《台灣政論》,這篇觸及國民黨敏感神經的〈兩種心向〉,我當然詳讀,而且對作者的大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那是我第一次留意到「邱垂亮」的名字,不僅印象深刻,對這樣一位關心台灣的海外學人更是深深感佩!
我萬萬沒想到五年後,我擔任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執行編輯,參與「黨外」民主運動,而與黑名單解禁回台的邱垂亮教授開始見面結識,成為忘年之交。他算是我的老師輩,但平易近人、愛開玩笑的他,則把我們後生晚輩當平輩朋友。
二○○○年民進黨執政後,邱老師更常回台,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更加讓我感受他幽默風趣、愛開玩笑的性格。
邱教授在海外長期替台灣發聲,為澳洲與台灣關係鋪路牽線,在海內外不斷為文,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呼號,啟蒙大眾。在台灣的民主運動路上,他是一位堅毅的勇士!一位「個子不高」的巨人。
一般學者寫政論,總是中規中矩,力求所謂「理性」、「客觀」,因此他們的文字往往艱澀索然。但是邱垂亮老師的政論,則大異其趣,他的政論裡面有許多他的身影、他的故事,喜怒哀樂,嬉笑怒罵,生動活潑,所以他的政論,像是文學的散文。這種散文式的政論(或說政論散文),使人讀來津津有味,讓讀者融入他的心境中。我個人寫政論,也偏好如此表達方式,所以我與他可謂「臭味相投」,他也因此很賞識我,每次回台邀宴彭明敏教授時,我常獲邀敬陪末座。
雖說邱老師的政論常有他的喜怒哀樂、嬉笑怒罵的心緒,但是他並非莽撞無理、不顧大局之人。舉例來說,我們支持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蔡英文在第一任內的許多言行讓獨派人士不甚滿意,(詳見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一向很支持小英的邱教授,也對小英有很多不滿意,屢次為文評論。我與他幾乎看法一致,也有數篇文章評論蔡總統,他對我的評論也「心有戚戚焉」。小英準備競選連任前的民進黨的黨內初選時,我和邱教授都支持賴清德,但是我們當時即表明,最後誰出線就支持誰,這是「大敵當前,大局著眼」的思考。民進黨初選結果,小英出線,二○二○年總統大選時,已經罹癌的邱老師,極力支持小英,在澳洲組織「小英後援會」,抱病挺英,為小英募款。
邱教授不幸於二○二一年三月十三日過世,綠營很多識與不識者,同表哀悼。但是卻出現有位傅姓律師藉機在臉書上面取笑邱教授和我,傅律師留言說:「『不去投蔡,等於投韓』這句話只能嚇嚇邱垂亮、李筱峰這些書呆子,嚇不了二○一六年以後的彭明敏和一九九六年以後的我。」。所謂「書呆子」看如何定義?通常「書呆子」是指死讀書,食古不化、食經不化、食文字不化、不知變通,不懂因時制宜、不知忖度主客觀環境、毫無謀略……的頭腦僵化者。如是觀之,食「台獨」口號而不化者,用二分法看事物者,才是十足書呆子。
邱老師(有時候我們稱他「亮公」)當然不是書呆子,他頭腦靈活而不空喊口號。他被中共列為「台獨頑固分子」,但是邱教授靈活回應:「我不是『台獨頑固分子』,我是『民主頑固份子』。」邱老師的回應太好了!這正是我追求台灣獨立的理由。我們不是為台獨而台獨,是為民主而台獨。
去年(二○二一)年二月,邱教授邀集海內外的好友在Line上面組了一個群組。在二月十七日的Line群組上面他寫道:
……前年底韓國瑜旋風橫掃台灣。民調都說小英二○二○必敗。彭教授等三大老,公開請小英不再競選連任。我贊同,並建議賴清德挑戰小英。賴初選失敗,我和筱峰支持英德配。我出任布里斯班小英後援會會長,辦了一個很大的募款晚會,募了一筆競選經費。她大勝我大喜。她第一任時,我就認定她不會推動我的台獨議程。曾傳話給她,表明支持她的富國強兵政策,但會繼續堅持我的台獨立場。故有此台獨障礙之文。
〔按:是指他當天發表的〈台獨的障礙──習皇帝、趙少康和小英〉一文〕
此後數十天,他經常在Line群組中留言,抱病依然談笑風生,開著玩笑當「老頑童」。三月十一日,邱老師在line上留下這句話:「親朋好友,大家平安!我現在住院,非常虛弱,暫時不回答各位的關心問候。非常感恩!🙏」兩天後,三月十三凌晨,「老頑童」離開我們!
我們的摯友陳永興醫師將這位「老頑童」近幾年來在《民報》電子報上面的文章收集成冊出版。這是邱垂亮教授春蠶吐絲般對台灣的關愛,對民主的維護的最後心聲。
二○二二年六月九日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序
回首來時路
林月琴
垂亮與我雖然都在二戰開始前後誕生於苗栗山城,但成長歲月我一直都在苗栗市南郊龜山,他卻遠在公館鄉出磺坑,七歲又搬到更遠的台南東山區牛山礦場深山裡,在我進入台大之前我們是完全不知對方存在的兩顆行星。
一九五八年是台灣有史以來唯一不分組的聯考,那時我不懂自己的志趣,選校不選系,依照家人的願望甲乙丙丁組最高分都選,得分四百一十,考上第二志願台大外文系。台大外文一大堆才子才女,那一年北一女畢業生有三十幾位保送台大。第一名胡建華,她可選擇任何科系,但父母不讓她學醫,只得選外文,出國後才改行,後得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也曾是台大醫學院教授。第三名李明明,巴黎大學博士,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創所所長,還有其他男女同學也都在各行各業有傑出的成就。很明顯的,因為沒分組,文學並非我們第一志願,畢業後出國為工作、為家庭、為興趣都改行念其他科系,不像垂亮那一屆出了許多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等。
一九五八年的中秋夜,天高氣爽,大二的學長在螢橋(中正橋)下淡水河濱舉辦迎新晚會,我們的班代表陳家明把他同寢室的「老頭子」邱垂亮介紹給我,說同是苗栗的客家人。在朦朧的月光下我沒特別注意,只感覺怎麼有那麼奇怪的人,年紀輕輕的就叫「老頭子」。講到他的名字,真是落落長,他一直認為文責自負,所有中文寫作都用邱垂亮,我只看過一篇〈政治犯出來了〉用筆名林亮人(我的姓,兒子名),那是因為他在《首都早報》當總主筆時,社論可以不署名,但同一天出兩篇文章時必須有作者名字。小時候父母親、阿姨等用日語叫他「亮兒」,或客語「阿亮a」。也許從小就是「模範生」,在牛山被其他大人、小孩叫「老頭子」(Old Man=OM),一直叫到老。大學有段時間取名James,因喜歡《養子不教誰之過》的James Dean(詹姆斯‧狄恩)。英文用王雲五字典的拼法Chwei - Liang Chiou,這是他所有正式文件名字,但這個名字太難拼,外國人或自己出書都簡寫成C. L. Chiou,或只叫姓Chiou與簡單的C. L.。韋氏拼音是Chui - Liang Chiu,中國拼音Qiu, Chui - Liang,在尋找他的著作時,因地制宜必須知道這些拼法。孫子出生後用客語叫「阿公」(Agun),晚年則被生徒們稱為「亮公」(Lianggong=LG),鍾老(鍾肇政)的客家專用語阿「亮牯」(Lianggu=LG)。但他晚年也喜歡人稱呼他LG=Life’s good(美好的人生),就像韓國的電器品牌。我習慣叫他OM,因他給我第一封信,就叫我MH,自己署名垂亮,第二封就開始全部改稱OM。我們訂婚時很窮,買了兩個很小的純白金戒指,上面刻著的是MHOM。我的名字倒很簡單,就是林月琴,大二被會話課老師Father Murphy取名為Flora Lin,意為森林裡的花草。結婚後改為Flora Chiou(中文沒有改夫姓),Moonharp=Moon Harp=MH是他的直譯。多年後曾問他琴也可翻譯成鋼琴piano,為什麼一定要豎琴harp,他得意洋洋說:「小孩子不懂,MH也可以是My Honey,My Heart啊!」哈哈,這個詭計多端的老頭子,一開始就存心不良,還說什麼不是浮世的「追」。
言歸正傳,經過高中三年寒窗苦讀,剛從聯考壓力解脫的我只想身心自由地體驗大學生活,迎新會後也沒多想,很快就忘了。寒假過後,椰林大道兩旁杜鵑正在盛開,他把家明拉來一起到傅園旁的女生宿舍邀我去碧潭划船,我藉口要期中考,拒絕邀請,他們只得悻悻然離去。
一九五九年暑假過後,他又跟家明一起來邀看電影,又被婉拒。真正開始慢慢地瞭解他是在一九六○年的暑假,他在台中成功嶺受訓,七月十二日寄出第一封他所謂「不是浮世的『追』」的信,而只想跟MH談談音樂、文學,但信中卻讓我覺得「怎一個愁字了得」。為了不使一個年輕人頹廢下去,我回了一封鼓勵的信。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文字攻勢,雖然常是他寫了好幾封我才回,他還是雀躍萬分。受訓完,大四新學期,透過家明他得知我選了心理學,他也選了,這樣他每週都會來封限時信邀請或要我課後告訴他可否接受週末的活動,但他都沒有成功。他曾狂言要燒女生宿舍,我當然沒在怕,但後來想想也覺得他滿可憐,雨中來,淚、雨不分中離去。那時我已知道他嘉中同學有個念台大護理系妹妹很喜歡他,她寫信給我,也來找過我,我都鼓勵她繼續努力,我們真的不是一對。我忙,上課外一個星期最多時要跑三個家教,也想出國。但以後他學乖了,他不再透過任何人,他發現我家教地方,邀不成去看電影時,他說家教後要接我回宿舍,新生南路與仁愛路交叉口和台北橋是他最常站崗的地方。經過兩三年折騰,我終於由同情到被他的真情感動,決心「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使有淚,甜蜜和溫馨永不疲憊,堅信總有一天會有屬於我們的時光,能有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閃耀充滿希望的世界。
在台大,年少輕狂的他像一匹脫繮野馬,若不是一股愛的力量逼他出國,伺服他的也許就是被退學或監獄。當時他被選為班代,想要與國民黨推出的代表、經濟系的潘秀江競選台大學生會會長,我極力反對他雞蛋碰石頭,因秀江高中跟我同窗三年,我很瞭解她。一九六一年畢業,等待服役,暑假我們都留住宿舍。家教、田園的一杯檸檬水與古典音樂、椰林間漫步、工學院前草地上談心觀日出、西門町的電影與附近的燒鴨和小黃瓜、金山野柳的郊遊,還有那七月十二日無眠夜,在文學院樓上傳出韋伯的〈邀舞〉與令人泫然的舒曼的〈夢幻曲〉,一切宛如昨日,如今在那古樹下尋夢的老人與孩子已是天上人間。
快樂時光總是飛逝而去,八月他先在士林受訓兩個月,緊接著被分發到澎湖服預官役。他的辦公室和寢室是在一間廟宇的進口處看門神的官邸。他形容:
不管我坐著、躺著,對面就兩位堅毅地站在那裡的守門神,他們的高大有MH的三倍,相貌是又兇又惡,嘴巴紅紅的裂得又大又歪,面黑忽忽地呈猙笑貌,兩眼瞪得大大地,眉毛刷子一樣地下垂著,手上拿著一根大棍子,好像先要把你打成一堆肉醬,然後再把你吃掉似的,總之他們心腸是仁慈的,但是外貌卻如山魑鬼魅,此之謂人不可貌相也。
他說來到這個島上他的活動範圍就是廟宇、海、電影院和一家放古典音樂的冰果店。他說這四個地方有個共同點就是他在那些地方都非常寂寞,非常孤獨,所以他養成了每天日記式的寫一封限時專送給MH。五個月後移防台南新化,擔任排長,後又移駐嘉義內埔,他不喜歡圍牆內駐軍的生活,但還蠻喜歡那段圍牆外翻山越嶺行軍的日子。
從這一年的「軍中日記」我瞭解不少他童年的生活,在日本當護士長的阿姨口中的聰明伶俐又頑皮的小孩。他會為大哥出氣,把比他高大的人打倒,當母親拿起竹子要打他時,他一溜煙的就跑了,從來沒法追到。他《三俠五義》之類的書看多了,想當濟弱鋤強的遊俠。喜歡幫助弱勢,對窮困者的憐憫深深刺痛著他的心靈。小時就結交了二個啞巴,在軍中又碰到一個,學會了手語。他曾描繪其中的一個小啞巴:
記得有一次,天下著傾盆大雨,我們照例抓住這個良機突襲,龍眼正值最甜的時候,雨下得那麼大,主人不會有興趣出來巡邏,我們放肆猖獗,爬在龍眼樹頂上,又吃又採,正心花怒放,得意忘形的時候,一聲「吧啦」,有人掉下去了,我低頭一看,是小啞巴,雨水把龍眼樹澆得非常滑,他一不小心,就摔下去,樹大概有一丈多高,我感覺不妙,趕快兩三把急速下降,等我站在他的身旁時,他已經好好地站在那裡,我用手勢問他是否還要再爬上去,他搖搖頭,一邊吃龍眼,一邊走回家,很悠閑樣子,只是右手沒有在擺動,第二天我才知道他的右手已經完全摔斷。
在我們那個小村子裡面,憑著我的一點小聰明與山中無猛虎的情況下,我的書念得頗有盛名,小啞巴對這點也許太嚮往了,拇指一翹,衝著我咧齒一陣子傻笑,表示了他的欽佩與羡慕,後來……偶爾我們再度見面他依然是一翹拇指,一陣子傻笑,充滿了純厚的真誠。
他也談了很多電影和人物,蔣廷黻、胡適、葉公超、殷海光、余光中,甚至國外的邱吉爾、史懷哲、畢卡索,與一九六一年去參加停火談判,飛機墜毀身亡,後被追授諾貝爾和平獎的聯合國秘書長Dag(台灣翻譯成哈瑪紹),只要他讀過的書或報上出現的人物,他都會評論,中心思想是人道主義與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渴望。
一九六二年六月我畢業,準備在苗栗高中教一年,籌備出國旅費。八月他服役完,沒接受曾約農老師推薦的鳳山陸軍官校當英文助教,而去了沒有見面會談過、辛志平校長就發聘書給他的新竹高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在苗中,他每週都會來苗栗看我兩次,同時也家教。那時他們家還在牛山,所以來苗栗都住在他小學班導師董國英老師家。一直到他要出國前幾個月,他們家才搬回苗栗,但他還是習慣住董老師家。經過一年辛苦籌足旅費,預備一起到加州聖地亞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SDSU)。八月我們訂婚,但最後一刻我的體檢因肺部陰影(結核鈣化)被擋,他九月十七日經日本飛美,我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才出國。整整四個半月,那是我們決心携手同行後最長的分離,對雙方的折騰難以言喻,他又日記式的把所遇所學全都紀錄下來,也因此我還沒出國就已瞭解一九六○年代留美生活。他到達聖地亞哥第三天就註冊,跟研究所的所長Dr Lemme會談後來轉系成功。這所長在SDSU位子等於副校長,剛跟校長Love一起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美國總統甘乃迪,但幾個月後甘乃迪就被槍殺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拿到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碩士學位,同時就在加州州立大學的富勒頓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找到工作,也結束我們半工半讀的艱苦歲月,他得以全神貫注完成他的博士課程與論文。一九七一年他拿到加州大學博士,來澳洲昆士蘭大學任教。一開始他想回台,希望在台灣制度內改革國民黨的專制政治。他參與轟動一時的第一屆「國建會」和「革新保台」。在《人與社會》寫文章,當社務執委,但最後還是因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的一篇文章〈兩種心向〉成為黑名單,三年不准踏進家門,以後十幾年每次回台都需要經過冗長繁瑣申請特許。而當年一起開會、辦雜誌,蔣經國想吸收的台籍學人都去做了大官。
一九八○年代,他寫了很多文章,台灣的民主化風起雲湧,大步邁進。繼林義雄家與陳文成悲劇後,一九八五年特務殺到美國舊金山,他很失望,在香港《中報月刊》發表〈蔣經國先生應該下台了〉,這篇文章還被台灣多家雜誌引用,他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而怡然自得。這段時間他也常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人民、杭州、復旦等大學講學,講西方民主化的理論,也講台灣正快速民主化的經驗。因而結識了許多民主改革派學者和學生,如嚴家其、方勵之、蘇紹智等等。他也參加了第一次北京香山和第二次廈門鼓浪嶼的「台灣之將來」會議,那是鄧小平開放改革讓中台兩邊統獨學者對話的年代。一九八五年一月他還帶著我和小女兒,由國台辦重點招待的從北京、西安、上海、蘇杭、廈門、鼓浪嶼繞了一圈,看了大半中國河山。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民運人士被迫害,逃的逃、關的關、殺的殺,十年來他對中國民主宣揚、嘶喊,曇花一現,悲情、絕望落幕,他也從此不再踏上中國的土地。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他回淡江大學客座,在《自立晚報》的〈晚安台灣〉對著跟我同時期在南加大唸研究所而認識的蔡同榮說:「(那時蔡勸他回國實際參與政治,他拒絕)……對我,是寫出一兩本經典之作,向世人闡述台灣人民流血流汗創造民主現代化政治奇蹟的經過。」他的「雄心大志」是,「將來在英美西方政治學界,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研究台灣政治發展必讀我書」。一九九五年他終於完成英文本Democratizing Oriental Despotism(東方專制民主化)由英國Macmillan Press和美國Scholarly and References Division, St. Martin’s Press出版,這是從文化與制度決定論的不同角度,解說民主化在中國失敗,在台灣成功的理由,基本上論述了他對民主發展的看法。去年四月為了把他的著作寄回國史館,想買這本書(因我們只有一本,寄回去就沒了),打開Google一看,精裝本竟要價兩百多塊美金。今天(二○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再輸入他的名字與書名,四十一秒鐘,包括書評竟跳出一萬兩千一百條。這本絕版書在美國售價精裝本$131 - 286,英國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電子書(e - book),精裝本一百三十五歐元。劍橋大學出版社也上線了(online),一本要六十五美元。台灣研究似乎已成為顯學,在天上的他,一定很安慰現在英美西方政治學界都在讀他的書了。
一九九七年夏,我們去布達佩斯開亞非學會年會,OM要發表論文,會前先去巴黎,這是我們第二次遊巴黎。下了飛機,我們自己直接搭火車到巴黎市中心,住在事先預定好塞納河岸的旅館,預備漫步巴黎,迤邐塞納河。有一天,在羅浮宮廣場,四、五個吉普賽小孩,一人拿寫著不太像法語的紙板往他懷裡一揣,他還沒搞懂什麼意思,他們就一窩蜂跑走了。他也沒感覺什麼不對,直到要買票進去時才發覺皮包不見了。那次我們走遍塞納河兩岸的大街小巷,報警、辦新護照、簽證、取消所有信用卡,再趕飛去布達佩斯。開完會有個惜別盛宴在皇宮舉行,當我們去赴宴,剛上車就有旅客大喊「My wallet, my wallet(我的錢包,我的錢包)」,又是錢包被扒走,火車已動,他還是跳下去找錢包,那情景真是終身難忘!一九八八年是他第九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中國之行。在西安因擠公車也被扒走皮夾,損失慘重,裡面還有一張他心愛的全家福,故事也上了報紙。他從年輕時就有個習慣,把喜愛的雜誌或自己的文章放在背包或大褲袋子裡,隨時可以閱讀。一九九○年在台北,還因有這習慣,而物歸原主。這次他不需要取消與重新申請任何卡片,所以最近我才從他的剪報夾裡的一篇文章得知。他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是二○○八年,中國的詐騙集團賣「黃金」賣到他的辦公室。這個集團一定是專業的慣犯,並且也許跟昆大孔子學院有關,因為騙徒太瞭解他,連他的思想,親台反中共都知道。他們避開家裡,用窮苦的工人、客家鄉親為藉口,到辦公室找他,詐騙手法、設計,天衣無縫,過程複雜,一言難盡。結果被騙了七萬五千塊澳幣。事後才覺可疑,還叫Mattel拿了一塊到台灣去驗是否真金。二○一一年大水災,那堆「黃金」全變成掩埋物。他一生都淡薄名利與錢財,每次被騙、被扒、被偷後都會自我解嘲,錢是身外物,就認為把它捐給窮人、救濟院好了。
二○○○年陳水扁打敗連戰,台灣政治奇蹟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二○○一年他再回淡江大學客座三年,他把所有時間、精力都奉獻給台灣,教學、開會、演講。他沒接受任何官位,不領政府薪水,卻無怨無悔的為台灣出國訪問,與他國政、學界對話、宣導政策。他還有幸被彭明敏教授看重,參加他主持的幾乎每年兩次的亞盟年會與會議,和很多國家政、學界人士交流。我也很榮幸地跟著他們,全球走透透。他常說和彭教授一起打拚,是我們人生的一大榮譽與快樂。
想起一九六○年代我們在台大時看過的,由華倫比提和娜妲麗華領銜主演的電影《天涯何處無芳草》(Splendour in the Grass),這首詩來自華滋華斯的〈頌:永生之暗示〉。誰也不能使時光倒流,但願來生,我們仍能携手前進。
頌:永生之暗示
也曾燦爛輝煌,而今生死兩茫茫。
儘管無法找回當時
草之翠綠,花之芬芳。
亦不要悲傷,要從中汲取留存的力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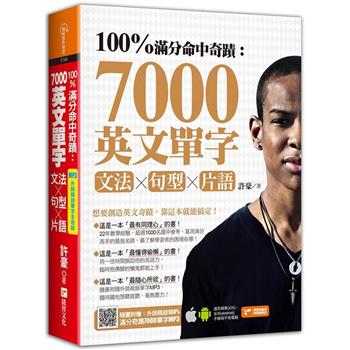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