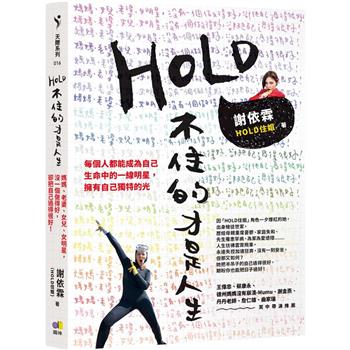楔子一
清順治三年,鄭成功開始了與清朝的抗爭,歷經無數戰役雖有勝負,可最終於順治十八年,因南京之役大敗退守廈門、金門。同年,鄭成功轉而攻取臺灣,深知眼前局勢不宜正面交鋒便由明轉暗,建立「天地會」組織,由軍師陳近南擔任總舵主,將反清復明的大業轉向地下行動。順治死後由康熙繼位,直至康熙二十二年由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兵收復臺灣,這才結束清廷與鄭氏王朝的多年鬥爭,但天地會並未因此消亡。
清朝與鄭氏一族的糾葛,讓天地會成了康熙的心病,清廷對待天地會只有一個態度,便是斬草除根。清廷的高壓清剿使天地會因為鮮血的灌溉而扎根更深,潛伏更深的天地會在清朝百餘年間,掀起更多的腥風血雨。
乾隆二十三年,位於湖南省一處隱蔽的小村莊遭官兵血洗,此時的陳家莊隨處可見殘破的屍身,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血腥味。
陳氏宗祠內,面容哀戚的中年男子跪坐在地,懷中抱著冰冷僵硬的妻子,不足一歲的孩子揮舞小手似乎想觸摸母親的臉龐,不哭也不鬧,可安靜的氛圍卻讓散不去的悲傷越發沉重。
一旁的青年率先打破沉默,「大哥,跟我走吧,官兵隨時會再攻進來,堂裡來的兄弟不多,我們擋不住的。」
中年男子沉默許久,隨後淡淡地問了句,「忠清,你說我既不曾入會,甚至躲起來隱姓埋名二十多年,可為何終究還是成了反賊?」
蔡忠清沉默,他已有了些猜測。大哥的父親曾是天地會總壇軍師,大哥自幼酷愛讀書不願參與天地會之事便未曾入會,更是十來歲便遠走他鄉隱居耕讀,知曉大哥身分的人屈指可數。
此刻清兵屠村,不僅只因窩藏天地會反賊,更因大哥乃是鄭王爺僅存的直系血脈,而知曉此事的僅有會中數人,且皆身居高位。蔡忠清雖不願相信,但最近正值下一任總舵主推選,加上數個堂口勢力間的紛爭,大哥只怕是因此被捲入其中。
蔡忠清看著結拜大哥,此時他更加不敢告訴大哥他父親身死的消息,若非老軍師死前託付,只怕蔡忠清還不知道大哥身陷殺機。
見蔡忠清欲言又止的愧疚模樣,他霎時明白了許多事,「終究是逃不過……」,男子看著懷中的孩兒眼眶泛淚,「難道秀兒非得過這種刀口舔血的日子……」
「大哥!不管如何還是先離開這裡吧,我會幫你找個地方藏身,以後你還要教秀滿讀書寫字……」
中年男子打斷蔡忠清急切的懇求,深吸口氣做出了決定,「帶著秀兒走吧,大哥只求你兩件事,除了教會秀兒讀書識字,務必讓秀兒勤修武藝,莫要如我一般……」男子輕撫妻子冰冷的臉龐。
男子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遞給蔡忠清,「將信物交給總舵吧,就說鄭氏再無後人,以後這孩子就隨他母親姓李,不要讓他知道自己鄭氏後人的身分,讓他遠離天地會的一切紛爭。」
「一起走吧大哥!現在還來得及的。」
「不了,我得留在這裡陪著繡妍,替我照顧好秀兒。」看著懷中的亡妻,他知道自己今日若是不死,定會牽連孩子和義弟。
「來人了!忠清,該走了!」祠堂外頭傳來一聲焦急地呼喊。
蔡忠清抱著孩子,臨走前最後回頭看了大哥一眼,四目相交的兩人作了最後的無聲告別。
乾隆二十三年,陳家莊因窩藏天地會反賊而遭屠村,賊首鄭亦勛自刎於祠堂之中。鄭亦勛為鄭成功一系後人更於天地會中身居高位,賊首伏誅令乾隆甚是欣喜,於此役有功者盡數獲得封賞。
清朝的追捕因鄭亦勛之死而告終,但天地會內部的紛爭還未結束,對蔡忠清懷裡的小傢伙來說,前途多舛的命運才剛剛開始。
在老軍師、鄭亦勛死後,天地會的派系之爭很快便有了結果,最終由陳長老登上新任總舵主之位。
陳總舵主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對老軍師一派進行打壓與清算。老軍師尚在時,憑藉其智謀手段及鄭氏暗衛,以其為首的派系在天地會中穩居首位。但也正因如此,才遭到其他派系的圍攻而落得身死的下場。
即便老軍師已死,他所留下來的勢力依舊為陳總舵主所忌憚,其中最首要的目標,便是鄭氏遺族及代表鄭氏直系身分的虎符玉珮。
在陳總舵主派人不遺餘力地搜查之下,帶著孩子的蔡忠清終究沒能躲過追捕。
襁褓中的李秀滿正躺在床上酣睡,蔡忠清心知肚明,面對眼前三名天地會長老,他絕無可能帶著孩子平安離開客棧。
「將孩子和玉珮交出來吧,你不可能從我們手中逃走的,沒必要為這事搭上性命。」胡嶽勸說道。胡嶽在總舵時和蔡忠清算得上相熟,若非必要他實在不願對這平日裡關係不錯的後輩出手。
「胡前輩的好意我心領了,玉珮可以交給你們,但只要我還活著,就絕不能讓你們帶走這孩子。」蔡忠清堅定表示。
「總舵主的命令便是如此,什麼時候由得你一介後輩討價還價了?放任這孩子流落在外,說不定會遭人利用引來禍端,由總舵保護豈不更安全,難道總舵主會對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出手?」面對蔡忠清的強硬態度,武峰感到有些不耐煩。
面對武峰長老的說辭,蔡忠清笑了笑,「說的倒好聽,要是讓這孩子落在總舵主手裡,怕是要淪為控制鄭氏暗衛的傀儡吧?」蔡忠清雖不喜老軍師行事作風,但是這場紛爭也讓他看清了,那些平日裡指責老軍師手段狠戾毒辣的前輩,也不乏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就算如此,不也能保住這孩子一命嗎?」胡嶽說道。
「這孩子是我結義大哥臨終所託,我就算拚上性命,也決不會讓他淪為他人手裡的提線木偶。」
「你賠上性命也打不過我們的,還會牽連孩子,你又是何苦呢?」胡嶽有些不忍。
「難道你們不知道陳總舵主為何要這孩子?你們和他不是一系,為何要助紂為虐?放過這孩子,由我帶著玉珮和你們一同回總舵覆命便是。」蔡忠清自知不敵三人,便出此提議。
胡嶽有些為難,就算他和師弟謝君實願意,但按照武峰的性子,他定不會違反總舵的命令。他知道蔡忠清說的沒錯,但若真的放他們離開,武峰長老定會將這事報上去,屆時會連累其他兄弟受罰。
「冥頑不靈!既然想找死那便成全你。」武峰是個急性子,見蔡忠清執意如此,便打算出手解決此事。
蔡忠清也不打算坐以待斃,同時面對三名長老的巨大壓力,讓他的神經如繃緊的弓弦,不只是對手強大,更因他身後床榻上有著正在酣睡的李秀滿。
「燎原勁」全力施為,蔡忠清全身赤紅真氣翻湧,面對毫無勝算卻絕不能敗的一戰,他願意犧牲一切,只要能守護那孩子。
戰火一觸即發,就在這時,先前不發一言只是冷眼旁觀的謝君實率先出招,一記重掌打在了武峰後背,掌力貫通胸背,武峰心脈寸斷,轉過身來不可置信地看著謝君實,喉中的鮮血讓他沒能說出一句話便倒下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蔡忠清有些不知所措。
「師弟!你這是為何?」謝君實突然出手讓胡嶽又驚又怒,無故對會中兄弟動手要受三刀六洞的極刑,他不明白謝君實為何如此。
「我認為蔡忠清說的對,讓這孩子和玉珮落在陳總舵主手裡,對天地會來說未必是件好事,只怕會造就另一個老軍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謝君實淡然說道。
「那你也不應該對武長老下手啊!」胡嶽急道。
「武長老不死,受到刑罰的便是我倆,況且,我已有盤算。」
胡嶽有些無奈,這個師弟向來如此,心思深不可測,一旦決定的事情便沒有人能說動他,他這個師兄是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事到如今,你有何打算?」
「將武峰和這孩子的死嫁禍在別的派系頭上,讓陳總舵主和他們鬥去吧。武峰所在一系向來不參與派系間的權力鬥爭,現在武峰一死倒是可以藉此設局,讓他們一系和我們合作,去對付其他派系。這幫喜歡爭權奪利的傢伙,是時候整頓一下了。」
胡嶽一驚,不知道謝君實是什麼時候連武峰的死也計算在其中。他們所在的派系和武峰身後派系一樣基本上處於中立,胡嶽也看不慣前些日子,爭奪總舵主之位時所發生的那些事,但謝君實算計武峰身死一事的狠辣果決,仍讓他感到心驚,只不過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再多說什麼。
謝君實看向蔡忠清,「我可以放你們離開,但你必須答應我兩件事。其一,讓這孩子加入天地會,往後在某些重要時候,或許還需要靠這孩子和他身後的鄭氏暗衛出手相助。其二,讓這孩子躲在臺灣,離總舵越遠越好。」
「第二點我不反對,但是第一點,讓他加入天地會可以,若想要這孩子用他的身分調動鄭氏暗衛,必須他自願做這件事才行。」
「可以。」
雙方達成了共識,約定好聯繫方式後,蔡忠清便帶著李秀滿離開了客棧。
「你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又為何非要讓那個孩子待在臺灣?」按照謝君實的性子,胡嶽不太相信他是動了惻隱之心才放過那孩子,他肯定另有打算。
「鄭氏不可無後,那孩子有他該背負的命運和責任,在他成人前離總舵越遠越好,臺灣是個適合的地方。」謝君實解釋道。
胡嶽半信半疑,但到底是救下了一個無辜的孩子,他便不再多問。
離開客棧的蔡忠清看著懷中李秀滿的小臉龐,想起先前謝君實那深不可測的模樣,不禁懷疑自己答應那些條件是否正確。
「本來答應你爹不讓你參與天地會這些破事的,不曾想還是食言了。不過幸好還能留下這塊玉珮,給你留了點念想,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蔡忠清將玉珮放在李秀滿的小臉上,小傢伙對這塊暖玉打造的玉珮甚是喜歡,緊緊抱著溫暖的玉石沉沉睡去。
一、城中詭事
乾隆四十九年,一個燠熱的午後,淡水廳竹塹城內,同知大人潘凱在衙門後頭的書房裡,正埋首在卷宗之中,和師爺忙著清點帳目,煩惱著土地丈量的事情。
炎熱的午後確實令人提不起勁,前頭當值的衙役找著一處涼蔭,正低著頭打盹,值班的捕頭陳寶昇也待在一處舒適的地方,隨手翻著一本破舊的雜書打發時光,和後頭忙得焦頭爛額的同知大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都說來臺做官「三年官,兩年滿」,要想當好這流水官,除了得和那些鐵打的豪紳打好關係,如何和手底下這些萬年差吏相處也是一門學問。自己吃肉也得讓人喝點湯,還得知道哪些不起眼的小吏是哪家安插進來的樁,除了得捋清關係,更需懂得人情世故的往來,否則豪紳們不僅不願掏出錢來,手底下的人再給穿穿小鞋,這正五品的官員也得灰溜溜地走。在臺灣,當官的要想從這些豪紳手裡掙得滿載而歸,那就得比商人還商人。
不過在書房裡忙得不可開交的潘凱,顯然不是這一路貨色,自赴任淡水撫民同知以來就和當地的豪紳不對頭,土地清丈、修定漢番邊界、清查港口進出等諸多舉措,無一不是從豪紳手中奪利,這讓一眾豪紳對這新來的同知可謂恨之入骨。
然而要在這塊積弊已久的土地上整頓吏治,其險惡艱困超乎想像,要實施這些政令,手底下就得有信得過的人。整個府衙自上到下人員已換過了一輪,能留下來的要嘛是些得罪過豪紳和他們有仇的,要嘛就是沒有關係和門路,純粹靠本事待在衙裡混口飯吃的。
對於這些人而言,不用迎合主官或擔心得罪有關係的同僚,不用再為被扣克薪餉和承擔些累差而頭疼,只需要在主官有令時將事情辦妥,其他時間同知大人可謂不聞不問,像這樣悠閒懶散的日子可說是潘凱上任後,衙門裡的日常。
一道匆忙慌亂的身影,一邊呼喊著一邊闖進了衙內,打破了午後的悠閒寧靜。
「殺人啦!殺人啦!有殭屍出來咬人啦!」一名神色驚恐的青年大聲嚷嚷道。
衙役們眼看這人衝撞公堂,唯恐驚動後院裡的大人便起身去攔,青年一身腱子肉,一看便是幹體力活的,慌亂下加之衙役們剛才還打著瞌睡呢,竟是兩三個人也沒能攔得住他。
陳寶昇見狀便起身上前,不疾不徐的將雜書收進懷裡,稍稍運氣,朝著青年的幾處穴位一拍,將慌亂的氣息給拍散了去。
「年輕人!放輕鬆點,有什麼事慢慢說。李二!去倒杯茶來。」
青年被幾掌拍矇了過去,喝過水,順順氣之後鎮定了許多,這才將事情的原委緩緩道來。
「你剛說有殭屍咬人是怎麼回事?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在公堂之上可不許亂說,胡亂造謠可是要被定罪的。」
「這……」面對陳寶昇的質疑,青年有些不知所措。
「你先說說你叫啥名字,住在哪,幹啥工作。」
「回差爺,草民黃嘉,在城裡頭幹些粗工雜活,住在城外崙子莊。」
「那你為何來報案?將事情的經過如實道來,別扯些殭屍啥的,就說說你看到的。」
黃嘉回憶起事情的經過,「我和幾位一起幹活的兄弟同住在崙子莊的一處院子裡頭,離著院子不遠處住著一對義兄弟,大哥名叫柴隆,小弟名叫黃平,只知道兩個人感情不錯,和咱們一樣在城裡幹活的。」
「死者可是兄弟其中一人?」
「恐怕……兩個人都死了。」
「發生了什麼事,接著說。」
「起初好像是柴隆得了瘋狗病,請了好幾位大夫怎麼也治不好,黃平只得四處找藥來醫治。這事還是黃平外出買藥時,拜託咱幾個替他照看一下他大哥時親口說的。」
「你和他們兩兄弟相熟嗎?你們有親眼看見柴隆的病況嗎?」
「也不算太熟,以往出工的時候見著面會聊幾句,畢竟住同個莊子。後來有很一陣子沒見到兄弟倆,等黃平來拜託時才知道原來柴隆已經得病多時了,怪不得好一段時間沒見著他們。咱去照顧柴隆時可嚇人了,那時他已經神智不清,有時還會暴起想要咬人,得兩三個人制住他,餵他吃藥才能好轉,真不知黃平自己一個人如何應付得來。」
「照你所說,這柴隆不過是得了瘋狗症,何來殭屍一說,莫不是胡編亂造!」
陳寶昇語氣有些嚴厲,讓黃嘉有些發怵。
「這……不是我胡亂造謠,我那一幫兄弟可都聽見了,昨晚那動靜……確實是殭屍咬人哪!」
「你說昨天晚上?」
「是啊!我們好幾天沒見著黃平了,昨晚他們家鬧出好大動靜,怪嚇人的,吵得我們整晚都沒睡。今天早上大伙商量著過去看一眼。屋裡頭可嚇人了,到處都是爪痕,就像被猛獸給襲擊了,滿屋都是血痕還有碎肉……大人,這柴隆……不會是變成殭屍,將黃平給……」
「這麼說來你並未見到兩人的屍體,你如何肯定他們已經死了?又何來殭屍一說?」
「唉呦,那是你沒聽見昨晚那詭異的吼叫聲!我們這幫兄弟平時也進林子裡打些野味,哪裡有甚麼猛獸會發出這種聲音?再說了,我們親眼看到地上有幾根人的指頭,四周又只住著他們兄弟,只怕他倆已經……」
陳寶昇聞言臉色一沉,最近城外不太平靜,今天這事不是第一次發生,已有好幾起像這樣,住處偏僻又沒有親人來往的人遇害消失,只不過也沒人因此來報官立案,最後都不了了之。陳寶昇可不信什麼殭屍一說,這定是兇嫌有心刻意為之,挑選過被害人造成的結果。可既無人報官立案,同知大人多半也是交代人去查驗記錄便草草做結,渾然不顧這事已經鬧得有些人心惶惶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山中邪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推理/驚悚小說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驚悚/懸疑小說 |
$ 342 |
華文推理/犯罪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80 |
推理\犯罪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山中邪神
「那是殭屍,一定是殭屍!大人,我真的沒有亂說!」
當天地會遇上詭異的殭屍,反清復明大業最腥風血雨的一役!
★2021年第一屆謎團小說獎 優選
★清代五品命官潘凱砍頭案魔改武俠
★官場算計X江湖恩怨X蠱術煉屍
竹塹城外出現離奇命案,
捕快李秀滿在查案過程中遇上力大無窮的蠱屍,
不想其背後竟有白蓮藥王、林爽文勢力涉入,
更意外捲入重重謎團!
乾隆年間,臺灣竹塹城外發生一起命案,由於現場沾滿血跡、斷肢四處散落,報案者信誓旦旦說是殭屍殺人。與此同時,隱身衙門的天地會成員李秀滿在圍剿盜賊時,遇上堪稱金剛不壞之身的黑衣人,好不容易將其絞殺後,卻發現其中一人生前只是個農夫。這是什麼邪術!?
另方面,中國天地會的三位長老秘密來臺,想追查躲藏在深山的白蓮藥王行蹤,確認他是否真有能夠回春的蟠龍草。為了用此草藥籌措反清復明的糧草軍資,天地會三人隨同番人嚮導進入深山......
不久,有人通報在山中發現三具無頭屍,更有線索指出死者可能為天地會成員,同知大人潘凱率隊前往調查,卻因此招來殺身之禍!誰敢殺害朝廷命官?三具無頭屍是誰?死因為何?與其他命案又是否有關聯?
先是殭屍出沒、同知遇襲,現在又疑似有天地會弟兄遇害,李秀滿痛心之餘只得深入調查這一連串事件,不料卻陷入天地會內部的權力鬥爭。當揭開詭屍的真相時,面對自身的責任與使命,他該如何抉擇?又該將天地會帶往哪條路?
真正可怕的,是屍傀?或是人心?
作者簡介:
墨鹿客
彰化人,多媒體應用學系畢業。
喜歡各種類型的故事並且載體不拘,遊戲、影視、小說……等都喜歡。
雖然涉略廣泛不過「武俠」始終是心中的第一位。
時常將光怪陸離的夢境紀錄下來,編成故事。
相信故事中人物的悲喜都具有現實意義,到一個有溫度的故事裡歇一歇,能更好的面對冰冷的現實。
希望能持續寫下令自己滿意的故事,若是能令駐足的旅人獲得些許溫暖那就更好了。
章節試閱
楔子一
清順治三年,鄭成功開始了與清朝的抗爭,歷經無數戰役雖有勝負,可最終於順治十八年,因南京之役大敗退守廈門、金門。同年,鄭成功轉而攻取臺灣,深知眼前局勢不宜正面交鋒便由明轉暗,建立「天地會」組織,由軍師陳近南擔任總舵主,將反清復明的大業轉向地下行動。順治死後由康熙繼位,直至康熙二十二年由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兵收復臺灣,這才結束清廷與鄭氏王朝的多年鬥爭,但天地會並未因此消亡。
清朝與鄭氏一族的糾葛,讓天地會成了康熙的心病,清廷對待天地會只有一個態度,便是斬草除根。清廷的高壓清剿使天地會因為鮮血的...
清順治三年,鄭成功開始了與清朝的抗爭,歷經無數戰役雖有勝負,可最終於順治十八年,因南京之役大敗退守廈門、金門。同年,鄭成功轉而攻取臺灣,深知眼前局勢不宜正面交鋒便由明轉暗,建立「天地會」組織,由軍師陳近南擔任總舵主,將反清復明的大業轉向地下行動。順治死後由康熙繼位,直至康熙二十二年由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兵收復臺灣,這才結束清廷與鄭氏王朝的多年鬥爭,但天地會並未因此消亡。
清朝與鄭氏一族的糾葛,讓天地會成了康熙的心病,清廷對待天地會只有一個態度,便是斬草除根。清廷的高壓清剿使天地會因為鮮血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楔子一
第一章 城中詭事
第二章 暗流湧動
第三章 引君入彀
第四章 十面埋伏
第五章 兔死狗烹
第六章 靈藥現跡
第七章 藥屍活傀
第八章 部落之殤
第九章 窟藏百骸
第十章 青紅皂白
第十一章 長夜將盡
第十二章 明曦未生
楔子二
第一章 城中詭事
第二章 暗流湧動
第三章 引君入彀
第四章 十面埋伏
第五章 兔死狗烹
第六章 靈藥現跡
第七章 藥屍活傀
第八章 部落之殤
第九章 窟藏百骸
第十章 青紅皂白
第十一章 長夜將盡
第十二章 明曦未生
楔子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