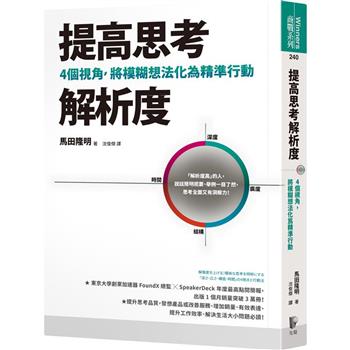圖書名稱:帶著你的雜質發亮
我早在漂移 像一個出海的夢 在過去之間漂移
I've been drifting
Like a dream out on the sea
I've been drifting in between what used to be
- 截錄 Tim Buckley, 1969 , “Driftin' "(漂移), Album: Live at the Troubadour.
要去法院註冊的前一天我在被窩裡哭。 我不想住在這裡。一間沒 有陽光的房子。我住進我先生的房間。一間放了一張加大單人 床。一張書桌。一個書櫃。一個衣櫃。一個沒有辨法走動的空間。 我先生很高興把我放在他家。他跑到外地上班。他很高興我能 在家裡陪他退休的老母。
那時我關在房裡畫了這張畫。在無法走動的空間擠了支畫架及 三十號的畫布。我在這間家沒有味道地走進,走出。
看著自己把一片片的空間,刷成了灰色。 他們冷冷地看我的畫在客廳晾乾,傻傻地看著。
-而,故鄉是母親留給你命中的一塊糖
多年前母親收起我出發那天的日曆
像樹一樣矗立著目送我上車
多年來鄉愁從唇邊漫溢出來
黏在我肌膚上 源源不絕地滋養著我
它們溶化長成了一棵樹
搖著我 撫摸我
01故鄉是母親留給你命中的一塊糖
我知道母親和我說,發亮去吧,帶著你的雜質發亮。
我沒有辨法和任何人長期共處,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身分。一種逃離在外的身分。我喜歡這樣冷卻的過程。這樣稀釋的過程。因為注定會有死別,我預習。離開又見面叫你懂得珍惜,叫你去選擇記得更多的美好。慢慢的,我不再對相聚特別的執著,不再對共處一室特別在意。
我媽媽一整天都在勞作。做家事、種田。我到家的時候,她總是煮湯麺給我吃,我將行李箱扛進一間很久沒人睡的房間,那也許曾是弟弟的房間,也許曾是姑姑的房間,也許也曾是我的房間。離開的時候,我會將房間打掃好,物歸原位,扛著我的行李箱去坐車,到機場,到另一個國境,打電話給她,說,媽,我到了。然後大概隔了半年或一年我又打電話給她,媽,我幾號要回去。
我念美術系。她都說我畫的不好看,我一點都不介意。她有時會說誰誰誰的孩子在台灣賺多少錢、多好多好;我一點都不在意。她總是叫我不要買書,我卻越買越多。最後她花錢買了一個大書櫃來裝我的書。
她喜歡實用性的果樹。一整天蹲在楊桃樹下將一顆顆小楊桃包起來。即便如此,這些果實還是布滿瘡疤,尤其在結蒂處總有一堆白色的蟲卵,或是褐色如傷口的結疤。我吃著這些難看的水果長大。沒有幫她包過一次水果,沒有幫她鋤過草。我對這裡完全沒有貢獻。她放任我像旅人一樣,像野貓一樣。
在家裡我沒有自己的房間。因我總是在外。中學六年我在學校附近租房間住。幾乎每年搬一次。她總是幫我搬家,幫我收東西。每個週末我回家吃飯睡覺。要走的時候,她都會切一包水果給我。那時候,我已經懂得自己洗衣服。國小時我住奶奶家,每回假日她來,要幫我洗一整桶的衣服,手洗,水一直嘩嘩地流著,還有刷子涮涮的磨擦洗衣板,我卻只是躲在房裡,靜靜聽著這一切聲音,沒有出去幫她,她也沒有喚我。
我媽媽作菜比餐館還快,她老是在做事,一堆做不完的事。我扛回家的行李箱,裡頭的衣服亂七八糟,當我外出一陣回來,赫然發現一件一件整整齊齊地摺好,該熨的也熨過了,還有一件破了個洞,已經補好放在縫紉機上。她到台北來,刷我的浴室;一件一件依顏色摺叠好我老是凌亂的衣物。還說,妳買的衣服都不好看。
小時候喜歡跟著她,她走到哪,我都愛跟著,靜靜地跟著,很小的時候有次跟丟了,哭著,她走過來,用沾了口水的手帕擦我的眼睛。她總是騎腳踏車載我,長大了一些,我騎另一台跟著,跟著她去買雜貨,跟著她做小生意,那時我心想,一直跟著,就永遠都不會失去她。
小時候的照片裡,我一定是怯生生地拉著她的衣角。她不在時,便想著她,甚至幻聽見開門的聲音,甚至因過於害怕失去她,作了她死去的夢,那樣地小,卻要那樣地擔心。那樣早熟的擔心,原來在那時便起了頭。而我後來才發現,每一年,都在擔心她的離去。
從留學台灣一直到揹上了這一場異國婚姻,我一再地離開她。她成了凝結在腦海裡的一朵冰塊,遇熱就溶化,我必須小心控制著溫度。離開表面上成了麻木的機場。每離開一次,我的心不是越堅厚,而是越來越地薄、越來越地纖弱。年歲的增長增添了我的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鄉愁,曾經我引以為恥的鄉愁變成了緊貼在皮上的一塊疤。
我媽媽沒教我幾件事。她不教我作菜,不叫我作家事。她什麽都沒教我,老是自己在做。我用盡力氣想到的只有兩件事,她教我騎摩托車,教我踩縫紉機。但我縫的東西醜之又醜,上不了檯面,我在生活上的能力弱之又弱。因此,若我進入了一個傳統性特重的家庭,我注定被嫌棄。
我不光被嫌棄,還沒有辨法習慣城市。我沒有辨法習慣坐公車、捷運,好像被吞沒一樣。我不光滑,我說話不若你們溫柔,太粗,我不如你們的溫和圓滑地待人。彷佛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樣粗糙。我不服從這座城市。
十九歲的時候,我開始在這座名為台北的城市求學。我只買一件一百塊錢的衣服,冬天便一件一件地亂套。因為沒有好的冬衣,我討厭冬天。離下課還有一個小時我就溜出去打工,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回到宿舍。上課的內容不吸引我,老師不吸引我,同學不吸引我。我作畫速度很快,作功課也是。我過了四年像河一樣的生活,沒什麽特別的味道,但流動著。我不特別高興畢了業,看不起畢業典禮。我帶著空白離開。這空白像夾在書頁裡的花瓣,枯竭的褐色汁液,已經失去味道的扁平花瓣,殘留在我心裡頭。
那個時候,我開始想畫一種沒有什麽顏色的畫,有一些文字。我長著一雙憤懣的眼睛,叫人害怕。我成了一張沙漠,常缺水,亁涸,都是沙子,不斷流失水分;像洩氣的大氣球,把什麽都放掉。我嫌棄那時候,嫌棄那所大學,那裡面所有的人。我體內張牙的那些雜質推擠著我,我卻無處可去。
大學畢業後,我為了居留跑去結婚。我厭惡那張有限制期限的證件,我無法理性處理這種事。大學裡空白的那枚褐色印記,漸漸被雨水飛濺、滲透而癱軟。那個時候愛情只是異鄉的一種方便性,我不相信那是一張真的愛情。我原來以為愛情她是貼在我傷痕上的矽膠片,貼近而柔軟,可以一洗再洗,安靜地護著我的傷,直到她平整。結婚後那傷痕卻開始隆起,長成一塊疤,一個黏在我肉體上的疙瘩。我有時可以聽見那塊疤在跟我說話,癒合起來嫩紅的一張唇,乳色的單薄。沒有人願意貼近它。
我知道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種滿是瘡疤的果實。我其實一點都不平滑誘人。我沒有辨法去理解愛情,因為愛情她肢解了我。我沒有想到這張婚姻不請自來了巨大的晃動。在我的畫作裡,悲傷就坐在那裡,大剌剌地,剎那之間讓我難堪,我無法注視自己的畫太久,故鄉與愛情的撕裂,碎成一地,徹骨,且孤寂,是沒有人的下著滂沱大雨的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