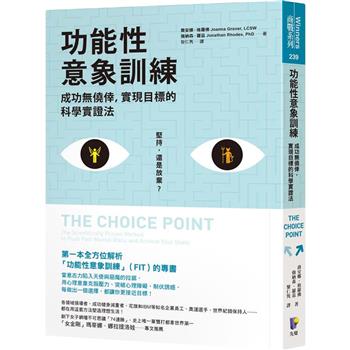即便是非營業時間,午後三點的水底寮菜市場還是太過安靜,連經常在傳統市場奔竄的水鼠都不見蹤跡,不知道這算是難以言喻的淒清,或是死神壓境帶來的窒息感,月雪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積水,深怕踩到蟑螂踢到老鼠。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每一步幾乎都是低頭盯著地板慢慢走出來的。
眼前的「榮旺號」魚攤就像某個旅遊書介紹過的景點聖地,從來都只能看著照片想像,如今親臨現場,胸口難以撫平的情緒隨著血液奔流而鼓譟著,耳根跟雙頰都開始發燙,月雪還記得這種感覺,她正細細地品味著每一次心跳帶來的衝擊,她當然知道必須趕緊調整心態,不能讓自己太過激動,不然她怎麼對得起靜芳那三天沒能好好休息,為了照顧她崩潰的精神狀態,忙裡忙外準備三餐,還得幫她應付學校跟謝文哲的日子。
魚攤的對面,雞鴨禽鳥攤位隨地散落著十來個生鏽的雞籠,快要鏽壞的鐵柵上沾黏著看似微不足道的雞毛,活雞放血的時候沒來得及啼叫,倒是失禁的雞糞雞尿灘了一地,月雪抬頭看著水底寮菜市場的鐵皮屋頂被海風刮落,鹹氣陣陣分不清是海風還是鏽味或血味。難以辨別真假,看似虛幻不實但又能困住肉體的奇怪空間,月雪認為那是她腦中零碎而殘缺的創傷記憶,正巧被陳林淑芬片片斷斷的資料襲奪了,導致過多的幻視與幻覺干擾了她對現實世界的判斷力,也誤導了她的感官神經,憑空妄想出一個用以逃避現實壓力的世界。每個人心中多少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會經歷一些難以修復的傷痛,無論是否求助醫生,都得要花上許多時間慢慢經歷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而後接受的五個階段,才有機會讓心底的沉痾曬見陽光。有些人會停在其中一個階段無法繼續往前,也有人即使走過了五階段,還會需要再進入下一個五階段。
雖然頻繁地看見從前跟李嬌爭吵的畫面,還有李嬌飄忽無蹤的幻影,但是在月雪接手陳林淑芬的案子之前,三十餘年來從未發生過類似的幻視幻聽等幻覺,更精確地說,「李嬌」這個名字,早在月雪轉學考錄取波士頓大學心理學系的那一刻起,或者稍晚一點也就是金流中斷導致月雪必須打黑工,被迫露宿街頭那天開始,理應徹底從月雪的生命中失去影響力,成為一個沒有意義,不再與月雪有任何關聯的名詞,月雪甚至頗自豪連惡夢都不曾遇見李嬌。
當幻覺發生的時候,月雪的遲疑大過於驚嚇,她不認為李嬌足夠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所以也相信自己沒有嚴重到必須迫切尋求醫療協助的程度。
月雪曾有想過,該不該為了陳林淑芬的案件,打越洋電話回母校,問看看指導教授漢娜會給她什麼專業建議。月雪還記得漢娜曾經在課堂上,還有私下指導Meeting的時間都講過,當初她協助聯邦調查局研究大艾德(Big ED)的案子,花了她不少時間調整對連續殺人犯、強姦犯等犯罪行為的界定方式,這類無法停止犯罪的嫌犯,往往都是有組織性地思考如何安排殺人計畫,還會經歷一段相當漫長的心理變化,所以在犯案之前都有一些跡象或徵兆,足夠讓警方有機會在社區預先佈下防護網,提前掌握高危險的嫌犯及可能的受害者。
例如那位連續殺了六位女大學生的大艾德,他坦承小時候經常虐殺小貓,把貓釘在木板上,然後砍下貓頭取樂。如果這樣的事件提早被慎重看待,說不定有機會扭轉大艾德的性格,或阻止大艾德的連續犯案。
深知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大艾德對監獄裡一成不變,必須被管控監視的生活感到十分滿意,他很樂意配合漢娜跟探員的訪談,他的口述資料,是漢娜研究犯罪者與性侵害案件的一個基準點,大艾德成為聯邦調查局對相關嫌疑人的鑑識標準,預防犯罪的措施也都是從大艾德的案例進行發想的。
成年後的大艾德都是邊開車邊尋找下手的對象,他會誘騙女大學生上車,極其暴虐地將之殺害;他還會姦淫屍體,而且特別喜歡對砍下的頭顱進行口交,當他逞完淫樂後,就會將遺體肢解棄屍。
童年即展現暴力傾向,會針對特定族群進行的誘拐手段,還兼具戀屍或蒐集癖等要件,大艾德儼然就是最標準的連續殺人犯範例。不只如此,他最後還對親生母親下了狠手,用榔頭擊碎母親的腦門並砍下母親的頭,割下母親嘮叨的舌頭,劃開那副總是要針對他發出苛薄言論的聲帶,丟進廚餘處理機,激動地按下啟動鍵,熱血沸騰地聽著攪打肉團與軟骨發出的雜音。
那都是他早就想回嗆母親但卻不知道怎麼開口的話。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腥紅速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5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推理/驚悚小說 |
$ 334 |
驚悚/懸疑小說 |
$ 342 |
華文推理/犯罪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80 |
推理\犯罪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腥紅速寫
真實案件改編:臺灣治安史上第一起隨機連續殺人
最惡女魔頭與犯罪側寫女學者的心戰對決
「不可以吃陌生人給的東西!」
場景宛如知名電玩《沉默之丘》
★睽違四年,推理小說家唐墨精心之作
★改編自屏東枋寮陳高蓮葉連續毒殺七名學童事件
★為謎團小說獎獻上的教科書等級示範
★劇本已同步完成
1986年,水底寮接二連三發生學童暴斃死亡的事件,兇手神出鬼沒,讓警方疲於追查不相干的嫌疑犯,樸實的小漁村從此被壟罩在未知的恐懼之中,長達一年的時間,造成七名學童受害。
「身高普通,年紀不超過四十,已婚,當地人,應該是女性,是個外表相當不起眼的婦人,有生育小孩的經驗,她跟受害小孩的父母們應該很熟。家庭主婦,或者她的工作相對單調,讓她有時間對放學的學童們下手。」
「只是一張照片妳就能看出這麼多資訊?」
王月雪是美國聯邦調查局顧問學者漢娜所指導的得意門生,回國第一個經手的案件就是水底寮連續殺人案,不僅能針對犯罪案件進行速寫,在入監面會採訪過程中,月雪還看見地獄般的景象,恍惚的幻影,穿梭在月雪的研究室跟牢房之間,瀕臨精神崩潰的學者,要如何與連續殺人犯鬥智?
作者簡介:
唐墨,本名林恕全,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疑案辦網站內容主編。單口喜劇演員。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高野山真言宗僧人。曾獲林榮三小說獎、入圍臺北文學獎年金、文化部創作補助、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勵。出版小說《清藏住持時代推理.林投冤桃花劫》、《清藏住持時代推理.當和尚買了髮簪》、《濃度40%的自白:酒保神探1》以及散文《違憲紀念日》。
章節試閱
即便是非營業時間,午後三點的水底寮菜市場還是太過安靜,連經常在傳統市場奔竄的水鼠都不見蹤跡,不知道這算是難以言喻的淒清,或是死神壓境帶來的窒息感,月雪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積水,深怕踩到蟑螂踢到老鼠。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每一步幾乎都是低頭盯著地板慢慢走出來的。
眼前的「榮旺號」魚攤就像某個旅遊書介紹過的景點聖地,從來都只能看著照片想像,如今親臨現場,胸口難以撫平的情緒隨著血液奔流而鼓譟著,耳根跟雙頰都開始發燙,月雪還記得這種感覺,她正細細地品味著每一次心跳帶來的衝擊,她當然知道必須趕緊調整心態,不...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每一步幾乎都是低頭盯著地板慢慢走出來的。
眼前的「榮旺號」魚攤就像某個旅遊書介紹過的景點聖地,從來都只能看著照片想像,如今親臨現場,胸口難以撫平的情緒隨著血液奔流而鼓譟著,耳根跟雙頰都開始發燙,月雪還記得這種感覺,她正細細地品味著每一次心跳帶來的衝擊,她當然知道必須趕緊調整心態,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部 重返水底寮
一、幻象
二、車過水底寮
三、媽媽在哪裡?
四、骨肉相離
五、一碗飯湯之後
六、挑戰媽祖婆
七、犯罪學通論
八、滷煮魚頭
第二部 女死囚現身
一、打城
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三、邀請函
四、手繪家園
五、魚塭底的故事
六、第八位受害者
七、轉骨秘方
一、幻象
二、車過水底寮
三、媽媽在哪裡?
四、骨肉相離
五、一碗飯湯之後
六、挑戰媽祖婆
七、犯罪學通論
八、滷煮魚頭
第二部 女死囚現身
一、打城
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三、邀請函
四、手繪家園
五、魚塭底的故事
六、第八位受害者
七、轉骨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