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只有黑夜的圖書 |
 |
只有黑夜 作者:約翰.威廉斯 出版社: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3-0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30 |
小說 |
$ 300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42 |
美國現代文學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英美文學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只有黑夜》是《史托納》、《屠夫渡口》、《奧古斯都》作者、1973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約翰・威廉斯二十六歲出版的第一本創作小說。這本書揭開了約翰・威廉斯終其一生處理「個人力量」和「命運偶然」間摩擦侵蝕的偉大寫作生涯。
亞瑟是一個神經敏感且對生命感到虛無的年輕男子。某天他收到久違未見的父親的來信。亞瑟對父親有著強烈的恐懼和厭惡,然而卻無法抑制與他見面的衝動。在他們會面之後,已是夜晚,亞瑟失魂地進到夜總會,他與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相遇,兩人喝著過量的酒、自然而然變得親密,但隨著他童年創傷的記憶浮現、勾起種種畫面。亞瑟的夜晚走向一場災難。
首次出版於1948年,《只有黑夜》是約翰・威廉斯的首部作品,彷彿希臘式無可避免的悲劇。故事以主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為時間軸,藉以訴說他童年曾目睹的暴力和創傷,成了他日復一日的惡夢,唯有黑夜是他的庇護。
「他忽然間相信,任何他有生之年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不能怪罪於他,因為他沒有行動過,他從來沒有做過出於自願的行動。某些莫名的力量推著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地方、推著他走一條他不想走的路、推著他進入連他都不想知道的不知名的地方。一切都是黑暗、都是無名,他走在黑暗裡。」
作者簡介│
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1922-1994)
出生及成長於美國德州。威廉斯雖然在寫作和演戲方面頗有才華,卻只在當地的初級學院(兩年制大學)讀了一年即被退學。隨後威廉斯被迫參戰,隸屬空軍,在軍中完成了第一部小說的草稿。威廉斯退役後找到一間小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並且進入丹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從1954 年起,威廉斯開始在丹佛大學任教,直到1985年退休。在這段期間,威廉斯同時也是位活躍的講師和作者,出版了兩部詩集和多部小說,著名的小說有:《屠夫渡口》(1960)、《史托納》(1965)及《奧古斯都》(1972)。《奧古斯都》於1973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譯者簡介│
馬耀民
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外文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曾任台大外語教學與資源中心主任(2006-2012)。博士班時候開始從事翻譯研究,一九九七年完成博士論文《波特萊爾在中國1917-1937》並獲得博士學位。多年來在外文系除了教授西洋文學概論、歐洲文學史、文學作品讀法外,翻譯教學也是他關注的重點,一九九六年開始連續教授翻譯與習作至今,從未間斷,曾領導外文系上具翻譯實務的老師先後成立了大學部的翻譯學程及文學院翻譯碩士學程,整合了台大豐富資源,讓台灣最優秀的學生獲得口筆譯的專業訓練,貢獻社會。他從碩士班修業其間即開始從事翻譯工作,除刊登於《中外文學》的學術性文章外,也曾負責國家劇院每月節目單的英譯工作,以賺取生活費,並奠定了翻譯教學的實務基礎。他從前年開始已經放棄教授文學課程,而專注於翻譯教學上,希望於退休前為翻譯教學能有更積極的付出,現教授翻譯實作、中翻英、文學翻譯,公文法規翻譯,以及在翻譯碩士學程開設筆譯研究方法。翻譯出版著作包括《史托納》、《屠夫渡口》、《奧古斯都》及《北海鯨夢》,《奧古斯都》獲2018 Openbook翻譯類年度好書,《北海鯨夢》獲第34屆「梁實秋文學大師獎」翻譯大師獎首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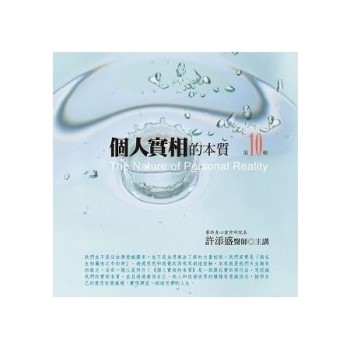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