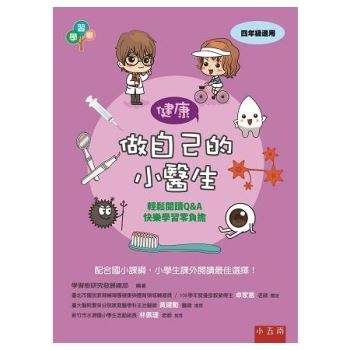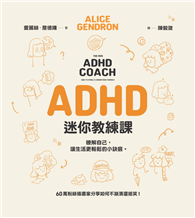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一章
奶奶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到故去活了九十二岁。一九六八年,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把奶奶从她生活的姑姑家接到我们居住的农村,又过了十二年直至她去世。按她老人家当时的打算,能活十年,但寿命的多少是个人不能决定的。我和奶奶感情一般,因为我一直欺负弟弟,奶奶一直偏着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奶奶的丧事,弟弟也回来了。奶奶故去的前前后后,我一直陪伴在家里。老人家身体不算太好,但九十多岁的人,尤其最后的几年,到家里看望的人总也不断。我的父亲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农机站打更,这个差事是我的一个表叔托人帮忙找的,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个表叔是奶奶的亲侄,他每年春节都来看望奶奶。现在奶奶故去了,自然要通知表叔。表叔的父亲是奶奶的亲弟弟,奶奶的丧事办的不算太隆重,但是,八十年代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农村对于丧事从简、一律火化要求得很严格。奶奶临终前一再叮嘱不要火化,当时父亲和我都暂时敷衍。当时我心里明白,实在要求严格,可以埋在自留地里。村上说了只要深埋,不立坟头,村上不追究。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办丧事,亲朋还是来了不少人,又加上八零年我家面临几桩大事:第一、父亲的“右派”身份获得平反;第二、我七八年参加高考已经上学; 第三、我弟弟结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来参加葬礼的人还是很多的。
亲属以外来的都算是朋友,父亲的朋友、我的朋友。父亲的朋友有一位是邻村的冯伯伯。据父亲讲,冯伯伯的家里很富庶,当然指的是旧社会那会儿。冯大概1920年生人,四十年代以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据冯伯伯说日本自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政府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归国有,按土地质量、数量,国民向政府购买土地,分期付款,实行土地货币化。据他讲这项国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政府设计,但未能很快执行,而且中国的“孙中山”也有土地改革的打算, 也学日本。不搞阶级斗争式的土地分配,农民最终都能得到土地,政府从中扮演土地分配的中介角色,用和平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政府避免了农民之间可能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纠纷。另外, 农民之间没有土地资产的纠纷,而且农民的土地有耕作的成本, 是有价值的劳动。这些分析是冯伯伯到我家与父亲谈话时我听说的,那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冯伯伯家虽然是地主成分, 但未戴地主分子的帽子。父亲另一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姓连,年龄小父亲两岁,应该是1927年生人,六二年到我们村上,是城市下放到农村的。那时我还没有到农村,我是六八年以后才到农村劳动,到农村以后认识的连叔叔。关于他的身份,父亲不让我详细打听,他的个人喜好是在劳动中逐步了解到的。又一次青年点的同学读宋词,其中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位同学无意中流露出来,他便顺口说道“红杏尚书”。以后同学们每每与其聊到唐诗、宋词,他也不回避我们,但他的出身一直不便问,只知道他回乡以前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六二年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才奔着农村的自留地回乡的。参加在自留地挖墓地的还有一位刘姓朋友,人们都叫他“红胡子”。他的胡须的确是红颜色的,人也像俄罗斯人,皮肤白皙。当时我们读《水浒传》记得有一个赤发鬼刘唐,现在看来赤发鬼可能真是外来族人或是少数族人。唐诗中有“胡姬押酒劝客尝”,那个时候阿拉伯人越过地中海和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人都纷纷到东方讨生活。这个红胡子是俄罗斯人后裔也未可知。他也是下放到我们村的城市工厂工人,可见在饥饿面前人们都难以坚持。中国六十年代前三年人的确整年没有机会吃上一顿饱饭。我记得六零年冬到六一年冬,不知吃饱是什么滋味,就渴望能吃上一顿饱饭。记得又一次红胡子说中午到家三个孩子没人给做饭,大孩子12岁、小的8岁,每个孩子拿一个玉米面饼子,吃一口饼子,拿大粒盐蘸水吃一口,他看到后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三个孩子跑着吃玉米饼子,争着往嘴里放大粒盐还挺高兴。红胡子是什么地方人我也忘记了,但他的原籍肯定不是在我们村,况且他孩子能吃到玉米面饼子,能吃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情况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可能是七二年或七三年。现在红胡子的孩子应该都过六十岁了。红胡子的孩子比我们幸运,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六二年、六三年出生的人回忆生活时有人说他只记得小时候吃到肉很难,买副食一般都要“券”,比如豆制品等等。提到吃肉,有一个下乡青年下地劳动脚踩在豆茬上扎了一个窟窿,医院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结果化脓了,后来医生从脚跟处查出一小节豆槎,知道了化脓的根源,伤算是治好了,但是伤口不愈合,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到北大桥黑市买一斤肉吃上就好了。我们下乡的村庄,农贸市场都取消了,北大桥实际是黑市场,有卖猪肉、羊肉和鸡蛋的。人们需要就悄悄去买,当时很贵,知青的脚不愈合,现在看是因为营养不良,果然,吃了肉不久伤口就愈合了。红胡子从城市的工厂申请下放到农村,我和他相处近四年,都在副业队,也就是农村烧砖瓦的窑地。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人,多半是农业生产不内行的。奶奶的丧事这些人也帮了不少忙。还有一个人,他并不在副业队劳动,但由于有共同的爱好,比如他在文学上的造诣, 使我很敬重他。我和他以及他的远房叔叔关系比较好。经二位肖姓叔叔介绍,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读小学时一次学校出现过一则“反动标语”,全校当作重大政治事件,上级限期破案,那时他才三年级,由于平时沉默寡言,成了被怀疑对象。学校组成了调查小组,放学不让他回家,一个孩子,校领导千方百计劝说威胁,告知“只要承认不给任何处分”。他经不住大人的威胁利诱,加上连续三天不让休息,不得不承认那起非他所为的政治事件。这事是十几年后我到农村才知道的,他告诉我他到初中以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没有意外考入高中应该不成问题。但,真的出了意外。初中三年级他的班主任姓张,给他做鉴定时非常含蓄地将这段陈年往事当作优点写入升学鉴定:该生很诚实,能主动向老师承认小学三年级时书写过反动标语的事实。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能放过这件事,谁又敢放过这类事情?就这样他没有升入县高中,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即使升入高中,也无法升入大学。因为六六年高中毕业生不允许考大学,全国统一停止了高考。他在与我的交往中表现出两个特长, 第一,对《红楼梦》的喜爱,金陵十二钗的诗烂熟于心;第二, 对陶渊明有深入研究。另外他对于自学日语也非常投入,功夫下的可不少。七八年恢复高考时我鼓励并动员他参加,由于他的婚姻变故,无论我如何再三鼓励,他都表示拒绝。如果他能参加当年的高考,是很有把握被录取的。就这样,一个很有希望成为大学生的有志青年,没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他是1946年生人,大我四岁,他的父母早年去世,他在农村生产队为队里到城市推销蔬菜,一个席店的部门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个女青年,两人结婚后日子过得不错,七六年诞下一女。但他的妻子受当地村民挑拨,带着女儿改嫁他人。他的晚年生活很不如意,十几年前我去过那个村庄,见过他,已经苍老很多。现在不知他的境况,但愿能比我想象中过得好吧!我参加工作时,在一所完全中学做教员,八二年,我班上有个学生叫钟士志,其父钟兴国。见到钟兴国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农村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钟士英,原来钟士英是钟士志的堂兄。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家长到我劳动过的农村向他哥哥讨要玉米。钟兴国的哥哥叫钟兴凯,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做教员,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被迫离职。钟士英还有一弟一妹,当时家庭生活窘迫,就向弟弟借了50斤玉米。结果弟弟前来讨要玉米,哥哥没有准备好,惹得弟弟很不高兴。刚巧我在钟士英家,见了当时的场面,便自告奋勇到同一个生产队一位哈姓的回族朋友处借了50斤玉米,总算化解了窘境。现在回想,为50斤玉米,兄弟可反目,都是那个时代的责任。城里和农村一样,为了生存,兄长可以不顾尊严,大有向人乞讨之尴尬。我与钟士英关系甚好,此事幸有回族哈姓朋友相助,这位朋友性格豪爽,平时又和我一起打球,因此我开口求助,其当即应允, 对此我记忆犹新。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儒道(簡體版)(POD)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2 |
文學 |
$ 432 |
文學作品 |
$ 456 |
中文書 |
$ 456 |
華文歷史小說 |
$ 456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儒道(簡體版)(POD)
章玺地因在家里是老大,抗美援朝每家必出一人参军,岑里明在家亦为老大,与章玺地同时参军,加入第三十九军,那是一九五零年的事。同年章与岑所在的部队被北朝鲜叛逃的一个团裹挟,被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俘获,中国却认为他们作战战死,于是由部队开出作战死亡证明。其实是台湾的人员将被俘的人员接到台湾,章与岑也不敢声张,只能听天由命,随遇而安……
谢明经从满洲国与其妻辗转到了当时的临时首都重庆,与同去的三十三人接受了培训,蒋先生那时还不曾动用这些人,故这些人都没有参加与日本的作战。抗战胜利后谢一直认为中国的军队必然能抗战直至胜利,所以一直没有携妻儿到南京,当准备携家人随大批国军退往台湾时已经来不及了。
作者簡介:
易中和,一九五零年冬月初十生人,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务农。一九七五年到海城油酒厂做临时工至一九七八年。同年参加高考,考入鞍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一九八零年分配到鞍山48中学做教师,一九八二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九九一年调入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九六年任中文系副主任主持系工作,一九九八年开始任鞍山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院长,二零零四年任学院图书馆馆长直至退休。现与夫人永居澳大利亚西澳洲珀斯与其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奶奶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到故去活了九十二岁。一九六八年,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把奶奶从她生活的姑姑家接到我们居住的农村,又过了十二年直至她去世。按她老人家当时的打算,能活十年,但寿命的多少是个人不能决定的。我和奶奶感情一般,因为我一直欺负弟弟,奶奶一直偏着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奶奶的丧事,弟弟也回来了。奶奶故去的前前后后,我一直陪伴在家里。老人家身体不算太好,但九十多岁的人,尤其最后的几年,到家里看望的人总也不断。我的父亲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农机站打更,这个差事是我的一个表叔托人帮忙找的,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个表叔是奶奶...
奶奶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到故去活了九十二岁。一九六八年,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把奶奶从她生活的姑姑家接到我们居住的农村,又过了十二年直至她去世。按她老人家当时的打算,能活十年,但寿命的多少是个人不能决定的。我和奶奶感情一般,因为我一直欺负弟弟,奶奶一直偏着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奶奶的丧事,弟弟也回来了。奶奶故去的前前后后,我一直陪伴在家里。老人家身体不算太好,但九十多岁的人,尤其最后的几年,到家里看望的人总也不断。我的父亲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农机站打更,这个差事是我的一个表叔托人帮忙找的,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个表叔是奶奶...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儒道》前言(代序)
这本书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但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能动笔,今年因为世界疫情,澳洲飞往中国的班机停飞,才腾出时间将以往的思绪总结成书。“儒道”的架构,其中有两个人颠覆了我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始思考我很小就形成的思想框架。动摇了我的思想认识。一九六三年年春节前后父亲带我分别到我的二爷爷家和我的舅爷爷家。
我的二爷爷是父亲的亲叔叔。由于爷爷去世得早,听父亲说他三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们家在腾鳌镇开了一家洋货商店,主要经营日本的搪瓷盆、碗等器皿。爷爷健在时与二爷爷和他们的父亲,即我的太爷爷共同经营。爷爷去世后...
这本书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但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能动笔,今年因为世界疫情,澳洲飞往中国的班机停飞,才腾出时间将以往的思绪总结成书。“儒道”的架构,其中有两个人颠覆了我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始思考我很小就形成的思想框架。动摇了我的思想认识。一九六三年年春节前后父亲带我分别到我的二爷爷家和我的舅爷爷家。
我的二爷爷是父亲的亲叔叔。由于爷爷去世得早,听父亲说他三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们家在腾鳌镇开了一家洋货商店,主要经营日本的搪瓷盆、碗等器皿。爷爷健在时与二爷爷和他们的父亲,即我的太爷爷共同经营。爷爷去世后...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儒道》前言(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