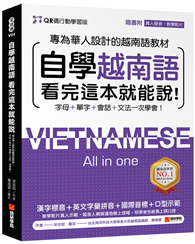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故事新編的圖書 |
 |
故事新編 作者:魯迅 出版社:新視野NewVision 出版日期:2023-08-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中文書 |
$ 252 |
近代文學 |
$ 252 |
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2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故事新編
內容簡介
《故事新編》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收錄魯迅在1922~1935年間根據古代神話、傳說、傳奇所改寫的短篇小說八篇,作品內容從古代的神話傳說到20世紀30年代的現實,涉及到許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情節,對古代流傳的文言短篇故事有精采的改寫和創作。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魯迅(1881.9.25~1936.10.19)
浙江紹興人,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1936年出版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該書主要以神話為題材,想像豐富,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演義的總集。
魯迅(1881.9.25~1936.10.19)
浙江紹興人,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1936年出版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該書主要以神話為題材,想像豐富,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演義的總集。
序
自序
這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卻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見,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茀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付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吳先生正在創造設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認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況且「如於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絕不能稱為佳作。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魂靈」回敬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裡,只剩著「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裡,對著大海,翻著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裡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卻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裡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花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為《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做一段速寫,卻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卻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魯迅
這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卻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見,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茀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付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吳先生正在創造設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認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況且「如於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絕不能稱為佳作。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魂靈」回敬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裡,只剩著「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裡,對著大海,翻著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裡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卻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裡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花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為《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做一段速寫,卻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卻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