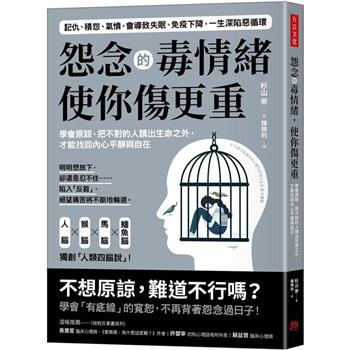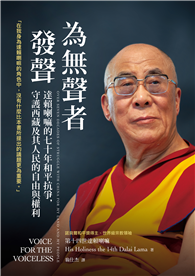〈大編輯〉
編輯往往被戲稱為「大編輯」,而要做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編輯卻絕非易事。有的編輯一輩子能改改錯別字就不錯了;有的編輯能改稿子也能做好選題;有的編輯能編能譯能寫能與作者譯者交流。這後一種就是名副其實的大編輯了。
這些話不是鄧蜀生的原話,但是你若有幸和他坐下來談談編輯這一行,你會深信這就是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理解和說法。幹一行愛一行的人很多,幹一行精一行的人也不少,但是幹一行能說一行並且能說到點子上的人就有限了,因為「說」的前提是說法,是觀點,是獨立,是自由,是思考……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當今大多數知識人所缺乏的。鄧蜀生不缺乏這些,也可以說他的強項就是這些。當初在版本圖書館認識鄧蜀生的時候,他是「老同志」中間最愛說的。如同稱呼所有的老同志一樣,我們年輕人都叫他「老鄧」。他喜歡對每件事情評說:小到柴米油鹽醬,大到國際時事。老同志中間有個叫陳步的,搞哲學,鄧蜀生愛和他討論辯證法。有時討論不了了之,鄧蜀生就會說:
「陳步呀,陳步,別人的辯證法是越變越多,你怎麼變來變去還是個單身?」
這時候,憨厚的陳步就嘿嘿一笑,把頭搖個不住。陳步的單身完全是因為他很年輕時就被打成了右派,不願意給別人帶來痛苦,就痛苦著自己。打倒四人幫後,陳步很快組成了家庭,過得很幸福。因為單身,陳步邀請我去過他家兩三次,給我燉海帶豬肉吃,順便告訴我如何搞選題。他做事很專業,所以老鄧和他討論哲學方面的事沒有優勢。有一次,老鄧又說陳步的單身身分,被領導馮黎雲聽見了,就替陳步說老鄧:
「鄧蜀生呀鄧蜀生,你這張嘴!」
後來很晚的時候,我才明白「你這張嘴」是指什麼。不過老鄧並沒有因此改變什麼,還是喜歡評說。老鄧最喜歡評說電影,我們很快知道他的老伴兒叫秦文,在《青春之歌》等電影裡扮演過角色,是更有名氣的演員秦怡的妹妹。有一次,老鄧問我以後找個什麼對象,我笑說:
「電影演員。」
「可別找!」
「為什麼?」
「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真哭什麼時候真笑!」
這話現在聽起來輕鬆,但當時正是四人幫猖狂的時候,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矛頭直戳戳朝著鄧小平去的。所以,老鄧的什麼話一旦讓領導馮黎雲聽見了,一準會說:
「咳,這個老鄧,瞧他這張嘴!」
不過,老鄧也有不評論的時候:比如我一旦說起農村農民糠菜半年糧的苦日子;農村各級幹部如何虛報產量;農民們如何在地裡只管混工分不管種莊稼,等等。我們認識的第二年,我因故回家探親,老鄧悄悄走到我的辦公桌前,塞給我五十斤全國糧票。
「別推卻,農村的情況我知道,糧票不多,但有比沒有強。」老鄧說。
何止「有比沒有強」?那時得到五十斤糧票,遠比得到五十塊錢難得多,而且全國糧票裡是含著供應的食油呢。老鄧出手大方一直使我感動,因為老鄧是一個生活非常樸素的人。他的自行車車筐裡總是有他買好的菜,冬天冷了還會裝些煤塊,給人一種十分生活化的景象。哪家副食店有什麼好的供應品,他還會在辦公室裡告訴大家。我那時對投入生活的人有偏見,以為心思操在吃喝上,業務必定放鬆。其實是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受煽動教育的蠱惑,不懂生活。老鄧熱愛生活,工作一板一眼。每逢我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掰開揉碎地耐心給我講解。一九七七年我們從版本圖書館重新分配,我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到了人民出版社,同在一棟樓裡上班。只要碰上,老鄧總是熱烈地迎上來和我說話,而且念念不忘打聽我們老家的情況。當我後來告訴他說,土地下戶後農村的飢餓問題解決了,他很高興地說:
「那就好,那就好!」
只要來我們這邊樓裡辦事,他就會到我的辦公室裡坐坐,問問我在幹什麼,還譯東西不譯。說來不堪回首,我在出版社遇上的每一個頂頭上司都不是學英語的,而外行領導內行總免不了吹毛求實瞎指揮,還有就是到更上一層領導那裡搬弄是非。因此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過得很難受:他們說我業務不行,但是我能搞來一個全國青年翻譯比賽的獎狀;說我業務好,那是外行做領導的大忌,還不如死了呢。但是老鄧一有合適的稿子,不是讓我業餘編輯,就是讓我業餘翻譯。每逢我把工作做了,他還總忘不了表揚我幾句。因為在一棟樓,我慢慢地瞭解到了老鄧的一些經歷。下麵只摘取兩項:
四十年代他先後在重慶《新民報》、上海《新民晚報》和《新聞報》做記者,曾到印緬前線實地採訪。他是中國唯一親身深入到作戰前沿的記者。
五十年代到新華社做記者不久,隨志願軍到朝鮮戰場上採訪,曾以鄧超筆名撰寫過多篇有影響的國際時事評論。
如今的記者,哪怕只有其中一項經歷,那也不知會得到多少榮譽,把自己炒作成什麼樣子,從中獲取多大利益。我五六年前應《北京晚報》之約,寫一些文化人物,到他的辦公室和他交談,再三請他說說他的豐富經歷,但是他談到這些極具傳奇色彩的經歷時,口氣十分平淡,好像只是在品評一頓豐富的晚餐。對於受過的苦難,他從不避諱,而且會以一個哲人的態度和我說,壞事的確可以轉變成好事,比如:
我五十年代後期到人民出版社《時事手冊》任職不久,因為「言論自由」(只因這張嘴!)被打成了右派,經歷了人生的逆境。我挺過了十幾年繁重的體力改造和思想磨練之後,于六十年代初回到編輯部,首先把研究美國歷史確定為編有所長的切入點,在當時中美關係處於一種很敵對的環境中,對美國歷史進行了深入地研究。
唯有在談及這一經歷時,他會露出一些得意的神情。他有理由表現出他的得意,因為他在中國是少數幾個最早研究美國並取得很大成就的專家之一。我們從以下他編輯的主要作品可以窺見他研究美國的功底:
他在人民出版社做編輯幾十年,編輯的高品質書幾十種,如《世界便覽》、《美國史論文集》(六卷本)、《美國史話》、泰晤士版《世界歷史地圖集》和《世界七千年大事總覽》等等。《美國史話》原本是美國讀者文摘出版社的一部分知識性讀物,全書共二十七章。對這種書的出版,一般說來翻譯過來就很好了,但是鄧蜀生卻為讀者著想,把它變為一套叢書,分別取名《美國建國史話》、《美國擴張與發展史話》、《美國社會史話》、《美國科學技術史話》、《美國教育史話》和《美國文學藝術史話》,在當時的圖書市場上大受歡迎,充分顯示一個編輯做選題的水準和能力。從研究大國著手,收益也大。泰晤士版《世界歷史地圖集》是眾多世界地圖集中的精品,其中準確性和權威性是無可爭議的。要把這樣一部大書翻譯並編輯成中文版,且不論其工作量的浩大,僅其無以數計的山名、河名和地名就讓人望而卻步。然而,鄧蜀生主持的中文版最終成為所有十四種不同文字的版本中最精良的一種,受到了原出版者的充分肯定和熱烈讚揚。
老鄧不止一次和我說:
「對有我這樣經歷的人來說,一九七八年是一個思想解放年,忽然之間覺得自己有許多能量要往外放。」這是他的心裡話,他也是這樣做的。他在不長的時間裡信後寫出了《伍德羅‧威爾遜》、《羅斯福》、《美國與移民》以及新近出版的《美國歷史與美國人》等幾部很有分量的好書。作為編輯,他的知識積累的爆發力和釋放量更是驚人。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書,去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100系列叢書」又一次體現了他的大能量。這套叢書共分為五冊,每冊30多萬字,分別為《影響世界的100次戰爭》、《影響世界的100次事件》、《影響世界的100個人物》、《影響世界的100種文化》和《影響世界的100種書》。五百個提名是從成千上萬種書裡歸納和篩選出來的,而這種歸納和篩選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嚴謹大膽的治學態度。
老鄧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一九八八年他辦了退休手續,但是出版社至今仍給他保留著一間辦公室,因為他總在為出版社出新的主意,貢獻餘熱,成就新的事情。我說憑他的資歷和成果,不論以記者身分還是編輯的身分,他都應該榮獲「韜奮獎」的。他聽了馬上說他哪種身分都不夠資格,還是讓更有貢獻的同事們得去吧。這種虛懷若谷淡泊名利的處世觀無疑應屬一位智慧老人了。我認識老鄧近三十年了,老鄧的頭髮白了許多,但是他一直精神高昂,每天還到他在出版社的辦公室去一趟。有時我碰上他,問起他的身體和生活,他還是那麼精神飽滿地說:
「我好,可老伴兒身體不好,我的任務是把她伺候好。」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不願做小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不願做小
本書收集了多年來的文章,一部分關於親人朋友,多與童年和青年記憶有關係;一部分關於職業中和各種人打交道的所思所想和所得。因為來自鄉村,和上層流行的意識形態大不相同或者說南轅北轍,更多是從個人層面的經歷針對集體的掌控出發寫作,反應各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當然也包括我這個闖入者。
因為專業是外文編輯,文化背景受西方文化影響,視野和觀念比較寬,深入專業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是一種專業化的總結。更重要的是對公有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在《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裡反映的是鄉村,而《不願做小》是上層又上層,下層又下層的。
作者簡介:
▎蘇福忠
生於一九五○年,握過鐮刀,舉過鐝頭,掄過鎯頭,鐮刀鎯頭老鐝頭,錘實在二兩重的筆頭,電腦助力到鍵盤敲字,沒有重量因此無需很大的力量,退休了還能有些老驥伏櫪的餘熱,把過去的小文或讀或改,更多的時候是翻檢記憶中的東西,合在一起,竟然有些字數,大感意外,自然希望能和喜歡它們的讀者見面了。
編輯過一些書,如《眾生之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吳爾夫文集》《福斯特文集》《莎士比亞全集》等;翻譯過一些書,如《莎士比亞詩歌全集》《索恩醫生》《巴塞特的最後紀事》《道連•格雷的畫像》《霍華德莊園》《月亮與六便士》《一九八四》《哈克貝利•芬恩》《馬丁•伊登》《了不起的蓋茨比》《夫婦》《漫漫長路》等;寫過幾本書,如《譯事餘墨》《編譯曲直》《席德這個小人兒》《瞄準莎士比亞》《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臺灣版)和《朱莎合璧》等。
章節試閱
〈大編輯〉
編輯往往被戲稱為「大編輯」,而要做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編輯卻絕非易事。有的編輯一輩子能改改錯別字就不錯了;有的編輯能改稿子也能做好選題;有的編輯能編能譯能寫能與作者譯者交流。這後一種就是名副其實的大編輯了。
這些話不是鄧蜀生的原話,但是你若有幸和他坐下來談談編輯這一行,你會深信這就是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理解和說法。幹一行愛一行的人很多,幹一行精一行的人也不少,但是幹一行能說一行並且能說到點子上的人就有限了,因為「說」的前提是說法,是觀點,是獨立,是自由,是思考……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當...
編輯往往被戲稱為「大編輯」,而要做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編輯卻絕非易事。有的編輯一輩子能改改錯別字就不錯了;有的編輯能改稿子也能做好選題;有的編輯能編能譯能寫能與作者譯者交流。這後一種就是名副其實的大編輯了。
這些話不是鄧蜀生的原話,但是你若有幸和他坐下來談談編輯這一行,你會深信這就是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理解和說法。幹一行愛一行的人很多,幹一行精一行的人也不少,但是幹一行能說一行並且能說到點子上的人就有限了,因為「說」的前提是說法,是觀點,是獨立,是自由,是思考……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當...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節錄)
一九八六年,我在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室做編輯六年多,但還不曾編輯過一本書,主要參與《外國文學季刊》的編輯工作。就我而言,因為頭兒沒有交給你什麼任務,你又沒有組稿的權利,主要還是以學為主,每天早上都要大聲朗讀幾頁英語小說,然後默念,腹譯,檢驗理解原文的程度。趕上有譯本的原著,一個星期用一天動筆翻譯幾百到一千字,然後仔細對照譯文,尋找自己中英文存在的差距,連帶找到了別人譯文的死穴。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一九九○年我去英國留學,回來後就堅持不了了。現在也說不清是編輯工作忙了,還是別的什...
一九八六年,我在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室做編輯六年多,但還不曾編輯過一本書,主要參與《外國文學季刊》的編輯工作。就我而言,因為頭兒沒有交給你什麼任務,你又沒有組稿的權利,主要還是以學為主,每天早上都要大聲朗讀幾頁英語小說,然後默念,腹譯,檢驗理解原文的程度。趕上有譯本的原著,一個星期用一天動筆翻譯幾百到一千字,然後仔細對照譯文,尋找自己中英文存在的差距,連帶找到了別人譯文的死穴。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一九九○年我去英國留學,回來後就堅持不了了。現在也說不清是編輯工作忙了,還是別的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卷 觸底反彈
星星並不遙遠
祭母
發高燒的時候
我和我的父親
兩鍋飯
苦杏樹
人鼠之戰
吃的故事
老薗的魅力
我的第一本字典
我的貴人
馬老師
▎第二卷 識字識人
寫在老黃去世一周年
綠原先生點滴
大編輯
寧折不彎
少成即天性
詩人綠原譯詩
我認識蕭乾
韋老太,你慢走
嚴文井的童話
趙樹理印象
《洗澡》的深水區
別有肺腸
文人的輕佻與暴跳
腦殘是幾級傷殘
之不拉與海乙那
翻譯這回事
把 leek 譯作 leek
▎第三卷 說東道西
古瑞夫婦
吉普尼和鞋市
托爾斯泰的文藝觀
喬治‧奧威爾的馬列觀...
星星並不遙遠
祭母
發高燒的時候
我和我的父親
兩鍋飯
苦杏樹
人鼠之戰
吃的故事
老薗的魅力
我的第一本字典
我的貴人
馬老師
▎第二卷 識字識人
寫在老黃去世一周年
綠原先生點滴
大編輯
寧折不彎
少成即天性
詩人綠原譯詩
我認識蕭乾
韋老太,你慢走
嚴文井的童話
趙樹理印象
《洗澡》的深水區
別有肺腸
文人的輕佻與暴跳
腦殘是幾級傷殘
之不拉與海乙那
翻譯這回事
把 leek 譯作 leek
▎第三卷 說東道西
古瑞夫婦
吉普尼和鞋市
托爾斯泰的文藝觀
喬治‧奧威爾的馬列觀...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