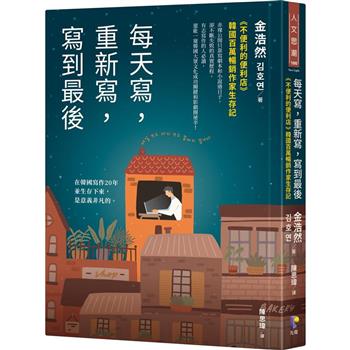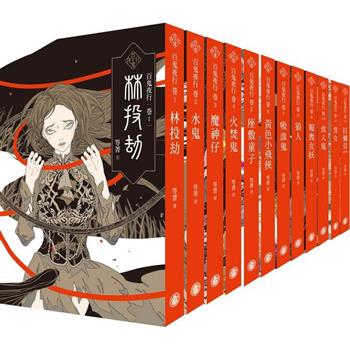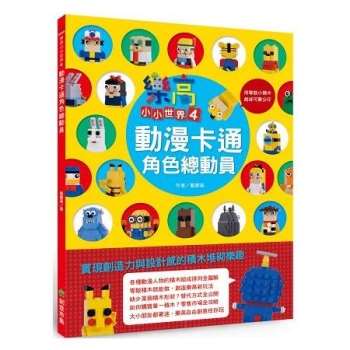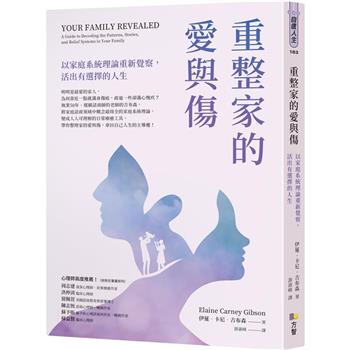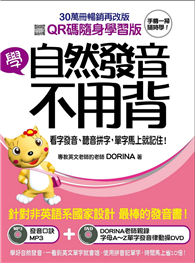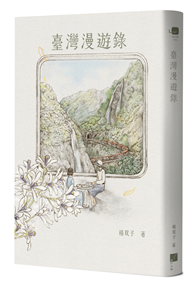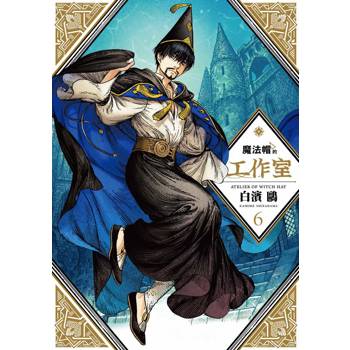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我看見歲月飛逝︰方明詩作・洛夫書法的圖書 |
 |
我看見歲月飛逝: 方明詩作.洛夫書法 作者:方明;洛夫/書法 出版社:長歌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2-2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74 |
詩 |
$ 774 |
文學作品 |
$ 862 |
中文書 |
$ 882 |
華文現代詩 |
$ 882 |
書法欣賞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以現代書寫古典
★以毛筆詮釋詩意
★以詩作見證友情
《我看見歲月飛逝—方明詩作・洛夫書法》
一場橫跨時空、年齡與輩分的詩書藝術對話。
——謹此獻給洛夫夫人 洛夫文學紀念館以及泫念洛夫泱泱風範
2024.9.14 方明
《我看見歲月飛逝—方明詩作・洛夫書法》是方明第七本詩集,全書收錄詩作四十六首。
洛夫以毛筆書寫方明詩作,筆墨之間流露對詩書藝術的追求與理解:「作為一個詩人兼書法家,我追求的是一個二元合一的整體世界,我企圖以書法藝術來表達我的詩情詩意,以詩情詩意來提升我的書法境界,以期達致二者完美的結合。」
方明與洛夫是跨越年齡與輩分的忘年之友。當年方明就讀台大時,與廖咸浩、楊澤、苦苓、詹宏志、天洛與共同創辦「台大現代詩社」,並向洛夫請益詩學,二人因而結緣。方明的獲獎詩作〈青樓〉、〈髮〉深受洛夫讚賞,亦成為洛夫抄錄方明詩作的開端。其後,洛夫耗時一年,抄錄方明詩作四十餘首。
2018年洛夫仙逝,方明以詩句弔念:「眾相乃游離流逐的漂木 /偶然彼此從心脈交會的一場盛宴
/隱題詩矜持在青春季節裡裸告 /生生世世共鳴著湛湛承諾 /因為風的緣故 」
作者簡介:
洛夫(1982-2018)
原名莫運端,筆名洛夫。身兼詩人、評論家、散文家 與書法家。
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湖南衡陽,一九四九年隨軍到台灣, 一九七三年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曾任教於東吳大學,一九九七年移民加拿大。
他於一九五四年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長期擔任總編輯,對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影響深遠,作品被譯為多國語言,廣受國際詩壇推崇。
洛夫詩作以超現實主義風格著稱,作品中融入魔幻手法,被譽為「詩魔」。名作《石室之死亡》與《漂木》等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漂木》更以三千行長詩震撼華語詩壇。詩集《魔歌》被評為台灣文學經典之一,評論集、散文集與譯作逾數十部。
他曾多次獲得國內外文學獎,包括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及中國文藝協會終生成就榮譽獎章。
晚年醉心書法,擅魏碑漢隸與行草,書風靈動蕭散。 洛夫於二〇一八年出版最後詩集《昨日之蛇》後辭世, 享壽 91 歲。
方明
廣東番禺人,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巴黎大學經貿研究所,文學碩士。
《兩岸詩》詩刊創辦人 、「台灣大學現代詩社」創辦人之一,並曾任社長 、「世界華文文學交流協會」詩學顧問 、「藍星詩社」同仁 、成立「方明詩屋」提供學者詩人吟唱遣興(二〇〇三年)。
獲獎
兩屆台灣大學散文獎,新詩獎
中國文藝協會五四文藝獎章新詩獎(二〇〇五年)
香港大學中文系宏揚中華文化「東學西漸」獎(二〇〇五年)
台灣大學外文系「互動文化」獎(二〇〇五年)
香港大學首展臺灣個人詩作,為期一個月(二〇〇八年)
國新詩百年百位最有影響力詩人(二〇一七年)
兩屆台灣大學散文獎,新詩獎
全球華文詩歌著作首獎(二〇二三年)
著作
詩集《病瘦的月》(一九七六)
散文詩集《瀟洒江湖》(一九七九)
詩集《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二〇〇四年)
集《歲月無信》韓譯本(金尚浩教授翻譯二〇〇九)
論文集《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兼談越華戰爭詩作》(二〇一四年)
詩集《然後》(二〇二二)
詩集《我看見歲月飛逝》(二〇二五)
——《我看見歲月飛逝》詩與書法合集
中國大陸稱作家轉行經商為下海,稱有文化商人為儒商。儒商這個身份頗適用於方明,但一面經商,一面仍不懈於詩歌創作且成績可觀如方明者,即便兩岸也不多見。
方明原為越南僑生,少年的歲月是在殘酷的戰爭陰影下渡過,青年留學台灣、巴黎,嗣後即投身商海,在數十年的衝折拼搏中,事業顯然有成。戰爭與商場這兩種特殊的經歷,交織成了他作品中不是一般人所能培育的詩歌品質,這種品質其實也可說是越南華語詩歌的傳統,正如方明自己所說:「西貢、台北、巴黎將我成長的心路歷程切割...
洛夫序文二 12
方明序文 16
方明詩觀 18
一 瀟灑江湖 22
西湖情繞 30
花間集 32
書生 38
破陣子 42
清明 46
然後 51
深宮 56
習字 58
黃河62
毀約之後 64
詩人 68
馳古三卷 72
青樓 80
邀酒 84
離騷篇 88
中秋 92
月悲中秋96
二 典藏年代 102
交會 104
有一種心情 106
始末110
肉體時空 112
長路將盡 116
宴終 120
家122
訣 128
情 132
愛的演出 136
情人的臂 138
情簾 140
簾 146
預約仳離 150
髮 152
三 寂寞局勢 158
我看見歲月飛逝 160
巴黎午後 164
日落塞納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