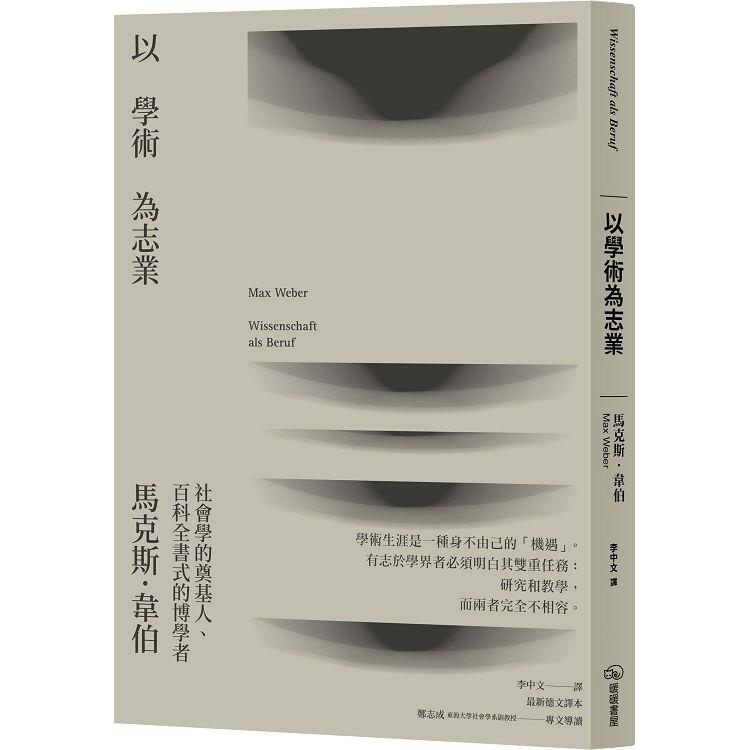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奠基人、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
談投身學界的條件與特質
學術生涯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機遇」。
有志於學界者必須明白其雙重任務:研究和教學,而兩者完全不相容。
本書是韋伯於1917年11月7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第一場演講,第二場演講為《以政治為志業》。兩場演講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之一。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
講座對象主要是學生,即將面臨職業生涯的選擇,有些人可能會選擇走上學術之路。韋伯首先指出這個職業的外部條件,他比較了德國與美國在學術體系上的差異,分析體制對於學者選拔過程的影響,很大程度是由機遇而非才能所決定。不僅如此,他還告誡有志於此的年輕學子,必須明白等待他的是雙重任務:他不僅要有學者的研究能力,更要具備教師的教學能力,而這兩種素質通常是完全不相容的。
他再談到學者的內在條件,必須心無旁騖的沉潛在工作上,並堅守嚴格的專業。但就算抱持再多的學術熱情,在研究成果上仍是無法強求的,且學術追求不斷的進步,更是永無止境的命運,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嚴苛事實。此文發表雖已百年,依舊是精闢透徹的經典之作。
何謂「以學術為志業」:
個人唯有在最嚴格專業化的情況下,才能夠得到某種定見,也就是在學術領域貢獻出某種確實相當完美的東西。……誰要是沒有能力做到所謂的心無旁騖,並且沉潛到某個想法,也就是自己心靈的際遇就取決於:他能否對這部抄本的這個段落做出某種正確的推測的話,那就只好離學術遠一點了。
唯有單純為事業獻身的人,才具備學術領域的「人格」。……任何學術上的「完滿」都意味著新的「探究」,並且想要被「超越」和變得過時。所以任何想要效力於學術的人,都必須遷就這一點。
本書特色
◎全新德文譯本
◎投身學界的條件與特質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文導讀,疏理韋伯演講的背景脈絡。
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國知名的社會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與馬克思和涂爾幹公認是社會學理論的三大奠基人。
年輕時就展現出對哲學、歷史、法律、政治、經濟、神學等各方面的廣泛興趣。一八八九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律博士,一八九一年開始在柏林大學法律系任教。一八九三年與妻子瑪麗安娜結婚,一八九四年受聘於弗萊堡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一八九六年轉至海德堡大學任教。一八九八年曾因精神狀況無法正常工作,後來雖曾短暫恢復教學,但最後仍在一九○三年辭職,與宋巴特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期刊,開始撰寫他後來最知名的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九年開始寫作《經濟與社會》。一九一五年發表《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前三個部份,隔年發表第四部份。一九一九年參與威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一九二○年出版《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一卷,即修訂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年六月因肺炎在慕尼黑辭世。
他身後留下的大量作品,都是由遺孀瑪麗安娜編輯整理後出版,包括:《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二、三卷、《政治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科學學說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等。一九八四年開始,《韋伯全集》陸續出版。
譯者簡介:
李中文
輔仁大學德文碩士。擔任過出版社主編、大學德語講師.目前為專職譯者。譯作包括:《兒童背脊健康法》、《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運動讓你不生病》、《無效的醫療》、《細菌之謎》、《閱讀的歷史》、《美國說了算》、《何謂哲學問題》、《論時間》、《數位癡呆症》、《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二、三十本書。E-mail: roger6869@gmail.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文導讀
韋伯的各方評價:
˙雅斯培(Karl Jaspers):馬克斯.韋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韋伯的才能是百科全書式的,這在現代極其罕見。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馬克斯.韋伯是歷來登上學術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響的一個。
˙史壯柏格(Roland N. Stromberg):社會學最大的黃金時代無疑是馬克斯.韋伯,一個具有極大眼界與創力的學者。
˙亨尼斯(Wilhelm Hennis):涉入韋伯的著作,乃是一項冒險。
˙拉德考(Joachim Radkau):無論偉大與否,韋伯在社會科學上無疑是一位具備了獨特觀點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通常能磨礪我們思考的思想家。
˙柯塞(Lewis A. Coser):韋伯是最後一批博學者中的一個。
˙克斯勒(Dirk Kaesler):馬克斯.韋伯是近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世界公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名人推薦: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文導讀
韋伯的各方評價:
˙雅斯培(Karl Jaspers):馬克斯.韋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韋伯的才能是百科全書式的,這在現代極其罕見。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馬克斯.韋伯是歷來登上學術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響的一個。
˙史壯柏格(Roland N. Stromberg):社會學最大的黃金時代無疑是馬克斯.韋伯,一個具有極大眼界與創力的學者。
˙亨尼斯(Wilhelm Hennis):涉入韋伯的著作,乃是一項冒險。
˙拉德考(Joachim Radkau)...
章節試閱
以學術為志業
按照各位的要求,我要來談談「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我們國民經濟學者總帶有幾分學究氣,所以我想依循此點來談:我們一向拿外部的情況作為出發點,因此這裡的問題是:就職業這個詞的物質意義而言,學術的情況是如何呢?不過,這在今天實際上主要意味著:一名決心投入學術生涯、以學術做為職業的畢業生,其處境是怎樣的呢?為了瞭解我們德國的情況所具有的特殊性,這裡最好以比較的方式來處理,並揣摩國外在這方面的情況,美國在這方面跟我國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德國大學的私聘講師和美國大學的助教
大家都知道,在我國,一名以學術為職志的年輕人,生涯通常是從擔任「私聘講師」(Privatdozent)開始的。他在跟相關的院所代表面談並取得認可之後,以一本書以及一次通常偏向形式上的科系考試為根據來獲得講師資格,可以在一所大學裡頭開課,主題則是從他自己的講授許可(venia legend)範圍內來決定。但校方並不支付薪水,酬勞獨獨仰賴學生的聽課費。至於在美國,學術生涯通常有完全不同的開端,也就是被聘任為「助教」(assistant)。這就類似於我國在自然科學和醫學科系的大型機構向來所出現的情況,只有一小部分助教才能獲得私聘講師正式的任教資格(Habilitation),而且通常要很晚才能夠得到。這種對比實際上意味著:在我國,一個學術人的生涯完全建立在金權政治的前提之上。因為對於一名完全沒有財產的年輕學者而言,完全仰賴學術生涯的這些條件是格外冒險的。他必須能夠忍受至少好幾年,完全不知道自己往後是否有機會謀得一個足以糊口的職位。至於在美國,則有官僚制度。因為年輕人從一開始就是受雇的。薪水當然並不多,這份薪資通常達不到一名不完全熟練工人的薪資額度。雖然他是從這麼一個貌似穩定的職位開始,因為他是固定受雇的;然而通常的情況卻是,就如同我國的助教,當他不符合期待時,就有可能遭到解聘,對於這一點,他要有種種勇敢的心理準備。不過,所謂期待,甚至還包括他得做到「座無虛席」。這種情況並不會發生在德國一名私聘講師身上。人家一旦用他,就不會再趕他走,儘管他不能有所「要求」。不過,他還是有一個合乎情理的預期:在他工作數年之後,便擁有某種別人會考慮到他的道德權利,就連在核可其他私聘講師的講課資格的問題上(這通常是重要的)也是如此。至於是否原則上要讓每一位證明優秀的學者獲得授課資格,或者是否考慮到「教學需求」,也就是給既有的講師一種教學專利,這種問題是令人尷尬的困境,它牽涉到待會兒即將提到的學術職業的雙重面貌。通常校方會採取第二個選項。不過,這意味著某種危險性的升高,也就是相關的科系教授即使在主觀上非常的認真,依然會偏好自己的學生。就拿我個人來說——這麼說吧,我所遵循的原則是:在我這裡拿到學位的學者必須在不同的人以及別的地方那裡取得證明和獲得任教資格。然而結果卻是:我最優秀的一位學生卻在別的地方遭到否決,因為沒有人認為這算是個理由。
以學術為志業
按照各位的要求,我要來談談「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我們國民經濟學者總帶有幾分學究氣,所以我想依循此點來談:我們一向拿外部的情況作為出發點,因此這裡的問題是:就職業這個詞的物質意義而言,學術的情況是如何呢?不過,這在今天實際上主要意味著:一名決心投入學術生涯、以學術做為職業的畢業生,其處境是怎樣的呢?為了瞭解我們德國的情況所具有的特殊性,這裡最好以比較的方式來處理,並揣摩國外在這方面的情況,美國在這方面跟我國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德國大學的私聘講師和美國大學的...
推薦序
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誌韋伯《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百週年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緣起:向韋伯致敬
去年二○一七,韋伯演說《以學術為志業》一百周年;明年二○一九,韋伯闡述《以政治為志業》一百周年;今年二○一八,暖暖書屋出版這兩篇演講的中文新譯版本,正逢其時。對於一位學者的尊重致意,毋須歌功頌德,不必立碑膜拜,只要印其書,讀其書,論其書,不論著述還是譯作,足矣!我認為,這是對學者的最高禮敬吧!
相較於韋伯絕大部分論述著作的質地綿密,論證繁複,這兩篇演講說得平易近人,膾炙人口。平易近人許是因為以演說形式,而非書寫表述;膾炙人口則反映了演說內容切中時勢,直扣人心。最重要的是,百年以來,這兩篇演講並未過時,仍具時效。除了對於學術與政治兩大工作領域本質特徵的考察細究之外,特別是演說內容的規範性訴求,也就是學者當為與從政者當為的審度,以此檢視現下台灣學界、政界處境,當有清時弊、正風氣的警醒。
既然,韋伯的兩篇志業演講──以學術為志業、以政治為志業──讀來平易近人,那麼這一篇導讀的用意便不鑽入文本側重演講內容的梳理註解,而是企圖扣緊著這兩篇演說之講者對於講題的感知狀態與所處歷史情境,扼要鋪陳其生成緣起與背景脈絡。因為,演講人對於講題的感知狀態與歷史處境形塑了演講內容的框架與外部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捨了內容的開展。因而,這一篇導讀的任務便是試圖勾勒韋伯這兩篇演講的個人處境與歷史場景,盼能有助於讀者對於這兩篇志業演講的理解與掌握。
二、兩篇志業演講的共同背景
1. 演講魅力
在介紹韋伯兩篇演講的機緣發生之前,可以就有限的線索提供讀者關於韋伯的演說魅力。根據韋伯夫人瑪麗安娜在她那本刻意形塑其丈夫偉大形象的傳記中,瑪麗安娜援引了當時維也納報紙文化版對韋伯上課講演的報導,細緻地描述了韋伯的演講魅力:
這位身材高挑、留著鬍鬚的學者,看起來像是來自文藝復興時期的德國石匠。只是他的眼睛沒有匠人的直視和肉慾的喜悅。他的目光深邃,似乎沿著一個隱藏的通道,然後消逝在遠方。他典型的表情是外表凝固不動,似乎是一副具有無窮意味的圖畫。這裡所顯現的是某種近乎希臘人認識事物的方式。他的言辭洗練,讓人聯想起巨石。然而一旦我們集中到他這個人,他立刻就變成了紀念碑式的人物。他的每一個表情都彷彿是雕刻在大理石上,輪廓清晰。他講話的時候偶爾伴以輕柔的手勢。他纖細的手指和稍微有點任性的拇指做出的手勢恰到好處,幅度很小,他的手更像是Petroniusnatur[公元一世紀時羅馬諷刺作家]的而不像學者的。自Unger、Lorenz von Stein及Jhering以來,在維也納大學法學院,還沒有哪個教授像韋伯這樣能吸引如此眾多的學生。然而這種異乎尋常的吸引力,絕不是因為這個人能說會道,也不在於他的論證的原創性和嚴格的客觀性,而主要在於他所具有的激發潛藏在他人心靈中的感情的能力。他的每一個詞都明白地顯示出,他自認為是德國歷史的傳人,並被對後代的責任感所主宰。
類似的聽講印象,還可以在Karl Löwith的回憶錄中讀到,將於下文敘述《以學術為志業》時摘錄。當然,具備卡里斯瑪的演說魅力,並不保證演講內容的品質。但韋伯對於自己的演講能力當是有自信的。一九一八年夏天,韋伯應聘維也納大學任教。在一封給妹妹的書信中,韋伯曾感嘆自己不是上課教學的料,但卻也透露出他自己對於演講的自信:「我非常清楚,我的課最多就是中等。儘管如此,也許因為有備課,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不!我生來就是為了動筆寫作、為了演講講壇,而不是為了課堂講台。於我而言,這種經驗有些痛苦,但卻十分清楚。」
2. 演講文體
關於韋伯這兩篇分別以「學術」志業及「政治」志業為題的演講,早在一九九二年由Wolfgang J. Mommsen與Wolfgang Schluchter共同編纂以《韋伯全集》第Ⅰ部第十七卷(MWG I/17)出版。這個以全集面世的版本,主要文本係依據一九一九年由慕尼黑及萊比錫的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出版的《以學術為志業》(三十七頁)以及《以政治為志業》(六十七頁)兩本小冊子為主,並輔以當時報紙《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於演講隔兩日對韋伯「以學術為志業」演講的報導,以及韋伯「以政治為志業」兩份關鍵字詞手稿編纂而成。這兩本與演講同名的小冊子的內容都經過韋伯大幅增補修訂,因而並非當日演講的逐字稿。也就是說,出版面世的文本雖以演說形式為骨幹,但後續的內容補綴以及文字修辭係以書寫方式為之,不能等同視為「演講稿」。但我仍以為文各有體,得體為佳。這兩篇「志業」文本的「得體」仍屬演講形式,迥然有別於韋伯的其他書寫論文。
《韋伯全集》的編纂策略不若甫於二○一六年全部卷冊皆已出齊面世的《齊美爾全集》(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 GSG, 1989-2016)之編纂形式。《齊美爾全集》的編纂係儘可能蒐集齊美爾所發表之文章、遺稿、筆記、書信等文類如實重刊。並於卷後「編輯報告」、「付印的文稿」(Druckvorlage)及「版本差異」中簡要說明該文本緣起出處,標記版本內容差異處,並不提供內容評註及援引考據。因此《齊美爾全集》可以在「短短」三十年左右即全數二十四卷編纂完成出版。《韋伯全集》則採取「歷史性─批判性」的編纂綱領,也就是除了文本的掌握之外,還需考據文本生成、版本比較並儘可能並陳差異,以及文本內容的註解、考據。因而《韋伯全集》的編纂曠日經年,今年(2018)可望將全集第Ⅰ部分「論文與演講」總計二十五卷全部編纂完畢出版(1984-2018)。這一部分的編纂工作歷時近半個世紀。至於第Ⅱ部「書信」及第Ⅲ部「上課筆記」的編纂完工仍在未定之日。
也因為《韋伯全集》的編纂以「歷史性─批判性」的方式進行,所以被列為全集第Ⅰ部第十七卷《以學術為志業;1917/1919.以政治為志業;1919》的這兩篇「志業」演講之起始緣由與來龍去脈,以近百頁的篇幅(「導論」及兩篇志業演講的「編輯報告」;MWG I/17: 1-46, 49-69, 113-137)堪稱詳盡地獲得相當程度的考察並釐清。在此無法也不需鉅細靡遺照錄重述,僅以全集該卷的導論及編輯報告的文件與文獻為主要依據,扼要整理,重點介紹如下。
3. 演講推手:自由學生聯盟(Freistudentischer Bund)
韋伯的這兩篇「志業」演講的緣起要追溯到「自由學生聯盟巴伐利亞分會」於一九一七年起所構思策劃的「以精神工作為志業」(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講。自由學生聯盟係十九世紀末針對德國高等教育的劇烈變動之反應而形成。其政治立場大致可以歸為傾左的自由派學生團體。自由學生聯盟主要的抗議訴求是針對當時德國高等教育由規模較小的機構,隨著大學生人數的持續擴增,變成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大企業組織。因而「有識」之大學生在各地大學各式各樣的傳統學生社團之外,成立了所謂的「自由的」學生團體。這些各地各校的「自由學生們」於一九○○年聯合成立了共同社團,即名為「德國自由學生會」(Deutsche Freie Studentenschaft)聯盟,並提出代表所有未參與學生社團的學生們之訴求。其目標為打破傳統學生社團的優勢,聯合全體大學生成為一個團結並自主的社團。
此外,自由學生會運動主要致力於改善許多學生惡劣的社會處境,以及超越學校學習,拓展學生的精神視野。因此,自由學生會在各大學組織了學術部門,舉辦演講,以超越大學「職業培訓」的狹隘框架。亦有自由學生會舉辦連結學者與勞工的相關課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爆發了關於自由學生會理論基礎的爭辯。一九○七年Felix Behrend提出關於自由學生運動的內容與目標之高等教育政策計畫。Behrend主張回歸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理念,亦即學術的獨立性、教學與研究的統一性,以及知識促成人格培養。Behrend反對大學日益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秩序需求,並警告一種純粹的「營生學習」(Brotstudium)只會走向「市儈習氣」(Philistertum)。Behrend更批判專業化的蔓延現象迫使個人只滿足於知識的枝微末節。自由學生會的目光必須投向知識的一般原則問題,以及求索文化的基底。
在此特別提醒,上述場景與眼下台灣的高教處境多麼近似,但這是一個世紀前德國大學生的社會批判與自我省思。
自由學生會如是的高等教育政策理念主張與高教決策及行政管理階層自然格格不入,關係對立緊張,並促使自由學生會走向政治行動的抗爭方式。他們控訴,大學並不以完善的、自主的世界觀教育學生,反而在飼養專家,並且抗議將大學成為職業培訓所。其中一部分自由學生會領袖亦受到由教育改革家Gustav Wyneken所倡議的德國青年運動的教育理念影響。
約莫是在這樣抗議當時德國高教專業化、職業化取向日趨嚴峻,自由學生聯盟係十九世紀末針對德國高等教育的劇烈變動之反應而組織成立。「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系列演講亦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反思生成。(未完)
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誌韋伯《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百週年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緣起:向韋伯致敬
去年二○一七,韋伯演說《以學術為志業》一百周年;明年二○一九,韋伯闡述《以政治為志業》一百周年;今年二○一八,暖暖書屋出版這兩篇演講的中文新譯版本,正逢其時。對於一位學者的尊重致意,毋須歌功頌德,不必立碑膜拜,只要印其書,讀其書,論其書,不論著述還是譯作,足矣!我認為,這是對學者的最高禮敬吧!
相較於韋伯絕大部分論述著作的質地綿密,論證繁複,這兩篇演講...
目錄
鄭志成導讀: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一、德國大學的編外講師和美國大學的助教
二、學者選拔過程是由機遇而非才能本身所決定
三、靈感之於學者的重要性
四、學術所求的進步有別於藝術作品永不過時的完滿
五、學術在過去曾被視為追求真理的手段
六、學術作為志業的意義何在?
七、課堂不是先知和鼓動家的場所
八、教師在課堂上只是教師,不必是位領袖
九、教師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促成思緒清晰和責任感
十、現代人只能生活在疏遠神且沒有先知的時代
譯名對照表
鄭志成導讀:激情與理智同步、信念與責任共舞
一、德國大學的編外講師和美國大學的助教
二、學者選拔過程是由機遇而非才能本身所決定
三、靈感之於學者的重要性
四、學術所求的進步有別於藝術作品永不過時的完滿
五、學術在過去曾被視為追求真理的手段
六、學術作為志業的意義何在?
七、課堂不是先知和鼓動家的場所
八、教師在課堂上只是教師,不必是位領袖
九、教師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促成思緒清晰和責任感
十、現代人只能生活在疏遠神且沒有先知的時代
譯名對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