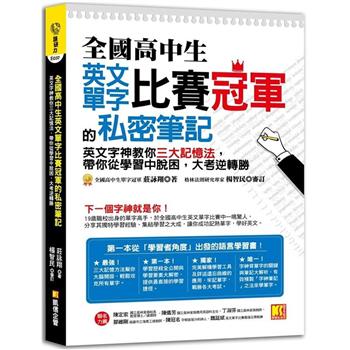小說家 沈默 鄭順聰 掛名推薦
本書獲得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
台灣,不止是蒙古和平的絲路、歐亞海權的大航海,台灣也曾經有過「一個逝去但兼容並蓄的時代」。平埔族吟咏歌謠、高山族傳誦祖靈,台灣俯瞰遠眺盡是梅花鹿群以及森林沼澤。漳泉、客人突破洶湧的烏水溝,遠離故土來到滅人山,為自我的宗族和信仰,在這大肚溪南北岸上披荊斬棘、不惜染上鮮血-
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新設「彰化縣」後,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蒙「朱一貴走反」的軍功,在大肚溪北岸(今台中市)一帶取得墾照【藍張興】,企圖將一片沼澤荒林,闢建成千里良田,管事職責全權予藍家女婿顏克軍。
【藍張興】頭家顏克軍以「藍張興庄」做經營據點,開始招募大量漳州移民,與大肚溪南岸的【高福盛】高家泉州集團隔江對峙,還不時面對西側貓霧捒社為爭奪獵場襲擊,北面亦有客籍集團虎視眈眈。
顏克軍手下一批「興營」,專司護衛、押鏢情事,其中一名「興營」子弟徐隆總認為自己僅需恪守本份,便能與同門師兄弟黎洪、何勇等建功立業,並與青梅竹馬黎貞常相廝守,長久安身立命一生。
雍正三年(1725年),因大肚溪南北岸漢人爭相墾伐內山林木引發的「骨宗事件」,導致彰化縣平地騷動不安,因此徐隆不曾想過包括他在內的無數人生,所謂生死吉凶、禍福榮辱,眨眼間都可以兌換成大人們談判的籌碼。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藍張興:大肚溪南北岸的拓荒者們(第一部 雍正三年)的圖書 |
 |
藍張興:大肚溪南北岸的拓荒者們(第一部 雍正三年) 作者:舟集 出版社: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72頁 / 15 x 21 x 1.8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華文歷史小說 |
$ 345 |
中文書 |
$ 363 |
台灣研究 |
$ 363 |
歷史 |
$ 414 |
現代小說 |
$ 41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藍張興:大肚溪南北岸的拓荒者們(第一部 雍正三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舟集
本名鄭承榆,1989年生,澎湖媽宮人,母系來自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舟集工作室」負責人,主要承接澎湖景點走讀、文史講座策辦、社區調查等委託案。中文維基百科編輯志工,使用者代號 user:Boattoad。
舟集
本名鄭承榆,1989年生,澎湖媽宮人,母系來自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舟集工作室」負責人,主要承接澎湖景點走讀、文史講座策辦、社區調查等委託案。中文維基百科編輯志工,使用者代號 user:Boattoad。
目錄
序言
(一)彰化置縣
(二)高家家宴
(三)短刀會
(四)顏家大舍
(五)謝容案
(六)報喪
(七)沖喜
(八)烏日巨漢
(九)春雷驚鳴貓霧捒
(十)薛家盛宴
(十一)風波迭起
(十二)誇力爭強不相下
(十三)朱弓下
(十四)大肚社湮滅
(十五)聖母鴻仁德可參天
(十六)年年歲歲花相似
(十七)歲歲年年人不同
(十八)媒妁之言嫁地主
(十九)軍功寮
(二十)北投鎮番寨
(二一)內山老婦
(二二)快官庄道狹路逢
(二三)萁在釜下燃
(二四)非是力不如
(二五)來如雷霆收震怒
(二六)夢迴幾度疑吹角
(二七)南岸豪門
(二八)蔴穎
(二九)卿未有期
(三十)墨衫客戶
(三一)嘴舌無骨茲事多
(三二)三方聚首
(三三)大肚溪誓盟
(三四)九月風颱無人知
番外篇:戊戌年大洪
【附錄】康熙、雍正年間.台灣中部大事記
(一)彰化置縣
(二)高家家宴
(三)短刀會
(四)顏家大舍
(五)謝容案
(六)報喪
(七)沖喜
(八)烏日巨漢
(九)春雷驚鳴貓霧捒
(十)薛家盛宴
(十一)風波迭起
(十二)誇力爭強不相下
(十三)朱弓下
(十四)大肚社湮滅
(十五)聖母鴻仁德可參天
(十六)年年歲歲花相似
(十七)歲歲年年人不同
(十八)媒妁之言嫁地主
(十九)軍功寮
(二十)北投鎮番寨
(二一)內山老婦
(二二)快官庄道狹路逢
(二三)萁在釜下燃
(二四)非是力不如
(二五)來如雷霆收震怒
(二六)夢迴幾度疑吹角
(二七)南岸豪門
(二八)蔴穎
(二九)卿未有期
(三十)墨衫客戶
(三一)嘴舌無骨茲事多
(三二)三方聚首
(三三)大肚溪誓盟
(三四)九月風颱無人知
番外篇:戊戌年大洪
【附錄】康熙、雍正年間.台灣中部大事記
序
序言
台灣清領時期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歲在辛丑,台灣爆發以杜君英、朱一貴為首的叛亂事件,造成台灣府陷落,文武官員陸續走避澎湖、福建避難,朝廷因此調派大軍,任命台灣鎮總兵藍廷珍(原籍漳州漳浦)署福建水師提督領軍,迅速來台掃蕩叛軍;這段朱一貴走反的事蹟,後人傳有「鴨母王」之名傳誦,那不是我們今日要敘述的故事。
之後,清廷在追捕朱一貴、杜君英餘黨的過程中,有感諸羅縣幅員過廣、管理不易,決議將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部份自諸羅縣劃分出來,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間新置一縣,面對當時縣境內「番社龐雜」的狀況,新的縣被命名「彰化縣」,縣治設於半線庄。
同一時期,若我們將目光調離台灣南部的戰場,朱一貴之亂掃平後,藍廷珍留駐台灣各處巡視,就在大肚溪以北、今日台中盆地的地方(原作張鎮庄,康熙五十八年已廢庄遺民),物色上那一大片佈滿沼澤、雜草的荒地,興起加以整治拓荒的念頭。
藍廷珍特意將從湄洲天后宮請來的媽祖金身,原本供奉在台南大天后宮,又迎奉至大墩「藍興宮」(今「萬春宮」),並就此長奉媽祖迄今,而我們這部叫《藍張興》的歷史武俠小說,就是自雍正年後的這一時期(一七二○年代)、環繞大肚溪南北岸兩端,開啟故事的篇章。
為保全故事文本在真實史實下的創作空間,本故事中登場的歷史人物,一個都不會登場,僅供人物對談時不時言及,登場人物係基於歷史時空創作而出,悉數杜撰,還望周知。此外,由於人物多採台語對白,但凡有稱「番」或「番仔」字眼,為保還原時人說話狀況將予以保留,在對話框之外的敘述句則會悉數避免,望各路賢達尚祈鑒諒。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歲在甲辰,首任彰化知縣談經正上任,在廷珍所物色原屬張鎮庄的範疇,新立「藍張興庄」,談經正在同一年度核發藍廷珍單准墾執照,委由笠事蔡克俊統理,其墾照名稱即為【藍張興】。
本作《藍張興》初版付梓於二○二四年,亦歲在甲辰,幸逢【藍張興】墾照核發屆滿三百周年,豈非巧合?幸甚、幸甚,引以為序。
導讀
台灣清領時期康熙六十年(1721年),歲在辛丑,台灣爆發以杜君英、朱一貴為首的叛亂事件,造成台灣府陷落,文武官員陸續走避澎湖、福建避難,朝廷因此調派大軍,任命台灣鎮總兵藍廷珍(原籍漳州漳浦)署福建水師提督領軍,迅速來台掃蕩叛軍;這段朱一貴走反的事蹟,後人傳有「鴨母王」之名傳誦,那不是我們今日要敘述的故事。
之後,清廷在追捕朱一貴、杜君英餘黨的過程中,有感諸羅縣幅員過廣、管理不易,決議將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部份自諸羅縣劃分出來,在雍正元年(1723年)間新置一縣,面對當時縣境內「番社龐雜」的狀況,新的縣被命名「彰化縣」,縣治設於半線庄。
同一時期,若我們將目光調離台灣南部的戰場,朱一貴之亂掃平後,藍廷珍留駐台灣各處巡視,就在大肚溪以北、今日台中盆地的地方(原作張鎮庄,康熙五十八年已廢庄遣民),物色上那一大片佈滿沼澤、雜草的荒地,興起加以整治拓荒的念頭。
\藍廷珍特意將從湄洲天后宮請來的媽祖金身,原本供奉在台南大天后宮,遷奉至台中市大墩地區的「藍興宮」,並就此長奉媽祖迄今,而我們這部命名做《藍張興》的台灣歷史武俠小說,就是自雍正年後(1720年代)的這一時期,環繞大肚溪南北岸兩端拓荒者們,開展故事的篇章。
為保全故事文本在真實史實下的創作空間,本故事中登場的歷史人物,一個都不會登場,僅供人物對談時不時言及,登場人物係基於歷史時空前提下,憑空創作而出,悉數杜撰,還望周知。此外,由於人物多採台語對白,但凡有稱「番」或「番仔」字眼,為保還原時人說話狀況將予以保留,在對話框之外的敘述句則會悉數避免,望各路賢達尚祈鑒諒。
雍正二年(1724年),歲在甲辰,彰化知縣談經正上任,在藍廷珍物色原屬張鎮庄的範疇,新立「藍張興庄」,談經正核發藍廷珍印單准墾執照,委由管事蔡克俊桶理,其墾照名稱即為【藍張興】。
本作初版付梓於2024年,亦歲在甲辰,幸逢【藍張興】墾照獲得核發逢300周年,豈非天意?幸甚、幸甚,引以為序。
自序
自從2016年下願投入長篇小說創作事業以來,2024年是第八個年頭,如今總算能夠以我能力企及最好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一切深懷感恩。
我出生於1989年6月,搭上龍年尾巴同屆的「福份」,正好是國民教育「部編本」的末班車。我猶記得我學生時代,手上看得漫畫是橫山光輝的《三國志》、《水滸傳》,打得電腦遊戲是〈三國無雙〉、〈軒轅劍〉及〈仙劍奇俠傳〉。
當時最流行的電視劇是一波一波金庸武俠小說的改編浪潮,從《笑傲江湖》、《神鵰俠侶》、《鹿鼎記》等等的戲劇,我看過好幾遍;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如此冀望,我也想成為像金庸那樣的小說家,讓自己發想的故事情節改編成影視劇,風靡傳誦這顆星球,其實此刻,我這個心願依然沒有動搖,但我已經不想成為金庸了。
記得2010年初有一度中國「穿越劇」非常流行,華文小說網也興起書寫穿越文的浪潮。「穿越回去?怎麼可能,光開口說話就露餡,還要跟歷史人物談戀愛?」這對我內心來說卻是不夠現實的,後來我開始寫小說,一堆人建議我也寫穿越文,總是過不了我心中的那一關。
無獨有偶,我也漸漸發現,一堆與我成長年代相仿的先進們,他們發表好多作品,背景居然大部份都是千里之外的「天山」、「江南」、「五嶽」,那些與我習慣生活環境相距千里之外的地方,「台灣人」怎麼可能寫得過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懷抱著這個命題,我認真地認為,撰寫武俠小說要開創新天地,勢必無法再以神州大陸為背景,我們只能寫台灣,因為我們只有台灣。.
如果我們能為《步步驚心》中,遠在北京紫禁城內四爺(雍正皇帝)與若曦的故事共鳴,為何我們卻對同一時期的台灣毫無聯想空間、乃至於一片空白?事實上就在雍正皇帝與若曦愛恨糾葛的同一時期(約1720年)前後,彰化縣和美鎮曾發生過大洪水,朝廷在大肚溪南北岸設置「彰化縣」,又因為水師戰船所需,大批移墾的漢人往內山侵墾,導致日月潭水社群以「骨宗」為首的原住民報復,此「骨宗事件」讓中部移墾的漢人一度人人自危。
我沒有能力編織中古玄幻的魔法世界、也沒有智識建構億萬星辰的科幻背景,但是我對於將「清領時期」的歷史轉換成敘事的舞台充滿熱情。金庸或古龍筆下的武俠人物、門派「高來高去」,似乎完全不必為吃穿用度煩惱,在《藍張興》的故事之中,即便享有江湖盛名的武林高手,依然是個「打工仔」,被墾闢拓荒的「大頭家」延請,完全借重「鏢師」、「隘丁」、「練勇」等職業身份,每個人都必須克盡職責才能「過生活」。
我期許,《藍張興:大肚溪南北岸的拓荒者們》只是個開端,台灣人從此也可以有專屬這片土地的武俠世界觀,這部小說就是我生於斯、長於斯三十餘年來,獻給福爾摩莎的情書。
台灣清領時期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歲在辛丑,台灣爆發以杜君英、朱一貴為首的叛亂事件,造成台灣府陷落,文武官員陸續走避澎湖、福建避難,朝廷因此調派大軍,任命台灣鎮總兵藍廷珍(原籍漳州漳浦)署福建水師提督領軍,迅速來台掃蕩叛軍;這段朱一貴走反的事蹟,後人傳有「鴨母王」之名傳誦,那不是我們今日要敘述的故事。
之後,清廷在追捕朱一貴、杜君英餘黨的過程中,有感諸羅縣幅員過廣、管理不易,決議將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部份自諸羅縣劃分出來,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間新置一縣,面對當時縣境內「番社龐雜」的狀況,新的縣被命名「彰化縣」,縣治設於半線庄。
同一時期,若我們將目光調離台灣南部的戰場,朱一貴之亂掃平後,藍廷珍留駐台灣各處巡視,就在大肚溪以北、今日台中盆地的地方(原作張鎮庄,康熙五十八年已廢庄遺民),物色上那一大片佈滿沼澤、雜草的荒地,興起加以整治拓荒的念頭。
藍廷珍特意將從湄洲天后宮請來的媽祖金身,原本供奉在台南大天后宮,又迎奉至大墩「藍興宮」(今「萬春宮」),並就此長奉媽祖迄今,而我們這部叫《藍張興》的歷史武俠小說,就是自雍正年後的這一時期(一七二○年代)、環繞大肚溪南北岸兩端,開啟故事的篇章。
為保全故事文本在真實史實下的創作空間,本故事中登場的歷史人物,一個都不會登場,僅供人物對談時不時言及,登場人物係基於歷史時空創作而出,悉數杜撰,還望周知。此外,由於人物多採台語對白,但凡有稱「番」或「番仔」字眼,為保還原時人說話狀況將予以保留,在對話框之外的敘述句則會悉數避免,望各路賢達尚祈鑒諒。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歲在甲辰,首任彰化知縣談經正上任,在廷珍所物色原屬張鎮庄的範疇,新立「藍張興庄」,談經正在同一年度核發藍廷珍單准墾執照,委由笠事蔡克俊統理,其墾照名稱即為【藍張興】。
本作《藍張興》初版付梓於二○二四年,亦歲在甲辰,幸逢【藍張興】墾照核發屆滿三百周年,豈非巧合?幸甚、幸甚,引以為序。
導讀
台灣清領時期康熙六十年(1721年),歲在辛丑,台灣爆發以杜君英、朱一貴為首的叛亂事件,造成台灣府陷落,文武官員陸續走避澎湖、福建避難,朝廷因此調派大軍,任命台灣鎮總兵藍廷珍(原籍漳州漳浦)署福建水師提督領軍,迅速來台掃蕩叛軍;這段朱一貴走反的事蹟,後人傳有「鴨母王」之名傳誦,那不是我們今日要敘述的故事。
之後,清廷在追捕朱一貴、杜君英餘黨的過程中,有感諸羅縣幅員過廣、管理不易,決議將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部份自諸羅縣劃分出來,在雍正元年(1723年)間新置一縣,面對當時縣境內「番社龐雜」的狀況,新的縣被命名「彰化縣」,縣治設於半線庄。
同一時期,若我們將目光調離台灣南部的戰場,朱一貴之亂掃平後,藍廷珍留駐台灣各處巡視,就在大肚溪以北、今日台中盆地的地方(原作張鎮庄,康熙五十八年已廢庄遣民),物色上那一大片佈滿沼澤、雜草的荒地,興起加以整治拓荒的念頭。
\藍廷珍特意將從湄洲天后宮請來的媽祖金身,原本供奉在台南大天后宮,遷奉至台中市大墩地區的「藍興宮」,並就此長奉媽祖迄今,而我們這部命名做《藍張興》的台灣歷史武俠小說,就是自雍正年後(1720年代)的這一時期,環繞大肚溪南北岸兩端拓荒者們,開展故事的篇章。
為保全故事文本在真實史實下的創作空間,本故事中登場的歷史人物,一個都不會登場,僅供人物對談時不時言及,登場人物係基於歷史時空前提下,憑空創作而出,悉數杜撰,還望周知。此外,由於人物多採台語對白,但凡有稱「番」或「番仔」字眼,為保還原時人說話狀況將予以保留,在對話框之外的敘述句則會悉數避免,望各路賢達尚祈鑒諒。
雍正二年(1724年),歲在甲辰,彰化知縣談經正上任,在藍廷珍物色原屬張鎮庄的範疇,新立「藍張興庄」,談經正核發藍廷珍印單准墾執照,委由管事蔡克俊桶理,其墾照名稱即為【藍張興】。
本作初版付梓於2024年,亦歲在甲辰,幸逢【藍張興】墾照獲得核發逢300周年,豈非天意?幸甚、幸甚,引以為序。
自序
自從2016年下願投入長篇小說創作事業以來,2024年是第八個年頭,如今總算能夠以我能力企及最好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一切深懷感恩。
我出生於1989年6月,搭上龍年尾巴同屆的「福份」,正好是國民教育「部編本」的末班車。我猶記得我學生時代,手上看得漫畫是橫山光輝的《三國志》、《水滸傳》,打得電腦遊戲是〈三國無雙〉、〈軒轅劍〉及〈仙劍奇俠傳〉。
當時最流行的電視劇是一波一波金庸武俠小說的改編浪潮,從《笑傲江湖》、《神鵰俠侶》、《鹿鼎記》等等的戲劇,我看過好幾遍;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如此冀望,我也想成為像金庸那樣的小說家,讓自己發想的故事情節改編成影視劇,風靡傳誦這顆星球,其實此刻,我這個心願依然沒有動搖,但我已經不想成為金庸了。
記得2010年初有一度中國「穿越劇」非常流行,華文小說網也興起書寫穿越文的浪潮。「穿越回去?怎麼可能,光開口說話就露餡,還要跟歷史人物談戀愛?」這對我內心來說卻是不夠現實的,後來我開始寫小說,一堆人建議我也寫穿越文,總是過不了我心中的那一關。
無獨有偶,我也漸漸發現,一堆與我成長年代相仿的先進們,他們發表好多作品,背景居然大部份都是千里之外的「天山」、「江南」、「五嶽」,那些與我習慣生活環境相距千里之外的地方,「台灣人」怎麼可能寫得過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懷抱著這個命題,我認真地認為,撰寫武俠小說要開創新天地,勢必無法再以神州大陸為背景,我們只能寫台灣,因為我們只有台灣。.
如果我們能為《步步驚心》中,遠在北京紫禁城內四爺(雍正皇帝)與若曦的故事共鳴,為何我們卻對同一時期的台灣毫無聯想空間、乃至於一片空白?事實上就在雍正皇帝與若曦愛恨糾葛的同一時期(約1720年)前後,彰化縣和美鎮曾發生過大洪水,朝廷在大肚溪南北岸設置「彰化縣」,又因為水師戰船所需,大批移墾的漢人往內山侵墾,導致日月潭水社群以「骨宗」為首的原住民報復,此「骨宗事件」讓中部移墾的漢人一度人人自危。
我沒有能力編織中古玄幻的魔法世界、也沒有智識建構億萬星辰的科幻背景,但是我對於將「清領時期」的歷史轉換成敘事的舞台充滿熱情。金庸或古龍筆下的武俠人物、門派「高來高去」,似乎完全不必為吃穿用度煩惱,在《藍張興》的故事之中,即便享有江湖盛名的武林高手,依然是個「打工仔」,被墾闢拓荒的「大頭家」延請,完全借重「鏢師」、「隘丁」、「練勇」等職業身份,每個人都必須克盡職責才能「過生活」。
我期許,《藍張興:大肚溪南北岸的拓荒者們》只是個開端,台灣人從此也可以有專屬這片土地的武俠世界觀,這部小說就是我生於斯、長於斯三十餘年來,獻給福爾摩莎的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