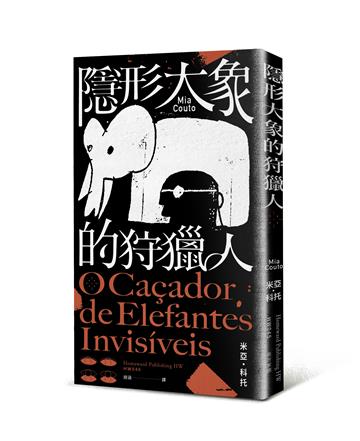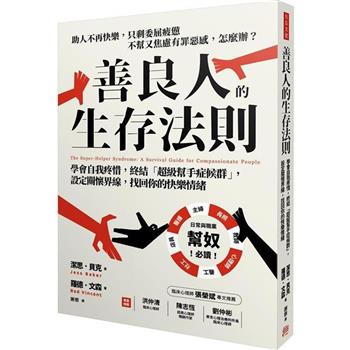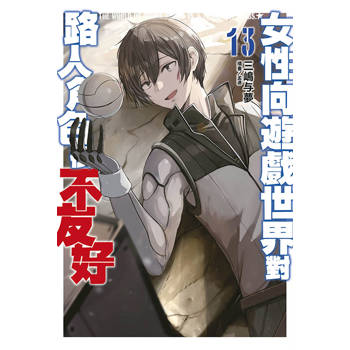代譯後記
現實與記憶——《隱形大象的狩獵人》中的詩性書寫
米亞·科托曾在《耶穌撒冷》(Jesusalém,2009)中,借德國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之口批判人類的遺忘本性:「整個世界的歷史不過是一本影像之書,反映了人類最狂暴、最盲目的慾望:遺忘。」書寫現實、抵抗遺忘,是貫穿科托整個創作生涯的重要使命,它促使科托寫下第一部長篇小說《夢遊的大地》(Terra Sonâmbula,1992),無疑也是他在上個世紀八、九〇年代創作一系列短篇小說的初衷。而當歷史的時針指向2020年,一場大流行病襲捲全球,非洲國家或許正經歷著後殖民時代最為嚴重的一次衝擊——並非因為疫情本身,而是指世人以疫情為由,對非洲複雜現實的又一次抹除和遺忘。科托試圖告訴讀者:在非洲,很多人在各種生存或精神危機的壓迫下,根本無暇顧及疫情——在當代莫三比克人眼裡,新冠肺炎從來不是唯一的問題,甚至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基於此,科托在疫情期間重回短篇小說創作,為葡萄牙著名週刊《視野》(Visão)寫下二十六篇專欄故事,後經修改、擴寫,於2021年10月出版成書,名為《隱形大象的狩獵人》(O Caçador de Elefantes Invisíveis)。
本書中,米亞·科托依舊聚焦莫三比克,以「狩獵人」的耐心和細緻入微的觀察力,書寫當代人在不同空間維度的個體與集體生活,挖掘被大流行病掩蓋的多重現實。這些現實往往是沉默的,幽居於世人的盲區,是那些「隱形的大象」,而科托作為「獵象人」,為小人物們提供了一個可被看見的舞台,帶領讀者了解其背後的集體不確定性、災難與創傷、希望與夢想。
每一個故事中,科托都向讀者展現兩個相互對立的世界。例如在〈一個溫柔的強盜〉和〈隱形大象的狩獵人〉裡,首都派來的防疫人員和衛生宣傳隊無法與偏遠貧困地區的居民互相理解,只能雞同鴨講:六十多歲的老人以為家門口拿著體溫槍、戴著面具和鞋套的年輕人是個強盜;獵人察佐則認為宣傳隊介紹的防疫方法都是無稽之談、不合常理。尷尬的無效溝通背後是一個令現代防疫觀念無從施展的莫三比克:這裡的人早在新冠病毒到來前就遭遇天花、肺結核、瘧疾、艾滋病和塵肺病的屠戮;醫院如此遙遠,窮人連在夢裡長途跋涉都不能抵達;門和牆壁都沒有的學校根本不需要封鎖,反正大部分孩子也上不了學;城市與農村、富人與窮人的生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葡萄牙語和本地語言的碰撞彰顯著數個世紀以來難以調和的文化對抗。
此外,米亞·科托還指出:如果大流行病是一場戰爭,那麼莫三比克內部持續不斷的戰爭也是另一種病毒,「戰爭和疾病並肩而行,就好像同一具軀體的兩隻手臂」。在〈旅行助手〉、〈抽星星菸的女人〉等故事中,科托重點書寫北部省份德爾加杜角的戰爭難民。該地近年來成為境內伊斯蘭國附屬組織襲擊平民的主要區域。故事中的難民不得不坐卡車滿世界逃亡,其父母被同為穆斯林的恐怖分子殺死,都來不及下葬;舉家逃亡的人甚至要掐死剛出生的嬰兒,因為嬰兒啼哭會招來全族殺身之禍。除了北部恐怖主義襲擊,莫三比克中部也時有政府軍與反對派火併;殖民戰爭的陰影仍然長久地籠罩親歷者心頭。科托書寫流離失所者和戰爭倖存者的創傷以及他們對死亡的記憶:在〈紅色連身裙〉中,戰爭奪走了「我」的丈夫和兒子,渴望再次成為母親的「我」帶著一件紅色連身裙踏上公路尋子,卻被一群士兵所俘虜,死裡逃生;〈靈魂織物〉裡的葡萄牙上校因參加過莫三比克殖民戰爭,晚年飽受記憶折磨,所幸女兒假扮成軍官悉心照料,最終他脫下軍裝,安然入睡,彷彿從未有過戰爭。可見和平與戰爭至今仍是莫三比克最常見的一組對立現實。
當代莫三比克社會的家庭關係同樣是科托非常關注的主題。在〈罪孽〉、〈我的第一位父親〉、〈另一個她〉等故事中,男性(或父親)總是酗酒、外遇、羞辱打罵妻兒或限制其自由,甚至強姦其他女孩,致使後者懷孕被趕出家門、流落他鄉。科托筆下的家庭多是充滿怨恨和悲傷的地方,它們折射出莫三比克社會日常生活的癥結:倘若一屋之下都有如此多的悲劇,人們又如何能擁有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
另一方面,現代文明與城市生活同樣衝擊著許多莫三比克人:〈盲鳥〉中的兒子忙於工作,無暇陪伴父親,孤獨的老人自稱眼底長出了白色的翅膀,他拒絕出門,因為城市到處都是樓房,沒有公園,也沒有天空。〈蝴蝶〉裡的秘書馬萊娜是跨國公司裡的小員工,丈夫因失業而脾氣暴躁,她的上司看到一隻蝴蝶飛進室內就要大動干戈,而她眼中的蝴蝶如同美麗的詩歌,落在一幅名為〈城市的天空〉的畫上,堅定地選擇一小片藍色作為「最終的停泊點」,「外面的天空對飛行來說,太稀缺;對死亡來說,太骯髒」。在〈石像座談會〉中,科托提及當今世界的反雕像浪潮:午夜時分,退休的歷史學家儒利奧目睹樓下廣場上的達迦馬石像走下基座,去找鄰居卡蒙斯雕像「開會」,因為時代變了,雕像曾是歷史上宗主國榮耀的象徵,卻與當下的去殖民化思想格格不入。今天的人們沈迷於重新定義「英雄」,審判、否定和譴責人類的過去。於是儒利奧決定聯合本地巫師新蓋一個廣場:「本地人和外來者,朋友和敵人」,所有人的雕像都會在同一片土地上立起。而這一切在儒利奧的妻子眼裡,不過是瘋人之舉。
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對立現實共同構成莫三比克的真實國情,並且讓讀者看到,莫三比克在擁有自身境況的同時,從未脫離世界成為孤島,它的現實也是世界現實的一部分。正如書中所說:「在這個如此灰暗的世界裡,其實我們所有人都同處在一片礦井之下。只有當它的頂部被一場災難摧毀時,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都在一起。」當然,米亞·科托並未侷限於書寫痛苦,他也在許多故事中寫到溫情、勇氣與希望:戰火中出生的嬰兒最終在家族女性的集體保護下免遭死亡;妻子永久驅逐強姦少女的丈夫,收留早育喪子的女孩,命自己的孩子視其為母親,使其不再顛沛流離;鄰居因小兒子病逝悲痛欲絕,於是「我」每天下午前去拜訪,像小兒子生前那樣為她梳頭,然後「踮著腳尖」,邁著小步子離開,「彷彿胸膛裡跳動著一顆不屬於我的心臟」。在全書最後一個故事〈無名之國〉裡,失去母親的小古斯塔沃從外面撿來一個破布娃娃,整日抱著它坐在客廳裡,聽電視新聞播報員講述世界各國如何身處水深火熱之中。他堅持認為布娃娃也是一個國家,而父親終於在某一天理解了兒子:小古斯塔沃是對的,玩偶就是一個國家,它的疆域像一個擁抱那樣寬廣,從未有人在那個國度死去。
米亞·科托曾經對媒體表示,像莫三比克人這樣時刻生活在戰爭、貧窮和道德危機之中的民族不能太悲觀主義。因此,他在《隱形大象的狩獵人》這本書中不僅捕捉和重塑現實,也讓讀者看到一絲溫暖:儘管莫三比克人患著不同的疾病,經歷著相同而又不同的戰爭,活在孤獨、悲傷或憤怒之中,卻同樣擁有愛與做夢的能力。
從事寫作數十年,米亞·科托早已蛻變為一位紮根於本土現實的世界性作家。近年來的作品中,我們已經很難看到他早期對葡萄牙語近乎癡迷的顛覆性改造,如「混成詞」的使用,因而他的語言愈發簡潔並具有普適性。但科托從未放棄展現莫三比克人獨特的思維與豐富的世界觀。本書中,這一點體現在許多可能令人驚異的語言表達上,例如一些看似奇怪的隱喻,「我們把房子從一地搬到另一地,但它從未長出根莖」,「早晨誕生了,我看見大海飛翔在我們村莊上空」;或者一些出其不意的詞語或短語搭配,如「一滴淚(⋯⋯)斬斷了他的雙腳」。所謂的「科托式」語言,正是指這種後結構主義層面的創新——用一種反叛性修辭打破常規性邏輯,從而釋放出言語之外原本靜默的巨大能量。此外,我們也會從本書不乏犀利的幽默、對人性的深沉思考和人道主義關懷中,一眼認出這依舊是讀者所熟悉的米亞·科托。我想特別提及的是,本書的中譯者胡涵十分敏銳地捕捉到了原文的這些特點,也精準地在譯文中予以再現,因此,相信漢語世界的讀者一定也會被書中的世界和情感所觸動,那裡的世界觀「更詩意、更純淨」,也「更深刻」。更多細節,就留待讀者慢慢發現與品味吧。
2024年,全球新冠肺炎似乎告一段落。人們摘下口罩,像疫情前一樣在日常中奔波,很多人甚至已經忘記前幾年的生活。此時出版《隱形大象的狩獵人》中譯本,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作者向不同世界的讀者發出的邀請:讓我們在時間的吉光片羽中留住現實與真實的記憶。米亞·科托將再一次向我們證明:記憶不可廢棄,因為它是人類面對未來的前提和基礎;記憶也有待補充,因為世上有太多正在發生或發生過的事,我們並不知曉,卻應該正視。文學雖不能直接改變世界,但可以修復記憶、重塑歷史,它是夜幕下的燈塔,照亮現實賴以生存的每一處空間,讓沉迷於盛世謊言的人有所清醒,也讓身陷苦難和徬徨之人看到溫暖和希望。這就是書寫的意義,也是米亞·科托在《隱形大象的狩獵人》裡想要傳遞給讀者的力量。
金心藝
2024年1月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