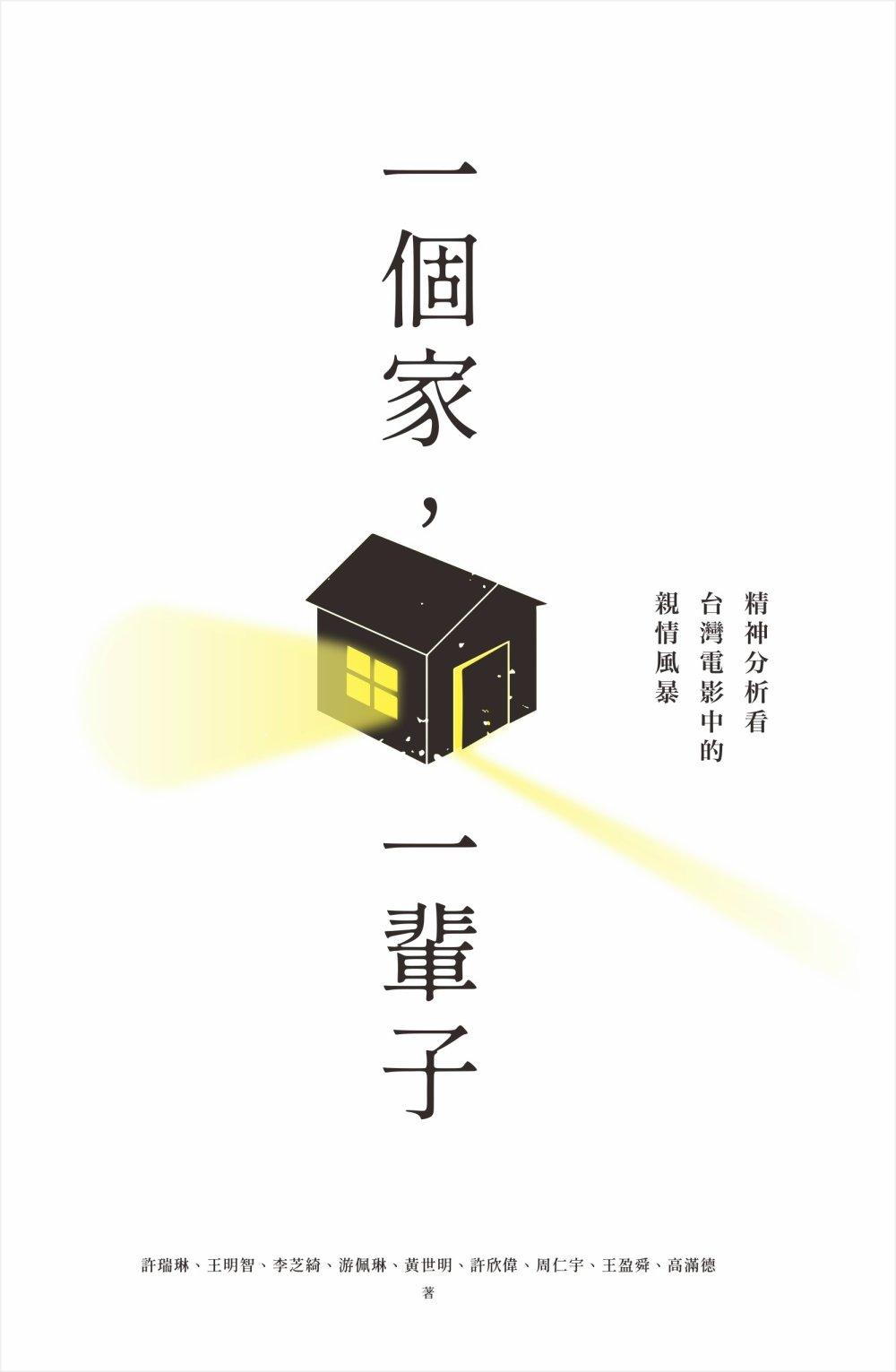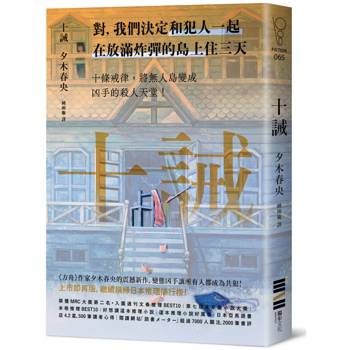過去幾年來,以家庭衝突為主軸的台灣電影大放異彩,質量兼備。鍾孟宏的《瀑布》、《陽光普照》,阮鳳儀的《美國女孩》,許承傑的《孤味》以及楊雅喆的《血觀音》等等,深刻勾勒出母女與父子,乃至於家庭或是家族的衝突,有些赤裸呈現,更多隱晦幽微。
再往前推移,李安的家庭(父親)三部曲:《推手》、《囍宴》、《飲食男女》,將父親這個角色擺在家庭與文化脈絡中,傳統與新潮,西方與東方,個人與群體,撞擊出難以直視的懾人火花。再如楊德昌、蔡明亮的作品中若隱若現的家庭/親情/性別衝擊,不同世代導演對於家庭關係有各自見解。親情猶如一場風暴,見證台灣社會的世代變遷。
精神分析工作者對於親子衝突點滴在心頭,對於伊底帕斯一點也不陌生,且看臨床工作者們如何在診療室/躺椅之外,築起精神分析與電影之間的對話。
◎「家人」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作為一家人有什麼意義呢?如果無法真實的親近,「家人」可能只是共同被收在一個「家屋」底下的人。
◎人要跟自己的本能慾望奮戰,也要跟祖先父母的期待搏鬥,被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力量牽著鼻子走,還要在現實之下求得生存和平衡,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角力讓「家」未必是個避難的地方,而是刮著永不停歇的風暴。
◎在台灣,「我的」比「我」重要太多了。我的成績、我的教養、我的人緣、我的科系、我的理想、我的收入、我的能力......,我們經常太過關心自我的產品,而忘了自我本身;太過注意孩子的表現,而忘了那個正在活著的孩子。
◎不管是《孤味》裡強勢的母親,《瀑布》裡流浪的母親,《血觀音》裡操控的母親,還是《美國女孩》裡,那個帶著女兒逃離命運、又回到命運的愧疚的母親,每個女兒都被迫唇齒相依,這些女兒能走出蚌殼、走出命運嗎?
◎台灣當代父子互動總摻雜著暴力、死亡、競爭、自戀創傷。父子之間激盪出拚輸贏的氛圍(或許稱之為伊底帕斯情結),是否為發展上之必要?台灣父子在被閹割和暴力攻擊之間,在承擔和閃躲之間,很難找到一個中介地帶求取平衡。
◎無論性別體制如何壓抑,同志對愛的渴求,對於性特質的認同,加上不被家庭接受,浪跡天涯卻與沒有血緣的客體組成另類家庭,在在刺激精神分析對於家庭的觀點:什麼是家庭?血緣是唯一的基礎?怎樣的家庭對個體的發展有利?
◎理解及表達對家人的情感常是最困難的事。蔡明亮的人物無法藉由對話或日常生活儀式與家人溝通,他們總是透過動機不明的行為、複雜的幻想或可能是自己無意識地渴望的「意外」暴露出家庭的緊張關係,有時反而因此釋放家庭的壓力。
◎當我們遭逢無法理解的情境時,便會在心裡引發一場風暴。這或許會波及身邊的人,在那人身上點燃另一場摧毀一切的風暴。但也或許,身處風暴中的兩人能夠彼此了解並因而成長。《美國女孩》不只說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也讓我們隨著故事經歷自己的風暴,並讓我們曉得:對流浪的人們來說,故鄉不必然是哪個地方,而是被深刻理解的經驗。
作者簡介:
許瑞琳 精神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王明智 諮商心理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李芝綺 臨床心理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游佩琳 精神科醫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黃世明 精神科醫師,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研究」學院碩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許欣偉 精神科醫師、東倫敦大學精神分析研究碩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周仁宇 精神科醫師、人類學博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王盈舜 自由紀錄片影像工作者、清華大學電機系學士、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藝術創作碩士(MFA)
高滿德 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與歷史碩士
章節試閱
親密一「家」+「人」
文: 李芝綺
親密又陌生的一家人
「家人」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作為一家人有什麼意義呢?如果無法真實的親近,「家人」可能只是共同被收在一個「家屋」底下的人。台灣2019年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談的是陌生的分離,也是渴望在一起的親密,或者可能是兩者間的相互矛盾與糾結。法國精神分析師葛林(Andre Green)曾說過,對潛意識來說,分離就是痛楚;但要如何才能感覺是「在一起」呢?想起元朝管道昇對丈夫欲納妾所做的〈我儂詞〉,既深情又哀怨,衍生出許多耐人尋味的不同解讀:「爾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將咱兩個一起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爾,爾泥中有我......。」所謂「在一起」的感覺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融合或相互認同嗎?或者要互相對等的愛才是所謂的親密?或者解讀成一種我還有你,你還有我的相互依偎?又或者人與人間的親近皆需要打破自我而重塑,才有可能真正的心心相印?回到潛意識裡來感受,親近也許類似心上有著彼此靠近或相似的感覺「愛你和我都一樣」 ,自我有他人力比多(libido)能量的投注,即對方心裡有自己的存在,以及像在治療室裡專注跟隨與回應著個案……,這麼說著說著,彷若「親密」的自體與客體交集勾勒出兩大川流的匯聚,也是此篇想圍繞探討的主軸:自戀與認同。
先來簡介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的角色與劇情,這是導演張作驥的第九部作品,也被稱為「母親三部曲」的最終部。影片在台南四草的綠色隧道水域中緩行開啟,悄然靜謐,只感受得到時間的挪移,接著家的場景在微光的雨中呈現,似乎暗喻了這個家也在轉換的過渡期中掙扎,充滿著未知與隱藏的能量。主角群包括剛出獄的未婚媽媽小夢及狂妄自私的另一半阿文(在角頭間挑釁插旗維生),兩人年少所生的孩子阿全由阿媽王鳯照顧長大,和舅舅跟著阿媽一起學演歌仔戲。幹練認命的王鳯在丈夫張軍雄失智後有了極端的改變,衝突對立的關係突然轉為溫柔而貼心,但恬靜的晚年生活仍在張軍雄的同性舊愛成恩來訪後透出強勁的高度張力。張軍雄是上校退伍的外省人,自小喜愛舞蹈而主導軍中藝工隊,但受母親以愛之名所箝制,終其一生未能擇己所愛,這也是張作驥導演想表達的主題:家人之間無可逃脫的捆綁與折磨。而同樣未獲丈夫真愛滿足的王鳳,因為匱乏的自我也無法認同與關愛同為女性的女兒,以致形成了一種重演尋愛、討愛而悲哀的代間傳遞。然而劇中並存著另一種象徵自由與真實親近的敍事,由火雞哥突兀的流浪漢形象與兀自的吶喊所構成,正和阿全排除眾議、努力呵護火雞蛋的孵化、悉心照顧小雞相互呼應。
這部電影帶給我許多真實的觸動,除了導演安排了真實的體驗(而不是演出來的)與真實身份特質的演員之外,劇情也頗貼近台灣人的真實生活:家庭在日常中有尷尬,平順中有揪心,恰如看似一般美滿的家庭,卻可能在家族團聚時被長輩問到大考或逼婚,剎那間又像回到了傳統威權的年代,不被傾聽與尊重的心聲,勾出早已塵封的幼年心理創傷或無法消化的家族秘密等;此外,劇中每個角色都很飽滿,刻畫出每個人都似主角的心路歷程;最後,多元文化匯聚也是台灣的特色,劇中廟口的野台戲與家景中飄揚的書法字體互尬,乍看之下有著強烈的違和感,但這不也是實實在在的台灣景況嗎?親密又陌生的台灣家庭關係,不管怎樣都還是要年節團聚,所以電影中的每一餐,就象徵著家人的聚合,是台灣人最最重要的事(或形式),也表達了各種親疏關係的更迭。頻繁出現的樓梯,則如導演所說,像是串連起代間的橋樑,上上下下流通著,引領家人與觀者看向樓上的兒女與孫兒,再轉向樓下的父母與祖先。
台灣人怎麼看待「家人」關係呢?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家」的甲骨文是個會意字,上面是「宀」,表示與室家有關,下面是「豕」,即豬。古代生產力低下,人們多在屋子裏養豬,所以房子裹有豬就成了人家的標誌;本義為屋內,住所。「家庭」則指一種以婚姻、血緣、收養或同居等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單位。
上述兩定義著重在家的物質與組成,直覺上與英文「家庭」的意涵就有所差距,譬如「We are a family.」中的family有著熟悉而親密的意思,推論英文文化觀點中的「家」,似乎更為強調關係中的親近與滋養。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於2022年發表了一份針對十七個先進國家的調查,了解各國人的重要人生意義。被問到近期的人生中,什麼事情讓您感到有意義、滿足、滿意?為什麼?相較於其它國家前兩名「家庭」、「職涯」的一致性,台灣人重要的人生意義排行第一竟是「社會」,內容涵括「國家建設」、「教育體系」、「社會福利」、「生活環境」、「安全」、「國家應對Covid」等,排名第二則是「物質福祉」(19%),第三名才是「家庭」(15%),第四名則是「自由」(12%)、興趣(10%)。這結果讓人訝異,不禁思索對台灣人而言,家庭關係與意義是因為夠好或夠糟而被放到第三名呢?或者是因為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台灣人深受衝擊而恐慌,因此重視社會大環境的管控更甚於家庭?
回到家人關係的熟悉與親密面向,國外亦有深刻探討不同組成、情感關係家人的電影,如《家有家規》、《空屋情人》、《東京奏鳴曲》等。而在《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中,反映的是相愛的關係但無法被家庭所接納;相對的,身為一家人卻無法感受親密,這些衝突正映照出內在對親密關係的掙扎:難道愛對方就無法同時愛自己?是否要先愛自己才能愛別人?難道對自己正向的感覺,不會讓人際互動更為親近與活力?
讓我們來看看精神分析裡的觀點。
寧願只愛自己的愛——談自戀
阿全的老師告訴阿全,只有自然常溫下的蛋才能孵出小雞,阿全篤定的守候著,並保護其不受舅舅的逗弄與侵擾。生命之初的給予,仍需要客體與守護的環境,這時的幼體在溫尼考特的說法是「完全的依賴」,完全的無助也無知、無情的使用著照顧者,猶如「一顆包在一層超薄而又完美的外殻中的生蛋」,完美但不禁任何刺激,隨時會因輕輕一擊而流個稀巴爛。唯有無所選擇、無所懷疑的守護生命的到來,一種母性的執著,才可能抱持(Holding)嬰兒的成長。嬰兒從動作、感覺、功能經驗中開始有了「我」的主體,分辨出自己內在和外在客體的分野,並從照顧者的眼中一點一滴的認識這個世界,心理和身體一樣地羽翼漸豐而茁壯。反之,在缺乏溫度與無法抵禦頻繁侵擾的狀況下,自我便可能殘缺不全或扭曲防衛,溫尼考特說「這個早期階段的焦慮不是閹割焦慮或分離焦慮。......實際上是對滅絕的焦慮。」極端的狀況下,如自我寄生在宿主,或繭居而活,一再地問著「你到底還要我怎麼樣?」、「你和我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打開自己,讓你進來?」與外在接觸等同於威脅與滅絕,自我寧願留在殻裡,看似能自給自足,但實際上心智永不會長大(未整合狀態)或早已死亡。簡言之,生命之初,為了活下去,人不得不自戀。
那寧願「愛」自己,是自戀嗎?溫尼考特曾說「愛」這個字不夠精確,而「分離」這個字太過粗糙。也許「愛」統包了太多的內涵與定義。上述未曾被滋養照顧的自我、分崩離析的自我,無法將力比多能量投注在他人外在事物上,也許連「愛」自己也說不上。如同劇中的小夢,一直向外追尋著夢想中的愛人,一個好好把自己放在心上的對象,眼前的阿文是不可一世、被愛寵滿的,但他卻完全不看小夢一眼,小夢在犠牲自己的情慾關係裡仍是孤寂、破碎而受盡折磨的。
最初佛洛伊德的「原始自戀」概念,意指嬰兒所有的性慾能量都是指向自己的,感覺自己完美而全能,週遭注意力皆灌注在自身,但隨著成長,遭受的挫折(不滿足)會打斷這自戀的專注,由於無法獲得滿足,而將能量轉向他人,企圖尋求不完美卻摸得到的滿足,即慢慢轉成對客體的愛。客體性慾及自戀性慾被視為反比的關係,佛洛伊德將性慾能量「力比多」比喻為阿米巴原蟲的原生質,在阿米巴身體中心的原生質越多,伸出去的偽足中的原生質就越少;當力比多能量因受挫等原因從客體再度撤回自身,即被稱作另一種自戀——次級自戀。
後來,寇哈特則提出正常的自戀發展,是每個人終其一生都需要的健康的自戀,而非傳統認定的,自戀就是自大、幼稚、暴露狂等病態。如同兒童是活在一個有超級英雄、超級力量的世界,有時幻想自己完美,有時想像照顧者萬能,沒有人會譏笑或否定孩子的天真與全能。但自戀疾患的病人,相反的,正因為早年缺乏童年活力與創意,才必須防衛性地保護著脆弱又誇張的自我形象。寇哈特最後完成的理論,認為健康的自體(Self)發展是在三種自體客體(selfobject)經驗的環境中演化而來:需要客體愉悅和認可;需要和強大他者形成關係(能敬仰並和其融合成鎮定、全能的形象);需要喚起兩人本質相似的感受。
在電影中,阿全逃出家人的紛擾,轉向火雞哥的幾個段落,都象徵著穩定客體的涵容、接納與協助,如背景港口之於海洋般自在而溫暖;但在臨床工作中,面對創傷纍纍的小病人時,涵容與被涵容、思考在眼前的孩子是正常或異常的自戀,卻常令人難以招架,譬如當一個破壞小魔王重覆問著治療師:「那你喜歡我嗎?」卻無法作出任何互動遊戲與溝通時,難免會讓我陷入一種空虛而表面的懷疑,治療師看似不重要或被拒絕,但實質上又對病人的主體性絕對必要,如同寇哈特所說的自戀移情,在治療互動中,感受到病人需要先被看見真實的自己(鏡映移情)、甚至被認定是受喜歡的,才能強化其孱弱不實的自體;而病人要感受到自己的強壯的同時,也要延伸擴展到週遭人,譬如治療師也必須和其一樣的強壯、無所不能,這是一種理想化移情,也可能是一種孿生移情的再現。但唯有被允許發展這些移情,病人才能發展出更有凝聚力性、韌性與堅固的自我感。反映出病態自戀在其虛張聲勢的外表下,內在卻是空虛而匱乏的,除了要保護自己,還是保護自己,力比多能量滯留於此,哪兒也分不出去。要從生的「蛋」中,孵化出穩固實在的自體,需要重新沉浸在可靠健康的依附關係裡。
「你為什麼不愛我?」除了小夢尋尋覓覓「能把自己放在心裡」(recognition看見自己)的人,在男友心裡卻連蕃茄都比不上;王鳳酸諷張軍雄「跟男人睡有什麼好?」也是不懂自己為何被拋下;張軍雄失智後的過往受暴經驗回返、張軍雄母親的遺書(要兒子娶能顧家的王鳳)等,都刺痛的割劃出重要客體在其心裡的鞭苔痕跡。無法視孩子為主體而作回應的客體,嚴重影響到主體自戀發展的品質,可能讓一個人永遠無法感受如何愛自己、什麼是自己想要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無止盡地討好客體,認為客體的目標就是自己的標竿,哪怕只為了看到這重要他人的一抹微笑,那可能就是肯定自己是好的吧!?而客體把個體當成為滿足自我需要來作支配、使用,把孩子當成自己的延伸,就算彼此痛苦仍無法分化,這樣綑綁糾結的失序與混亂,在家庭裡會相互牽連,也會一代一代地傳遞,悲愴也無以名之。費倫齊在〈認同攻擊者:早期創傷和解離〉的文章裡提及這最初的親職適應災難:
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恐懼:(它們之間的平衡塑造了心理發展),在自我及其功能發展之前,任何超出其處理能力的精神器官的外部壓力都會被感知為整個心靈本身的崩潰,一種對毀滅的焦慮。費倫齊:自我主張需要看護者的積極適應,這是先天傾向出現的先決條件。環境中的生活在自我主張的原則(被認為是愛)和適應環境的原則之間轉換——一種適應他人的壓力,超出了溫柔的心靈的容納能力,這是被感知的作為一種充滿恐懼的震驚,迫使嬰兒放棄任何自我肯定的反應。
身處其中的孩子,莫名所以,自小不斷地防禦、反應著侵入自我的干擾,也一直茫然找尋著渴望而缺乏的「愛」,生之本能驅使我們尋找,但死之本能又不斷讓我們重覆習慣的模式而跌跤。張作驥導演十年內拍攝的「母親三部曲」即坦露自己身為獨子和母親糾纏的一生:「《當愛來的時候》是我在發洩對母親的愛恨和怨,《醉,生夢死》是把我太怕母親死掉離開我的恐懼夢境拍出來。拍《陌生人》就是因為思念、想要紀念她,也是跟她揮手說再見。」也真實地呈現母親凡事以愛之名而包羅綿密的掌控,讓孩子無處可逃:
「我喜歡那個樓梯。......那是一個三代之間或幾代之間的橋樑。每部片子,我儘量都弄到三代。因為我家沒有三代同堂,我父母親就我一個小孩,永遠打不了麻將啊。......我二十年來,每天晚上都打電話,除了兩年多我(入獄)不能打,每天兩個小時電話,我媽都在罵我,連出國都是,因為我不能跟他講我出國,我一講出國,我媽會每天拜飛機,她非常擔心。不管到德國還哪,電話費回來都是十幾萬,她也沒有手機,直接撥室內電話,哇操,電話費嚇死人。」
甚至在母親失智症離世後,母親的影子仍罩在張作驥的自我上,難以哀悼!其中,受虐與自戀似乎有搭勾在一起的味道。他說:
「有人跟我說,這是你所有作品中,故事說得最白的一次,我認為是六十分啦,不能再複雜了,因為我沒有能力再處理那個複雜。現在晚上有的時候,欸我要打電話,好無聊喔,我媽早走了。我九點到十點晚上一定要打電話,開擴音,聽她罵我,已經養成習慣,現在走了一年多,還會覺得,欸時間到了,應該要打電話。……」。
在結束自戀段落前,我還想談談令人印象深刻的阿文。劇中阿全的爸爸阿文,對阿全而言是除了更生人媽媽外,另一個親密的陌生人。他的自大幼稚、火爆挑釁、無法無天與目中無人,連在道上混的都搖頭看不下去,最後在廟口前的親子相聚時刻,尋仇而來的死對頭,斃命的槍擊嘠然終止了阿文的人生......。他讓我想到葛林提出的「雙重自戀」——生之自戀與死之自戀(或稱作正向自戀與負向自戀)。阿文在螢幕裡傳遞出那忍無可忍的憤恨與挫折暴力,卻激起觀者一種瀕臨殺戮死亡的恐怖焦躁感,似一種病態的極度自戀:雖說正向自戀是為維護自體、滋養誇大自體,但又嗅到底下有著負向自戀的死亡氣息,當自戀和死亡本能融合在一起,那高度張力不僅能在瞬間捏碎旁人螻蟻般的生命,更對自身招來破壞與毁滅危險,將自己帶向死亡或虛無凋零,儘管阿文在意識中完全沒有想要傷害自己的念頭。
葛林認為驅力(力比多)如佛洛伊德所述,自我本應為愛慾服務,將驅力投入自我喜歡、重視的事物,但若此享樂原則受挫,則會轉向相反的目的,為仇恨的本能衝動服務。同樣不斷地切斷連結和斬除愛慾,成為自我中心,但他認為死之自戀更像是負向的自戀挹注,並不是為達到統整合一的自戀滿足,而是使主體的自我貧困接近到毁滅的地步,在自我逐漸消失、不參與下,走向精神死亡。那麼,我們可否大膽的臆測,如同生死本能之如影隨形,生之自戀與死之自戀也可能是雙螺旋的配對,時不時的競相出沒?
(待續)
親密一「家」+「人」
文: 李芝綺
親密又陌生的一家人
「家人」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作為一家人有什麼意義呢?如果無法真實的親近,「家人」可能只是共同被收在一個「家屋」底下的人。台灣2019年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談的是陌生的分離,也是渴望在一起的親密,或者可能是兩者間的相互矛盾與糾結。法國精神分析師葛林(Andre Green)曾說過,對潛意識來說,分離就是痛楚;但要如何才能感覺是「在一起」呢?想起元朝管道昇對丈夫欲納妾所做的〈我儂詞〉,既深情又哀怨,衍生出許多耐人尋味的不同解讀:「爾儂我儂,忒煞情多。...
目錄
許瑞琳 賦/附/複/復生的母女關係
王明智 漫漫回家路:台灣電影中的同志與家庭
李芝綺 親密一「家」+「人」
游佩琳 談父親的慾望:寡言木訥的父親與躲在水缸裡的子女
黃世明 時代洪流與家族框架下的人:從《茶金》的幾個角色談起
許欣偉 行過死蔭幽谷的台式父子群像
周仁宇 斷裂與翻越:《美國女孩》對療癒工作的啟示
王盈舜 「家」的皺褶,在紀錄片現場
高滿德 奇異如夢:蔡明亮電影中的家庭情感張力
蔡榮裕 精神分析走進電影裡,尋找什麼伴手禮送自己呢?
許瑞琳 賦/附/複/復生的母女關係
王明智 漫漫回家路:台灣電影中的同志與家庭
李芝綺 親密一「家」+「人」
游佩琳 談父親的慾望:寡言木訥的父親與躲在水缸裡的子女
黃世明 時代洪流與家族框架下的人:從《茶金》的幾個角色談起
許欣偉 行過死蔭幽谷的台式父子群像
周仁宇 斷裂與翻越:《美國女孩》對療癒工作的啟示
王盈舜 「家」的皺褶,在紀錄片現場
高滿德 奇異如夢:蔡明亮電影中的家庭情感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