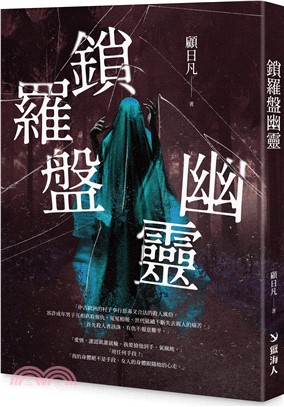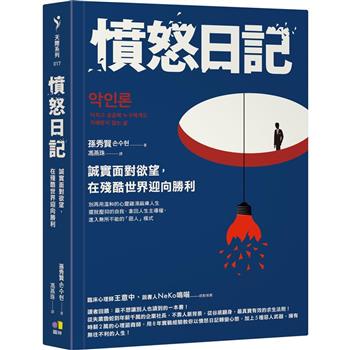8964 事件的新學年,xx大學的異域探索學會組織活動,會長何守聰率領共八人,先到同學家鄉的吉澳島參觀十年一度『安龍大醮』,後到鎖羅盤廢村露營探秘,期間一男二女爭風吃醋,此時刮起颱風,小島發生一起密室殺人命案。
他們在村外海邊紮營,二側大山環抱,中藏溪谷,流入潟湖,湖中有島,燒烤夜,八號烈風警訊,眾人對8964各抒己見,未來互有去留。
第二天早上泥石流傾瀉,封印出口,一男生徹夜未返,死在潟湖小島,裸著下體,死時漲潮,小島變做密室,一名在祠堂辱罵鬼神及向神位扔石的男生也牽涉三角戀愛糾葛,當晚另一名男生也死在村公所,先前那男生鬼上身,掐著一名女生的頸項殺她報仇,何守聰打昏他解圍,揭發七人捲入情海波瀾。
第三天早上被掐脖子的女生在山崗看風景,該名男生鬼上身發作,走上去將她推落懸崖殺死,男生逃跑到祠堂死去,跪拜神位,跟鎖羅盤村幽靈殺人的傳聞如出一轍。
何守聰看出謎團重重,撲朔迷離,追查下去,是幽靈殺人?醋海翻波?還是另有秘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鎖羅盤幽靈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鎖羅盤幽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