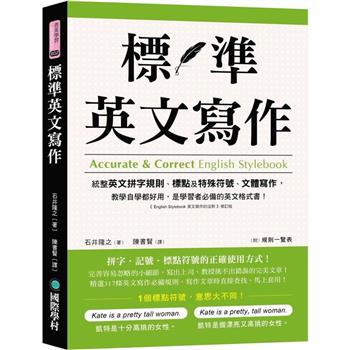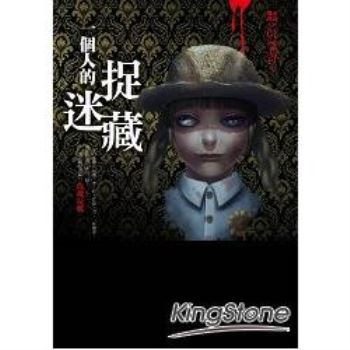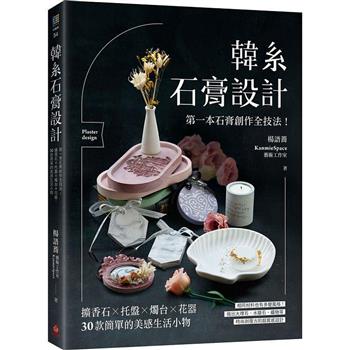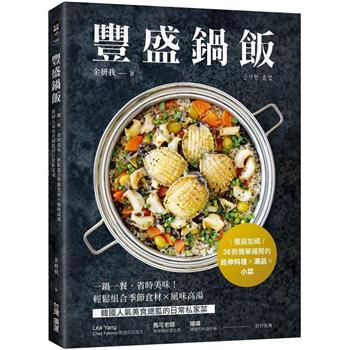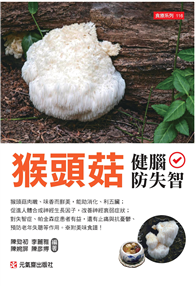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
內容簡介
本詩集收錄名音樂詞曲創作人/詩人李子恆五十年來之經典歌詞與詩作。此次跨界出版《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內容極其豐富【輯一】我的心樂府—故鄉的囈語、【輯二】舊陌新桑、以及花非花集。他的作品從早期的抒情性逐漸轉進深沉睿智的哲學思考,加入人性透析與社會感懷;賞讀李子恆的詩與歌,著實令人擊節讚歎。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子恆
金門古寧頭人
一九五六年於金門瓊林出生長大
十六歲離鄉赴臺就學
一九七八年服兵役時寫〈秋蟬〉
國立藝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前身)求學期間
即投入詞曲創作與唱片製作
至今累積詞曲五百多首
唱片製作百餘張
個人演唱專輯:
2004「母親的容顔」
2011「落番」
2012「回家」
平時亦嘗試新詩創作
本詩集即結集歷年來所積累的作品
作為詩歌生涯第一本詩集。
李子恆
金門古寧頭人
一九五六年於金門瓊林出生長大
十六歲離鄉赴臺就學
一九七八年服兵役時寫〈秋蟬〉
國立藝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前身)求學期間
即投入詞曲創作與唱片製作
至今累積詞曲五百多首
唱片製作百餘張
個人演唱專輯:
2004「母親的容顔」
2011「落番」
2012「回家」
平時亦嘗試新詩創作
本詩集即結集歷年來所積累的作品
作為詩歌生涯第一本詩集。
目錄
推薦序 《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
幾點觀察及致敬 /黃克全 7
自序 入世與出世 /李子恆 9
【輯一】 我的心樂府—故鄉的囈語 11
〔歌詞〕
秋蟬 12
歲月 14
歸航 16
紅蜻蜓 18
番薯情(閩南語) 20
回家 22
鄉愁音樂盒 24
采薇 26
寂寞的嘹亮 28
〔詩〕
田浦記行三則 29
真善美 36
鄉愁的樣子 40
悲劇的完成 44
在故鄉飲一二秋日 48
詠后水頭—金沙溪千年芳華錄 50
詠東埔—金沙溪千年芳華錄 52
鄉關三疊 54
紅與黑 57
月光屋(上) 62
月光屋(中) 65
月光屋(下) 68
【輯二】 舊陌新桑 69
〔歌詞〕
奔流 70
牽手 72
風雨無阻 74
飄零 76
雨簷 78
新芽 80
暗舞 82
海岸線 84
晨星 86
〔詩〕
牧羊人 88
叛離者 90
黑白兩三則 92
孤單的蟲子 94
夜宿武當 97
仰望 101
無題風 102
相逢 104
偶然 106
夢醒 108
露水 110
露水之二 111
枯木 112
枯木之二—復活(手機漫遊記) 113
九月風 120
零點零三分 124
和平獎空椅組曲 127
木頭與石頭的辯證 132
無題的原型 136
松果子之一 140
松果子之二 141
雲系列 143
後現代之無題組曲 147
廢墟組曲(民謠風) 150
遙遠 155
北方贈書兩則 158
未完成 162
花非花集—雪泥鴻爪之人生旁頁 164
紫系列 165
獨居的姿態 168
失香園 170
諸神的酒佐 172
香格里拉 174
烽火 176
親情 179
出水記 182
答客問 184
虛構的白 186
【結語】 190
幾點觀察及致敬 /黃克全 7
自序 入世與出世 /李子恆 9
【輯一】 我的心樂府—故鄉的囈語 11
〔歌詞〕
秋蟬 12
歲月 14
歸航 16
紅蜻蜓 18
番薯情(閩南語) 20
回家 22
鄉愁音樂盒 24
采薇 26
寂寞的嘹亮 28
〔詩〕
田浦記行三則 29
真善美 36
鄉愁的樣子 40
悲劇的完成 44
在故鄉飲一二秋日 48
詠后水頭—金沙溪千年芳華錄 50
詠東埔—金沙溪千年芳華錄 52
鄉關三疊 54
紅與黑 57
月光屋(上) 62
月光屋(中) 65
月光屋(下) 68
【輯二】 舊陌新桑 69
〔歌詞〕
奔流 70
牽手 72
風雨無阻 74
飄零 76
雨簷 78
新芽 80
暗舞 82
海岸線 84
晨星 86
〔詩〕
牧羊人 88
叛離者 90
黑白兩三則 92
孤單的蟲子 94
夜宿武當 97
仰望 101
無題風 102
相逢 104
偶然 106
夢醒 108
露水 110
露水之二 111
枯木 112
枯木之二—復活(手機漫遊記) 113
九月風 120
零點零三分 124
和平獎空椅組曲 127
木頭與石頭的辯證 132
無題的原型 136
松果子之一 140
松果子之二 141
雲系列 143
後現代之無題組曲 147
廢墟組曲(民謠風) 150
遙遠 155
北方贈書兩則 158
未完成 162
花非花集—雪泥鴻爪之人生旁頁 164
紫系列 165
獨居的姿態 168
失香園 170
諸神的酒佐 172
香格里拉 174
烽火 176
親情 179
出水記 182
答客問 184
虛構的白 186
【結語】 190
序
推薦序
《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幾點觀察及致敬
黃克全
約二十多年前,作為詞曲家的李子恆,就把他自己試寫現代詩的作品寄給我看,印象中他大概寫了約50首以各種花卉、植物為摹寫對象的短詩。所以我算是長期觀察李子恆詩路文風發展的忠實讀者。這次接到他這本有一部分我從沒讀過的處女作詩歌集《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不由令我感到驚艷。謹提出我個人幾點小小觀察,略表致敬之意。
語言具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性,物質開敞,精神隱蔽。所以語言也具備開敞與隱蔽的雙重性。李子恆的詩歌,早期偏物質、開敞,但他似乎有從物質逐漸移往理性、精神的趨勢,以是他晚近的詩較為隱晦些。但大體說來,他那結合古典與現代的詩語法仍很純淨,練達,少形容詞拖沓贅語。這使他筆下的詩作拋顯出一種令人欣羨的舒朗氣質。
關於李子恆的詩從物質、開敞,逐漸移往理性及精神、隱蔽的趨勢,這一點,這裡不妨再多說幾句。我發現到,越到晚期,李子恆越有二元辯證下朝向一元的趨勢;這無疑是一種理性、智性的表現。李子恆自己或有察覺,自認不能停滯在一己抒情,必須對生命有著更高懸的超越及透視。譬如其〈花非花集〉初稿寫於2000年,但我想稿末的結語係寫於本詩集出版前,而短短百來言的文中,拋露出二元的辯證,如「沒有一日不在開的狀態,也沒有一日不在謝的狀態」、「幻滅與重生」、「永始與永終」,這二元性及其辯證是過程,為要趨向那渾淪、圓融之境的一元,那才是吾人靈魂的安憩之地。
阿根廷詩人波赫士寫過一篇故事叫〈皇宮寓言〉,敘述皇帝帶詩人遊覽美侖美奐的皇宮,參觀結束後,詩人寫了一首短詩,這首詩居然把整座宏偉宮殿包含了起來。皇帝大吃一驚,直呼:「你搶走了我的宮殿」。李子恆不少詩就這樣搶走了我們心目中的宮殿,譬如我們那遙遠的鄉愁,譬如我們內心那永恆的抒情性、譬如那撫慰我們心靈深邃之處的「一」⋯⋯。
自序
入世與出世
李子恆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謝林在其《藝術哲學》一書中有句名言:「建築是凝固的音樂」。十九世紀,德國音樂理論暨作曲家霍普德曼補充道:「音樂是流動的建築」。
在這視覺與聽覺交替著時間、位置、乃至身分的同時,兩者必然存在著某一交織點,至細處,可能千萬分之一毫釐,交織後,可能相去千萬里,在物理學上,此點大約不出量子,因波粒之同時存在,故毫釐與千里也相對存在。然而在精神學上,那一點,恍兮惚兮,鴻蒙無貌,怎麼形容都不是,於是乎聽覺與視覺,動態與靜態,形上和形下,都渾然為一體之象了,還要去分別甚麼?
我的詩我的歌,又要去分別甚麼? 最遠的(最老的),寫在雙十年華,最近的(最年輕的),寫在從心所欲之將至,一路上,又能去分別甚麼入世與出世?顯然,在詩歌的領域裡,我也早被統一了。
部份因受邀而發表的詩,有它們幸運的偶然,其餘,窗門深鎖,不出世也不入世,只好隱世,髮蒼蒼,語茫茫,卻依稀一副鏘鏘然,實在愧歉了它們的誕生,而今果真要結集面世,恍兮惚兮,就不能不提及二人了: 激勵者王學敏,影舞者黃克全—反之亦然。王學敏詩、歌、散文、琴、畫都好,是位才女,對己對人對事都有著理想化的善意的執著—此詩集就是這樣被催生。黃克全則是台灣文壇要角,又是金門文學翹楚,獲獎無數,詩、散文、論述、小說等無不精闢,兩位兄嫂多次激勵與相挺,那麼我又何必在人生的顛盪中,老是去矜持甚麼是入世,又甚麼是出世?
又為了不讓詩集太單薄,揀選歷來獲各類獎項、或較具詩性的歌詞助陣,意在加重捧書的手感,而不在標榜個人的資歷。詩集再分二輯,【輯一】我的心樂府—故鄉的囈語,源於黃克全編纂《金門當代文學大歷史》之〈李子恆的金門新樂府〉一文。【輯二】舊陌新桑,就頗有野放於邊屋外那些蹁躚與微風的意味了。書末,花非花集,則是雪泥鴻爪之人生旁頁。
詩宜領會不宜多解,然而我還是忍不住做了程度上的自解,在黃克全大椽筆下定義的那些「新樂府」,相對我而言,既是一種負重,又何嘗不是一種承擔。
—寫在出版之前
《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幾點觀察及致敬
黃克全
約二十多年前,作為詞曲家的李子恆,就把他自己試寫現代詩的作品寄給我看,印象中他大概寫了約50首以各種花卉、植物為摹寫對象的短詩。所以我算是長期觀察李子恆詩路文風發展的忠實讀者。這次接到他這本有一部分我從沒讀過的處女作詩歌集《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不由令我感到驚艷。謹提出我個人幾點小小觀察,略表致敬之意。
語言具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性,物質開敞,精神隱蔽。所以語言也具備開敞與隱蔽的雙重性。李子恆的詩歌,早期偏物質、開敞,但他似乎有從物質逐漸移往理性、精神的趨勢,以是他晚近的詩較為隱晦些。但大體說來,他那結合古典與現代的詩語法仍很純淨,練達,少形容詞拖沓贅語。這使他筆下的詩作拋顯出一種令人欣羨的舒朗氣質。
關於李子恆的詩從物質、開敞,逐漸移往理性及精神、隱蔽的趨勢,這一點,這裡不妨再多說幾句。我發現到,越到晚期,李子恆越有二元辯證下朝向一元的趨勢;這無疑是一種理性、智性的表現。李子恆自己或有察覺,自認不能停滯在一己抒情,必須對生命有著更高懸的超越及透視。譬如其〈花非花集〉初稿寫於2000年,但我想稿末的結語係寫於本詩集出版前,而短短百來言的文中,拋露出二元的辯證,如「沒有一日不在開的狀態,也沒有一日不在謝的狀態」、「幻滅與重生」、「永始與永終」,這二元性及其辯證是過程,為要趨向那渾淪、圓融之境的一元,那才是吾人靈魂的安憩之地。
阿根廷詩人波赫士寫過一篇故事叫〈皇宮寓言〉,敘述皇帝帶詩人遊覽美侖美奐的皇宮,參觀結束後,詩人寫了一首短詩,這首詩居然把整座宏偉宮殿包含了起來。皇帝大吃一驚,直呼:「你搶走了我的宮殿」。李子恆不少詩就這樣搶走了我們心目中的宮殿,譬如我們那遙遠的鄉愁,譬如我們內心那永恆的抒情性、譬如那撫慰我們心靈深邃之處的「一」⋯⋯。
自序
入世與出世
李子恆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謝林在其《藝術哲學》一書中有句名言:「建築是凝固的音樂」。十九世紀,德國音樂理論暨作曲家霍普德曼補充道:「音樂是流動的建築」。
在這視覺與聽覺交替著時間、位置、乃至身分的同時,兩者必然存在著某一交織點,至細處,可能千萬分之一毫釐,交織後,可能相去千萬里,在物理學上,此點大約不出量子,因波粒之同時存在,故毫釐與千里也相對存在。然而在精神學上,那一點,恍兮惚兮,鴻蒙無貌,怎麼形容都不是,於是乎聽覺與視覺,動態與靜態,形上和形下,都渾然為一體之象了,還要去分別甚麼?
我的詩我的歌,又要去分別甚麼? 最遠的(最老的),寫在雙十年華,最近的(最年輕的),寫在從心所欲之將至,一路上,又能去分別甚麼入世與出世?顯然,在詩歌的領域裡,我也早被統一了。
部份因受邀而發表的詩,有它們幸運的偶然,其餘,窗門深鎖,不出世也不入世,只好隱世,髮蒼蒼,語茫茫,卻依稀一副鏘鏘然,實在愧歉了它們的誕生,而今果真要結集面世,恍兮惚兮,就不能不提及二人了: 激勵者王學敏,影舞者黃克全—反之亦然。王學敏詩、歌、散文、琴、畫都好,是位才女,對己對人對事都有著理想化的善意的執著—此詩集就是這樣被催生。黃克全則是台灣文壇要角,又是金門文學翹楚,獲獎無數,詩、散文、論述、小說等無不精闢,兩位兄嫂多次激勵與相挺,那麼我又何必在人生的顛盪中,老是去矜持甚麼是入世,又甚麼是出世?
又為了不讓詩集太單薄,揀選歷來獲各類獎項、或較具詩性的歌詞助陣,意在加重捧書的手感,而不在標榜個人的資歷。詩集再分二輯,【輯一】我的心樂府—故鄉的囈語,源於黃克全編纂《金門當代文學大歷史》之〈李子恆的金門新樂府〉一文。【輯二】舊陌新桑,就頗有野放於邊屋外那些蹁躚與微風的意味了。書末,花非花集,則是雪泥鴻爪之人生旁頁。
詩宜領會不宜多解,然而我還是忍不住做了程度上的自解,在黃克全大椽筆下定義的那些「新樂府」,相對我而言,既是一種負重,又何嘗不是一種承擔。
—寫在出版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