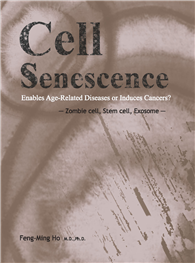當人們心中的善意徹底崩潰,這個世界還剩下什麼?
《血色童話》作者、「瑞典的史蒂芬.金」再一力作
當「恐懼」降臨純樸小鎮,人們心中的邪惡即將覺醒⋯⋯
六位截然不同的非凡角色,如何發掘內心的力量,一同拯救家園?
披著驚悚、警世的外衣,探討人性衝突與柔軟的巔峰之作
唯有恐懼能讓人脫下面具,現出真實面貌。
某天早上,一座亮黃色的貨櫃出現在瑞典諾爾泰利耶市港口,無人知道它的來歷。
貨櫃開啟的瞬間,惡夢也跟著流竄出來。裡面裝了二十八具難民的屍體,腐爛發臭,氣味衝出貨櫃、瀰漫港口,黑色淤積物傾瀉而出。然而除了屍水,被染得黝黑的貨櫃裡還有東西——無以名狀的「恐懼」。
恐懼滲入流經城鎮的河水,一切開始改變。人心中的善意崩壞,變為懷疑與爭執,甚至上升為肢體暴力。腐敗的不只屍體,還有這座小鎮與生活其中的人。
而在這個鎮上,有一些人成為解決此事的關鍵:
公園管理員馬克斯曾在古巴生活,卻因為在當地經歷意外,正在服用抗憂鬱藥。他的童年好友約翰經營保齡球館,痛恨市政府,也痛恨外國人。
馬可和瑪莉亞是一對兄妹,年幼時和父母一起從波士尼亞逃到瑞典。馬可是個成功的基金經理人,瑪麗亞則是揚名國際的模特兒。只是,他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最後是超市出納員希芙以及她來自黑幫世家的閨蜜安娜。希芙外表看起來是個普通單親媽媽,卻擁有特殊能力——她來自古老的女巫血脈,能聽見某處將會發生的事,卻無法知道確切時間。但她不曉得馬克斯也有類似的預知能力,只是他是能看見即將發生的意外,卻不會知道位置。
對未知的恐懼,對外來者的恐懼,那些不問原因的恐懼。諾爾泰利耶市就是世界的縮影,透過作者的筆,我們看見各種情緒實體化。單純的恐懼會致人於死嗎?與他人不同是必須壓抑、隱藏的缺陷嗎?當人因為害怕而不擇手段,世界是否距離毀滅更近了一步?
《血色善意》是我寫過的最溫柔的作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是最令人不安的。這部作品沒有太多暴力或血腥的場面;相反地,故事有個令人不安的前提:在我的故鄉諾爾泰利耶市的幾個秋季月份裡,有些事件導致簡單、日常的善意徹底瓦解。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如果善意消失,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外國媒體好評推薦:
倫德維斯特故事的力量和他促進人們互相了解的熱情是不容否認的。
——《衛報》
溫暖、堅定、令人身歷其境。
——《每日郵報》
令人感受深刻⋯⋯《血色善意》扣人心弦。
——《SFX》雜誌
我很少讀到結構如此縝密的故事。這部作品總共有七百多頁,卻一直牢牢地抓住我不放。故事怎麼能夠如此迷人?⋯⋯這是倫德維斯特寫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瑞典《耶夫勒日報》(Gefle Dagblad)
隨著倫德維斯特越來越專注於疏通人類靈魂裡的微妙管路,他已成為當代文學中獨特而迫切的聲音。
——《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
作者簡介: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John Ajvide Lindqvist)
瑞典人,生於一九六八年,成長於斯德哥爾摩郊區小鎮布雷奇堡(Blackeberg),從小夢想能闖出一番名堂。他曾是魔術師,還在北歐魔術牌技比賽中贏得第二名。之後成為喜劇脫口秀表演者長達十二年。後來轉戰進入劇作圈,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電視劇本《Reuter & Skoog》,並擁有多部舞台劇作。他的第一部小說《血色童話》在瑞典造成轟動,二○○五年獲選為挪威的最佳小說獎,並入選為瑞典電台文學獎。
譯者簡介:
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荒島男孩》、《雌性物種》、《柏青哥》等書。
章節試閱
我是來自虛無的風暴
1
女孩站在瑞典諾爾泰利耶市立圖書館門外,她叫希芙.范恩,今年十三歲。她前後左右張望,像在尋找什麼。她走了幾步,看似要離開,卻又停下來,轉身繼續前後左右張望。她在原地上下抬腳,搖搖頭。看來她比較像在等待,不是在找東西。希芙在等待某樣東西從未知的方向過來。
希芙有些特別,即使她沒有顯得焦慮,我們或許還是會繼續關注她。她稍微低於平均身高,稍微高於平均體重,你不會說她又矮又胖,但不免會有這樣的念頭。她留著一頭中等長度的褐髮,瀏海垂在深邃的眼睛上。渾圓的臉頰加上突出的下巴讓她看似因努伊特人,你可以想像她身穿海豹皮,手拿捕鯨叉。實際上她穿著有點舊的黑外套,一邊肩膀背的螢光黃背包也頗有年代。
她又準備要放棄了。她拿出手機查看時間:下午三點四十三分。她看向圖書館外的咖啡廳。一位帶嬰兒車的母親在其中一桌喝茶,年輕情侶在另一桌聊得開心。男子端著托盤,正在想辦法走出店門。希芙微微聳肩,攤開雙手,把手機塞回口袋,邁步離開。她哼著老調的民謠,不像十三歲小孩會唱的歌。
她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山姆霍公司的小巴士沿著畢爾伯街高速開來,駕駛忙著看儀表板,車子行經錄影帶店時大幅搖晃。希芙旋過身,再次看向咖啡廳。
端著托盤的男子已經走出店門,正要穿過母親和嬰兒車之間,走向一張空桌。他側身想擠過去,結果屁股撞上嬰兒車。母親一定忘了剎車,嬰兒車一碰便動了起來。前輪越過最頂端階梯——總共有三階——的邊緣,等後輪也滾過去,嬰兒車便開始加速往下滑。
由於男子的身體擋住她的視線,母親尚未注意到發生什麼事。嬰兒車顛著滑下另一階,加速朝馬路衝去,而小巴士正以時速至少五十公里的車速行駛在路上。兩件移動的物體即將相撞,造成悲劇。
直到嬰兒車滑到人行道上繼續前進,母親才看到怎麼回事。她的臉扭曲成驚恐的面具,發出絕望的尖叫。她跳起身,撞倒她的桌子,但她知道來不及了。她的人生即將分崩離析。
嬰兒車的前輪剛越過人行道邊緣時,希芙抓住了把手。小巴士從不到半公尺外呼嘯而過,吹起希芙的瀏海,露出底下因不可置信而睜大的雙眼。
嬰兒車裡的孩子哭了。孩子的母親歇斯底里地啜泣,緊抱著希芙,害她無法呼吸。越過女子的肩膀,她看到撞上嬰兒車的男子雙手摀住嘴巴,托盤掉在腳邊。希芙眨眨眼。這一刻,她意識到從本質上來說,她不是一般人。
2
「快點呀!你在看什麼?」
約翰退後兩步,仔細打量塔狀穀倉側面生鏽的梯子。馬克思朝他揮揮手,約翰指向梯子大約中段距離地面三十公尺的地方。「那邊不是斷了嗎?」
馬克思站到他旁邊,舉手遮著眼睛,擋住低垂的陽光。他看完後聳聳肩。「所以咧?」
「這樣不太好吧?梯子壞掉的話?」
「所以我們才帶了工具呀。」
馬克思搖搖袋子。他們從馬克思家的工具小屋搜刮了一些類似登山設備的用具,繩索、彈簧掛鉤、釘鞋。約翰搔搔後頸。「我不確定耶⋯⋯」
「糟糕!蹲下!」
標著「歐達人」的廂型車沿著碼頭開來,兩名男孩趕忙躲到電箱後面。不難判斷他們不該執行這個計畫,只要看看圍籬上顯眼的黃色標示就知道了。標示下方恰好有個凹洞,深度足以讓纖瘦的身體鑽過去。
馬克思和約翰都很瘦,應該說都是皮包骨。雖然兩人都滿十三歲了,四肢卻纖細得跟小小孩一樣—很高的小小孩。約翰腳踩長筒襪,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馬克思則一百七十八公分,兩人都還在長高。他們有同樣狹長、纖細的臉,同樣亞麻金色的頭髮,以及啥都不在乎的造型。要不是眼睛不同,他們簡直可說是兄弟。馬克思的藍色大眼淺到幾乎透明,尤其是反映天色的時候。約翰的眼睛是普通的褐色,下方的眼袋顯示他睡不好。他們就學以來就是最好的朋友。
「我們要不就爬,要不就不爬。」廂型車開走後,他們重新站到梯子底端。馬克思說:「我絕對會爬啦。」
「好啦,好啦。」約翰說,「我們要是摔死可別怪我。」
他們分別在腰上綁好繩索。馬克思比較會打繩結,因此由他負責打結,最後在繩子末端掛上彈簧掛鉤。「我們要不斷把掛鉤固定在上方幾階的橫檔上,懂嗎?如果你踩的橫檔斷了⋯⋯」
「如果固定掛鉤的橫檔斷了——怎麼辦?」
馬克思專注盯著約翰好一會兒,長到約翰得撇開頭。「幹嘛?你看什麼看?」
「你都不會希望自己最好死了嗎?」
「會— 但不代表我想死。」
「不然代表什麼?」
約翰聳聳肩。「代表我不想活了。」
「你要怎麼不活又不死?你是打算變成殭屍之類的嗎?」
「我們可以快點爬嗎?」
「當然。」
馬克思立刻大步邁向梯子,爬了十階,才第一次掛上鉤子。約翰待在地上,抬頭看他。
他們十歲時聽說幾個高中男生爬了諾爾泰利耶港的塔狀穀倉,便開始討論要不要去爬。過去幾年間,這個話題不時出現,每次都是馬克思提的。
兩人當中,馬克思比較大膽。以前他們在葛拉馬斯特街約翰家後方的小丘玩奇幻遊戲時,總是馬克思爬上樹的最高點,也是馬克思差點跌下陡坡摔到堤佛利街。他十二歲就拿到潛水證照,跟父母去印度洋上的模里西斯度假。約翰則從來沒離開過瑞典。
馬克思上方的光線使他成為不具形狀的影子。他爬上梯子,每次把掛鉤換到不同的橫檔都發出響亮的哐啷聲。約翰掂掂手中的掛鉤,嘆了一口氣,走到梯子底端。
他最怕的不是橫檔斷掉,而是整個梯子從塔狀穀倉側面分離,帶著他們往外傾倒,生鏽鋼鐵形成的巨大蒼蠅拍把他們像蒼蠅壓死。然而開始爬之後,他發現他錯了。橫檔斷掉更糟糕。
馬克思領頭,所以是他在測試梯子是否穩固。如果發生意外,馬克思幾乎肯定會罹難。當然他也可能跌在約翰身上,兩人一起滾著墜地而死,但可能性不高。如果有人要死,也是馬克思。
約翰費力再爬了幾階。他才離地五公尺,但當他低頭看,肚子仍忍不住抽搐。他把彈簧掛鉤固定在頭上看來最沒生鏽的橫檔。
馬克思朝他叫道:「怎麼樣?」
約翰想對他比大拇指,但他不敢放手。於是他大叫:「我快趕上你了!」
「要我等你嗎?」
「不用,沒關係!」
約翰不希望馬克思看到他開始冒汗,他的手掌黏在粗糙生鏽的鐵桿上,胸口湧現一陣顫慄。他繼續爬,試著回去想剛才在想的事。
如果有人要死,也是馬克思。
說實在話,這個念頭沒有鼓勵到他,反而讓他覺得糟透了。假如馬克思死了,約翰身邊就只剩下發瘋的媽媽。沒有人跟他去小丘或打電動,沒有人陪他說話,沒有人了解他。簡而言之,他會落得徹底孤單一人。
所以⋯⋯
所以他寧可梯子脫落,把他們像蒼蠅一起壓扁。沒錯,生活中的鳥事太多,他經常覺得不想活了,甚至真的開口說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只要馬克思在,他就可以活;少了馬克思,他就活不下去。
爬了十五公尺後,當他往下看地面,他不再那麼肯定了。他只希望趕快結束。他將額頭抵著前方的橫檔,桿子好細— 跟他腳踩的那根一樣。這些脆弱的鐵柱是他唯一的支點,保護他不至跌落,把五臟六腑撒得水泥地上到處都是。
「上帝啊,」他喃喃說,「親愛的上帝,他媽的混蛋,請讓我們活下來。你只要這次替我做點什麼,我就會努力少恨你一點。」
他閉上眼睛,繼續爬了三、四、五、六階。這時出事了。水冷的手指揪住他的肺,像擰抹布一樣扭,他感到身體被往下拖。約翰的雙手像鉗子緊抓著橫檔,他用牙齒咬住最靠近嘴巴的橫檔,當作絕望的額外安全措施,身子則緊貼著梯子,像被揍的狗一樣顫抖,不肯放開嘴裡的骨頭。然後他搞懂了。他忘了鬆開彈簧掛鉤,現在掛鉤在他下方好幾階,阻止他繼續前進。
他眼中冒出淚水,雙手拒絕鬆開,他急促地淺淺喘氣。要是他現在跌下去,掛鉤扣住的橫檔不可能撐住他的重量,他只能爬下去解開掛鉤。他強迫自己張開嘴,吐出幾片鐵鏽,往下看。
往下。
他感到最驚恐的是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放任一切發生,鬆手墜落,擺脫所有鳥事。再也不用整晚守夜,以防媽媽裸身跑到街上,對願意聽的人說教。再也不用時時害怕出事,害他落到寄養家庭。只要墜落,在空中懸浮一秒,然後讓他們哭,讓所有人哭。
即使要達成這個小目標,他也得先鬆開掛鉤。如果橫檔超乎預期沒有斷掉,他可能只會弄斷脊椎。他聽到馬克思的聲音從上方傳來:「超酷的吧?」
當下這一刻,約翰恨死了他最好的朋友。馬克思了解他,知道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馬克思不該讓他面對誘惑。馬克思漠不關心,蠢得要命,除非⋯⋯除非他一開始就這麼打算。約翰啜泣一聲,幾滴眼淚流下臉龐。或許馬克思希望他死。或許馬克思受夠約翰賴在他家,期望馬克思邀他留下來吃晚飯。或許他受夠了玩寶可夢,受夠了小丘上沒有人時他們仍會玩的奇幻遊戲。或許馬克思想擺脫他,於是選了這個方法。
他的悲傷轉為憤怒,驅使他爬下四階橫檔,解開掛鉤。
馬克思大喊:「你嚇壞了嗎?」
「沒有!」約翰奮力爬回剛才虛驚一場的位置,把掛鉤安全扣在頭上。
沒有!絕對沒有!
「我跟你說,梯子沒問題。」馬克思往下喊,「只是這邊有點彎掉。」
約翰把愚蠢的念頭推到一旁。馬克思把他丟進這個狀況並不明智,但他沒有打算殺約翰。況且約翰要是死了,馬克思可就麻煩了。不管約翰把自己看得多低,他也知道死了十三歲小孩是大事,至少會登上當地報紙頭版,警察會來偵訊,亂成一團。他往下看,同樣的誘惑再次浮現,但型態不同。整個小鎮都會談論他。
不行!絕對不行!
馬克思提到梯子的狀態,表示他已經爬到約翰在地上時注意到的位置,大概一半。距離他現在的位置還很遠,他必須爬上去。他做為約翰.安德森辦不到,所以他必須變成別人,他必須成為⋯⋯強獸人。
多年來,他和馬克思玩的很多遊戲都發想自《魔戒》。他們讀過小說也看過電影,等不及續集上映了。他們會扮演精靈和哈比人、巫師和咕嚕,但他們最常假扮半獸人,因為半獸人簡單專注的心智扮起來很有趣。
去年冬天學校的滑雪比賽,他和馬克思都滑到精疲力盡。他們體格不夠強健,對滑雪也沒有熱誠。總長五公里的賽道滑到剩三公里時,他們都快放棄了—直到約翰悄聲對馬克思說:「我們是出征的強獸人。」馬克思咧嘴一笑,開始像機器擺動雪杖,學半獸人滑雪,目標明確,充滿決心。他們沿路高喊「殺啊」或「毀了他」的口號,最後在不錯的時間內抵達終點。
我是出征的強獸人。
約翰清空腦袋,只看到可口的小哈比人在塔狀穀倉頂端紮營,自以為安全。爬上去,攻擊,殺了他們。他怒吼一聲,把沉重的半獸人身軀往上抬。他嘴中仍能嘗到鐵鏽味,很好,很像血的味道,他對血的無比渴望驅使他前進。可口的小哈比人。
他像出征的強獸人繼續爬。每次他把掛鉤挪到上方的橫檔,都會發出輕蔑的悶哼,鄙視他必須使用的人類工具。他滿腦子只有半獸人的思緒,一路爬到梯子往右彎的地方。
馬克思從上方說:「你挺快的嘛!」約翰往上看。馬克思一手放開梯子,往後靠好看得清楚。這番景象讓約翰的胃一陣翻騰,幻想差點破滅,但他負擔不起。他咬緊牙關,嘶聲說:「我是出征的強獸人。」
馬克思皺起眉頭,露出有點高人一等的含糊笑容。約翰本來沒打算把話說出來,只是說溜嘴了。他最近注意到漸進的轉變。馬克思大他六個月,但重點或許不是年齡差距,而是態度或需求。馬克思正在離開過去七年他們一起打造的世界。
約翰陷入無解的兩難。他迫切想長大,逃離他住的公寓,還有媽媽難以預料的瘋狂所造成的窒息環境。但同時他又不想拋棄幻想,承擔身為大人的責任。最簡單的解法就是自己發瘋,或許有一天他會吧。
馬克思繼續爬,約翰哼了一聲。馬克思想要的話,就讓他去當無聊的大人吧。約翰會繼續當出征的強獸人,直到亞拉岡出現,砍掉他的頭。
亞拉岡!
也許那個混帳跟哈比人一塊兒在上頭?那麼復仇的時刻到了— 那個半精靈混種灑了多少半獸人的血,得替他們復仇!前進,前進!
約翰的幻想幾乎撐到最後。他沒有往下看,不去想他在哪兒。他只看到橫檔從半獸人的黃眼前晃過,他像機器移動雙手和掛鉤,想著血和復仇這類基本的念頭。爬到距離頂端三公尺時,馬克思攀過邊緣消失,接著大笑一聲。他不是因為成功而開心地笑,反而是別的原因。什麼事這麼有趣?約翰的猜測像楔子插進幻想,粉碎一切。
我是出征的⋯⋯我⋯⋯站在窄梯子上,梯子隨時可能與塔狀穀倉分離。
就是要靠近頂端,在這兒才會出事,蒼蠅拍才能以最大的力道落在他身上,到時候他們得用湯匙從水泥地把他挖起來。他的手開始發抖,可能跌落的高度劃開他的胃,帶來灼燒的痛。他夾緊屁股,都爬這麼遠了——可不要最後拉在褲子上。
馬克思在說話,但約翰聽不出來他說什麼。他深吸一口氣,心想:三公尺,十階,你做得到。不知怎地,他真的做到了,不過爬過邊緣後,他臉朝下癱倒在美好的平面上。他的頭腦發暈,混亂中他覺得聽到另一個聲音,一個他約略認出的聲音。
馬克思說:「你太厲害了!」什麼意思?約翰比他害怕多了,因此他的成就或許更了不起,但馬克思不太可能懂這種事。約翰抬起頭。
塔狀穀倉的屋頂邊緣有一道鐵欄杆,比梯子鏽得還糟糕。有人坐在欄杆旁,雙腿居然懸在邊緣。原來是馬可。馬克思在跟他說話,厲害的人是他。
暑假過後,馬可轉到他們班上,至今才一個多月。他來自波士尼亞,在瑞士住了兩年。他們家最近搬到諾爾泰利耶市,剛好就住在葛拉馬斯特街,離約翰家只有幾戶,但他跟馬可只打過招呼。馬可的爸爸經常坐在陽臺抽菸,約翰也跟他點頭致意過幾次。現在馬可坐在塔狀穀倉頂端,冷靜沉著,看來像在等公車。
「你聽到了嗎?」馬克思對約翰說,「馬可每天都上來耶!他就直接爬梯子,不像我們,扮得跟他媽的登山客一樣。」
馬克思又笑了,馬可也露出微笑。理論上,約翰理解這句話很好笑,但笑不是現在最靠近表面的情緒表達方式。況且開口笑很容易變成狂吐,因此他只疲憊地點頭。他覺得他站不起來。這時馬克思才注意到他不對勁,在他身旁蹲下來。
「你還好嗎?」他問,「很可怕嗎?」
「對,對,很可怕。」
「我同意,我都快嚇死了。」
「看不太出來。」
「你也知道我是什麼德行嘛。」
約翰確實知道。馬克思與父母關係不錯,卻仍堅持永遠、永遠不要跟爸爸一樣,即使他跟爸爸非常相似。他爸爸常說他靠著自律和努力,從普通的鷹架工人變成規模頗大的建設公司副總。他也是諾爾泰利耶市前二十名有錢的人,每年都出現在當地報紙的排行榜上。
他的自律從情緒表現也看得出來。非要出大事,馬克思的爸爸才會稍微展露他的感受。當他非常生氣,有時會扭扭鼻子,就這樣。馬克思許多地方也很類似,但不像爸爸,他至少有辦法笑。
約翰說:「我知道。」
「你起得來嗎?」
「我不太確定。」
「需要幫忙嗎?你看不到這片景觀太可惜了。」
馬克思撐著約翰站起來。他們站在直徑約八公尺的圓形屋頂上,約翰一時忘了計算面積的公式。他看向馬可,點點頭。「嗨。」
「嗨。」馬可面無表情。
「你真的每天都上來嗎?」
「沒有每天。」馬可帶著些微口音說,「大概⋯⋯每兩天吧。」
「那個洞是你挖的嗎?圍欄下面?」
馬可點頭,約翰也點頭回應。馬克思走過去站在馬可旁邊,靠著欄杆,大大張開雙臂。「哇賽!」他說,「諾爾泰利耶市!你他媽的諾爾泰利耶市!」
馬可扯扯他的褲腳,指向欄杆。「不要靠上去,欄杆鏽得很嚴重,你會摔成鬆餅。」
馬克思舉起雙手,後退一步。這時約翰才注意到馬可哪裡不一樣。他在學校的穿著總是乾淨整潔——感覺有點拘謹。燙平的襯衫扣到脖子,斜紋布褲看似早上才從乾洗店拿回來。假如是別人,肯定會成為嘲諷奚落的對象,但他不是別人。馬可周圍環繞一股沉睡的巨大力量,沒有人敢鬧他。
我是來自虛無的風暴
1
女孩站在瑞典諾爾泰利耶市立圖書館門外,她叫希芙.范恩,今年十三歲。她前後左右張望,像在尋找什麼。她走了幾步,看似要離開,卻又停下來,轉身繼續前後左右張望。她在原地上下抬腳,搖搖頭。看來她比較像在等待,不是在找東西。希芙在等待某樣東西從未知的方向過來。
希芙有些特別,即使她沒有顯得焦慮,我們或許還是會繼續關注她。她稍微低於平均身高,稍微高於平均體重,你不會說她又矮又胖,但不免會有這樣的念頭。她留著一頭中等長度的褐髮,瀏海垂在深邃的眼睛上。渾圓的臉頰加上突出的下巴讓她看似因努伊...
推薦序
【自序】
許多年前有一天,我在諾爾泰利耶市閒晃,突然看到了:善意。兩名建築工人在談笑,其中一人拍拍對方的肩膀。一輛車停下來讓行人穿越馬路。有人替旁人拉開門。幾個陌生人幫忙把嬰兒車扛上公車。
注意到善意之後,我到處都會不斷看到,因為善意無所不在。大家會幫彼此做各種小事,好讓生活變得容易。我們會伸出援手,提供協助,幫忙抬舉重物,移除障礙。
我們的行為和談話背後都能瞥見善意。週末愉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加油,保重。這些都是簡單的話語,也沒有法律效應,但都是發自內心好意。我希望你開心,不管你是誰。
我們需要善意,而且不用思考就會代為執行它的旨意,彷彿這麼做的原因不言自明。視線相交,互相微笑,表達感謝。善意是防範社會崩解的防線,所以偶爾思索其意義,對我們都有益處。
善意非常重要,卻也非常脆弱。如果善意消失,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自序】
許多年前有一天,我在諾爾泰利耶市閒晃,突然看到了:善意。兩名建築工人在談笑,其中一人拍拍對方的肩膀。一輛車停下來讓行人穿越馬路。有人替旁人拉開門。幾個陌生人幫忙把嬰兒車扛上公車。
注意到善意之後,我到處都會不斷看到,因為善意無所不在。大家會幫彼此做各種小事,好讓生活變得容易。我們會伸出援手,提供協助,幫忙抬舉重物,移除障礙。
我們的行為和談話背後都能瞥見善意。週末愉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加油,保重。這些都是簡單的話語,也沒有法律效應,但都是發自內心好意。我希望你開心,不管你是誰。
我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