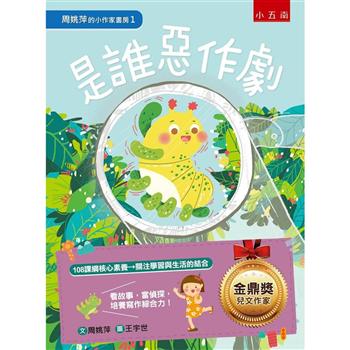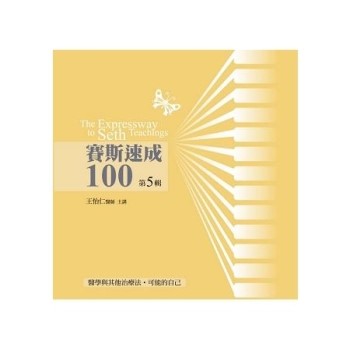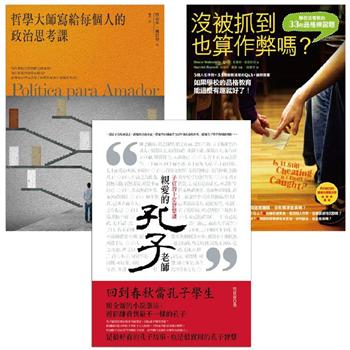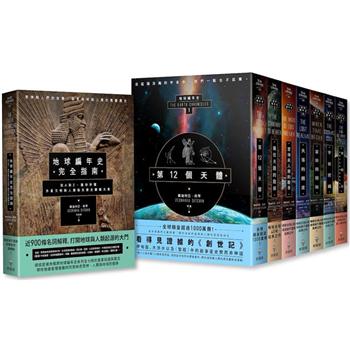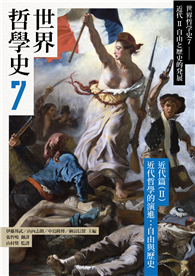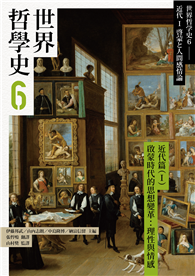聖經的解放性觀點是關顧不孕者的寶貴資源,然而,不能僅從認知層面處理不孕污名,不孕女性面對的動盪是包含身體、心理、社群、靈性的,所以需要深刻認識她的狀態。
女性從知道自己不孕到接納不孕、與不孕共處、轉化不孕經驗,會經歷不同階段,有的人歷經艱辛後得到期待的孩子,有的人沒有;也有人得到又失去,旁人不可一概而論或急於提供建議,而是需要謙卑地聆聽、同在,給予情緒抒發及想法述說的空間。關顧者若有尊重的態度、持續地祈禱(覺察上帝在每個陪伴中),就有可能觸及她人靈魂深處,進而有新的開始!
神學反思
子宮不是只有孕育胎兒才有意義,子宮絕對不能定義女性,有的女性天生無子宮等生殖器官,仍不減其女性身分。本段落以「子宮」形容不孕女性,並非為了強調子宮的重要,而是因為女性在求子過程容易對自己的身體有負面感受,所以透過賦予子宮生育以外的意義,讓女性覺察身體狀態,並接納自己的身體。努力克服不孕挑戰的子宮是勇敢的「戰鬥子宮」,雖然沒有孕育胎兒的「空子宮」會讓人感到失落,但不論有無子嗣,女性都富有生命力,擁有「創造的子宮」!
一、戰鬥的子宮
求子中的女性持續為著求子、夫妻關係、自我定義而戰鬥:為求子而戰鬥
求子者的生育動機可能來自外在環境,亦可能來自本身的內在動力,聖經創造敘事顯示人有上帝的形像,如同上帝渴望創造,人內在有上帝賜予的創造性渴望。在強調個人主義、充斥消費文化的社會,許多人選擇享樂,累積財富以過更優渥的生活,但求子者選擇一條付出的道路;又或是居高不下的房價、新興傳染病、緊張的國際情勢、全球氣候變遷等,都會讓人對未來失去希望,但求子者展現信靠上帝的盼望,願意在動盪的時代養育子嗣,因此,以生育回應創造性渴望是一個信仰行動,是為創造而奮戰。
現代女性求子會被質疑「回到傳統女性框架」,因為求子被視為回應父權制傳宗接代的要求。女性主義作家金博爾(Alexandra Kimball)描述不孕的女性主義者有雙重疏離感:一方面,不孕群體拒絕女性主義傳達不要子嗣的「生育權」;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忽視或誤解不孕女性的生活,認為求子是與父權制合作。金博爾的觀察傳達了當代不孕女性的困境:女性可否追求事業有成,又渴望成為母親?求子女性可否同時是女性主義者?金博爾指出不孕是女性主義議題,因為「不孕女性使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的謊言更清晰」,意即生育對女性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不孕女性可以驕傲地認同不孕身分,不孕身分本身就在挑戰父權制:生育不是女性生來應該做的事,也不是生來就能輕鬆做到的事。所以當女性主義提倡女性「選擇不生育」的權力,也要容納「選擇生育」的權力,不同選項都存在才是選擇,一位女性選擇生育或選擇不生育同樣值得被尊重,選擇生育也如同選擇事業需要奮鬥。
為夫妻關係而戰鬥
不論是創造敘事二人一體的愛情,或是《雅歌》挑戰父權、彼此相屬、神聖專注、無懼失敗、偉大喜悅、頌讚身體的愛情,都顯示干擾愛情的關係被排除在戀人之外,不論是與父母、公婆、手足的關係,都不當影響夫妻關係,夫妻要守護彼此的愛情!若夫妻忽略愛情,將每個月的期盼放在成功受孕與否,恐怕會使婚姻陷入希望與失望的循環,持續被抑鬱、不確定、絕望……壟罩,性生活便不再使人愉悅。
關注女性身體、性和神學的心理治療師鮑曼(Christy Angelle Bauman)認為,上帝設計「性」為人類創造生命的方式,是因為性行為本身就具創造性,不是只有在受孕、生產時才具創造性,一旦夫妻將性行為視為生育的手段,就是將雙方物化為生育工具;但當夫妻珍視「性」,在性關係互為主體、相互滿足,便是對抗物化男女的死亡力量,這就是性行為本身的創造性。
夫妻在求子過程會一再向對方揭露破碎的身體經驗──他是否接納我的卵巢老化?她是否接納我的精子活動力不足?──這是自我接納與彼此接納的過程,雖然夫妻一同面對求子的情緒會揭開傷疤,卻也會讓彼此更靠近,一起經歷重生的力量。鮑曼在流產後與丈夫進行性行為時,她感到自己的陰道記得理智無法描繪的經驗:「三週前,孩子無生命的軀體從這個通道而出,現在我的丈夫要進入同樣的地方。」於是他們先一起哀悼,才能再次在性關係裡重歷歡愉。
當夫妻要進行人工生殖療程,也必須是基於夫妻的愛情做決定,雙方都有得子的渴望,並承認上帝掌權,因為即使是試管,也不見得能按計畫懷孕。夫妻關係比懷孕更重要。
為自我定義而戰鬥
女性身體不是因為完美無缺而完整,而是因為是上帝的創造而完整!雖然不孕不影響一個人的完整性,但當女性為了生育成為「病人」接受檢查、診斷、治療,她會常常面對心中的殘缺感。她過去可能沒有仔細感受從身體而來的訊息,但因為身體經驗會塑造她對自己的看法,所以她需要不斷反芻新的經驗,帶給她在心理、社會、靈性層面的變化,對抗貼在她身上的負面標籤;她的奮鬥會讓她在不孕經驗中長出新的自我,不孕與懷孕同樣使一個女性內在、外在產生變化。澳洲女性主義生物倫理學家米爾斯(Catherine Mills)認為,生育權的重點不是關乎有無孩子,而是關乎女性根據不同的倫理和美學原則/或價值觀,自由地創造自我,當不孕者留意不孕經驗中的身體狀態及伴隨而來的感受,會與自我、與上帝有更深的連結,不孕成為具創造性的經驗,不孕者與懷孕者同樣有生產力!
二、空掉的子宮
當子宮未如預期孕育胎兒,不孕者會面對失落:
求而未得的失落
面對沒有懷孕的空子宮,不孕者會感到期望落空,有空缺感、失落感,在填滿這份空缺前,需要先面對真實存在的感受、想法。求而未得的失落包含許多意涵:無法成為母親的失落、無法聽到孩子喊「媽媽」的失落、無法傳承的失落、無法為孩子取名字的失落、無法將孩子抱在懷中的失落、無法與朋友聊媽媽經的失落、無法看見父母疼愛孫子女的失落、無法成為祖父母的失落、無法看著孩子上學的失落、無法經歷孩子叛逆的失落、無法祝福孩子獨立求職的失落、無法陪伴生命成長的失落、無法建立理想家庭的失落、無法與孩子一起經歷未來的失落……
好多好多的失落,無法一一列出。例如在與其他家庭互動時,可能又有新的觸動,像是跟朋友的孩子玩,不管玩得多開心,孩子最後還是會回去找自己的父母,這時就會浮現「沒有孩子是屬於自己」的失落……。各樣的失落讓不孕者感到悲傷、憤怒、遺憾、孤單、痛苦、不平、嫉妒……,看似小小的事情,其實一點都不小,重重地壓在不孕者心上。
身體形像的失落
「身體」是不孕的重要議題,不孕女性面對許多具體的身體經驗,例如:張開雙腿接受陌生人內診、被冰冷的醫療器械碰觸私密處、排卵針直接打在肚皮上、胚胎從身體排出……等,身體會記得那些理智想抹去的回憶,這些不舒服或悲傷的身體記憶,往往會在性行為、生理期、婦科檢查、人際互動的碰觸中再度浮現,有些人的傷痛記憶甚至會持續到老年。雖然女性身體不會因不孕而變得殘缺,但很多不孕女性都有「不完整」的感受,例如感覺自己比能生育的女性差一點,這時需要好好地為失去的身體形像哀傷,像是為失去的卵巢功能哀悼。不用害怕陷入負面狀態,也不要拒絕負面的記憶,因為那些都是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接住真實的感受才能再次感覺完整,越能尊重及聆聽負面的身體經驗,就越能感受身體愉悅、滿足的正向經驗。接納身體的失落經驗,並向上帝述說帶著傷痕的故事,便有機會重新定義不孕!身體經驗不是令人羞恥的敵人,而是使生命豐富的老師。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在生命邊緣,看見光:那些關於不孕的失落、勇氣與信仰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基督宗教 |
$ 297 |
婚姻/家庭 |
$ 297 |
心靈關懷/成長 |
$ 297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生命邊緣,看見光:那些關於不孕的失落、勇氣與信仰
每次從子宮流出血,
都讓我的眼流出水。
但我不孤單,
有流水與血的基督陪伴我。
這是一本從作者的生命經驗出發的書,同時集結五位不孕基督徒女性的故事。全書不只有理性嚴謹的神學思辨、溫柔細膩的關顧建議、女性視角的信仰儀式,更直面配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作者想要表達:在生命的苦難中,我們或許會找到啟示,但苦難始終是苦難,不必刻意美化,也無需失控的樂觀。最終我們只需銘記:人生最大的獎賞並非在於是否有子嗣,而是在於上帝的紀念與同在!
作者簡介:
潘叡儀
喜歡熱拿鐵、喜歡自我對話、喜歡圖像祈禱、喜歡孩子的笑容、喜歡耶穌,每天練習喜歡自己、練習在苦難中停留、練習不失去盼望,於是有了這本書。
經歷:
●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神學碩士
●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 現為馬偕紀念醫院院牧
章節試閱
聖經的解放性觀點是關顧不孕者的寶貴資源,然而,不能僅從認知層面處理不孕污名,不孕女性面對的動盪是包含身體、心理、社群、靈性的,所以需要深刻認識她的狀態。
女性從知道自己不孕到接納不孕、與不孕共處、轉化不孕經驗,會經歷不同階段,有的人歷經艱辛後得到期待的孩子,有的人沒有;也有人得到又失去,旁人不可一概而論或急於提供建議,而是需要謙卑地聆聽、同在,給予情緒抒發及想法述說的空間。關顧者若有尊重的態度、持續地祈禱(覺察上帝在每個陪伴中),就有可能觸及她人靈魂深處,進而有新的開始!
神學反思
子宮不是只有孕...
女性從知道自己不孕到接納不孕、與不孕共處、轉化不孕經驗,會經歷不同階段,有的人歷經艱辛後得到期待的孩子,有的人沒有;也有人得到又失去,旁人不可一概而論或急於提供建議,而是需要謙卑地聆聽、同在,給予情緒抒發及想法述說的空間。關顧者若有尊重的態度、持續地祈禱(覺察上帝在每個陪伴中),就有可能觸及她人靈魂深處,進而有新的開始!
神學反思
子宮不是只有孕...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推薦序一
從生命實況出發的溫柔書寫
得知叡儀願意將她的研究出版成書,分享給教會界的朋友,內心激動不已。從陪伴她做研究開始,看著她一路認真地探尋女性的身體、生命經驗、呼召……這些不容易的課題,到最後將她的靈性追尋與神學之旅集結成書出版,我充滿了欣喜與感恩。欣喜的是,看見她生命的旅程即便充滿了痛苦、掙扎,但最後她得到了甜美的果實;感恩的是,上帝對於信仰者的誠實叩問與認真追尋,總不會令人失望。
這是一本從作者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並集結了五位不孕基督徒女性的經驗,探詢女性與身體、女性與母職、女性與不孕汙名...
從生命實況出發的溫柔書寫
得知叡儀願意將她的研究出版成書,分享給教會界的朋友,內心激動不已。從陪伴她做研究開始,看著她一路認真地探尋女性的身體、生命經驗、呼召……這些不容易的課題,到最後將她的靈性追尋與神學之旅集結成書出版,我充滿了欣喜與感恩。欣喜的是,看見她生命的旅程即便充滿了痛苦、掙扎,但最後她得到了甜美的果實;感恩的是,上帝對於信仰者的誠實叩問與認真追尋,總不會令人失望。
這是一本從作者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並集結了五位不孕基督徒女性的經驗,探詢女性與身體、女性與母職、女性與不孕汙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一 從生命實況出發的溫柔書寫
推薦序二 在空洞中,知道我們依舊被顧念
推薦序三 指引不孕夫妻心的方向
第一章 為什麼是我?──一場旅程的開始
信仰的叩問
所謂「不孕」
我想要說的是……
第二章 她們──五位不孕基督徒女性的故事
她們的生活
她們的信仰
她們的自我
她們與關顧者的距離—經驗與建議
第三章 聖經怎麼說?──與經文對話
從何開始?
創造敘事的生育觀
無關生育──《雅歌》的愛情
生育的終末觀點
第四章 陪她一段──關顧實踐指南
神學反思
關懷不孕者可以這樣做!
第五章 前面有光──自助、助人的靈修...
推薦序二 在空洞中,知道我們依舊被顧念
推薦序三 指引不孕夫妻心的方向
第一章 為什麼是我?──一場旅程的開始
信仰的叩問
所謂「不孕」
我想要說的是……
第二章 她們──五位不孕基督徒女性的故事
她們的生活
她們的信仰
她們的自我
她們與關顧者的距離—經驗與建議
第三章 聖經怎麼說?──與經文對話
從何開始?
創造敘事的生育觀
無關生育──《雅歌》的愛情
生育的終末觀點
第四章 陪她一段──關顧實踐指南
神學反思
關懷不孕者可以這樣做!
第五章 前面有光──自助、助人的靈修...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