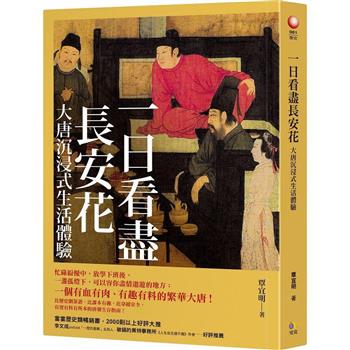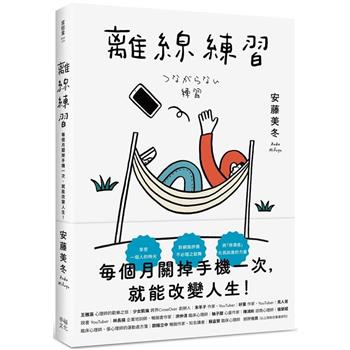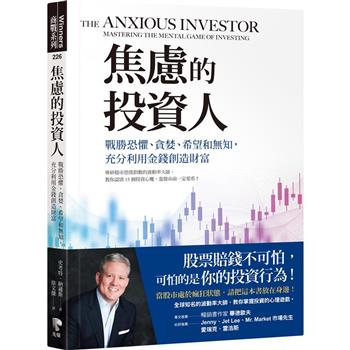導讀
寫實與虛構、犯罪與藝術之間的鑽頭世界
林浩立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在當下的饒舌世界中最受矚目的事情,莫過於亞特蘭大饒舌歌手「惡棍」(Young Thug)的訴訟官司。整個開庭過程都有實況直播,相關即時報導與評論層出不窮,完全不亞於早先好萊塢怨偶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互控誹謗的法庭實境秀。
出道於二〇一〇年的惡棍是近十年來最火紅的饒舌歌手之一,以魔性的呢喃唱腔聞名,作品在YouTube上動輒破百萬、千萬的觀看次數。然而在二〇二二年五月,他與其創立的YSL(少年呼麻人生Young Stoner Life,也有一說是少年黑幫人生Young Slime Life)唱片公司旗下藝人如「鋼納」(Gunna)與員工共二十八人因違反喬治亞州的「勒索及貪污組織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也就是RICO,又譯「反黑連坐法」)被逮捕入獄,一同以高達五十六項罪名被起訴。在幾位夥伴接受認罪協商開釋、一位在獄中遇刺、再加上陪審團的組成程序、以及惡棍自己多次交保被拒與健康出現狀況等事件的耽擱下,惡棍與剩下五位夥伴的訴訟案終於在二〇二四年一月初重新開庭審理。
主導起訴的喬治州富爾頓郡檢察官威利斯(Fani Willis,因為同時以相同罪名起訴川普而聲名大噪)認為YSL是一個犯罪組織,參與了包括謀殺、槍擊、竊盜、販毒在內的許多密謀犯罪活動,而其中一個最為顯著的證據就是——歌詞。這場官司會引起饒舌世界密切關注的原因,就是因為檢方提出十七首惡棍作品的歌詞作為呈堂證據,並得到了法官的同意。例如在〈黑幫勾當〉(Slime Shit)中的副歌:「嘿,這就是黑幫勾當,嘿/YSL勾當,嘿/殺死條子的勾當,嘿/去他的監獄,嘿」,就幾度在法庭上被法官與律師字正腔圓地唸出。另一方面,辯方律師除了強調惡棍是以音樂創作反映並翻轉窮苦的出身、以及YSL只是一製作音樂的團隊外,也同樣以歌詞、意象、手勢等符碼來為之辯護,例如在開案陳述中指出「惡棍」(Thug)一詞是「在上帝之下誠心謙卑」(Truly Humble Under God)的縮寫,並將著有《當饒舌遭受審判》(Rap on Trial: Race, Lyrics, and Guilt in America)一書的作者之一尼爾森(Erik Nielson)教授列為專家證人。
漫長的法庭攻防因為饒舌音樂與歌詞的加入而充滿反差的荒謬感,並且在一月二十九日這天來到戲劇性的高峰。檢方傳喚了之前接受認罪協商的YSL共同創辦人「提克」(Tick)接受交叉質詢,並以惡棍的歌〈醍醐灌頂〉(Droppin Jewels)中的歌詞一句句詢問是否反映他「在上帝之下誠心謙卑」。辯方律師則希望在法庭播放這首歌的現場演出版本,其意圖是要呈現這是一個徹底的藝術表演創作,且涉及惡棍私密的心靈世界,不能只憑歌詞脫離脈絡檢視。這個請求遭到檢方的反對,堅持只能播放錄音版本,法官最後也同意,儘管辯方律師慷慨激昂的抗議。如此針對一首音樂與歌詞的辯詰就花了半天的時間,可以想見這場訴訟官司會是如何曠日持久。
在法庭之外,幾個相關的法律行動也在進行中。稍早於二〇二一年,紐約州參議員賀伊曼(Brad Hoylman)已提出防止創意表現成為刑事證據的法案,並在州參議院通過;隔年在惡棍被捕後,於全國層級上來自喬治亞州的眾議員強森(Hank Johnson)在眾議院提出了「恢復藝術保護法案」(Restoring Artistic Protection Act,簡稱RAP Act);在此同時,YSL的發行公司三〇〇娛樂事業(300 Entertainment)執行長和大西洋唱片公司(Atlantic Records)營運長則是在推動「保護黑人藝術」的請願連署;隔海在英國,「藝術而非證據」(Art not Evidence)運動也有同樣的倡議。在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到清楚的種族政治論述,也就是許多歌曲都有犯罪行為的第一人稱描繪,如強尼‧凱許(Johnny Cash)〈佛森監獄藍調〉(Folsom Prison Blues)的經典一句「我在雷諾向一個人開槍,眼睜睜看他死去」,為何獨獨黑人饒舌歌手的歌詞會被當成犯罪證據。在學術界也有這個議題相應的討論,例如上面提到的《當饒舌遭受審判》專書。流行音樂研究的重要期刊《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則是在二〇二二年出版了以「起訴與監控饒舌」(Prosecuting and Policing Rap)為題的專號。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昆因(Eithne Quinn)教授早在二〇一五年已在進行相關研究,並在近幾年領導「起訴饒舌:刑事正義與英國黑人青年表現文化」(Prosecuting Rap: Criminal Justice and UK Black Youth Expressive Culture)的計畫。
這些都是瞭解社會學家史都華《子彈歌謠》的重要脈絡。
在進入這本關於芝加哥幫派黑人青年的都市民族誌之前,應該要先介紹什麼是鑽頭音樂(Drill)?在聲響上有什麼特色需要從饒舌類型中區分出來?跟惡棍正面臨的官司又有什麼關連?事實上,史都華在書中第二章裡就有一個小節專門在介紹鑽頭的音樂屬性,也明確指出其「陷阱」(Trap)饒舌的淵源。「陷阱」饒舌大約出現於二〇〇〇年代初,主要由美國南方特別是亞特蘭大的饒舌歌手創作出來。「陷阱」一詞是亞特蘭大的俚語,指的是販賣毒品的毒窟。可想而知,其內容多在敘述南方城市的街頭犯罪景況。到了二〇一〇年代,陷阱饒舌已高度商業化並出產了包括惡棍在內的饒舌巨星,同時也誕生了不同的次風格。在芝加哥,它與原本就十分猖獗的幫派結合形成了「鑽頭」饒舌。「鑽頭」一詞是芝加哥的俚語,意指槍擊、謀殺,因此相較於已在音樂產業中普及的陷阱饒舌,鑽頭饒舌的幫派意味更加濃厚,內容與節奏更為陰暗(或如同書中鑽頭音樂製作專家所說的,「無時無刻的小調」、「帶有軍隊聲響的小鼓」),多在展示幫派成員身分、地盤、犯罪活動以及幫派之間的爭鬥,被認為是有「芝拉克」(Chiraq)惡名的芝加哥之治安問題的元兇。在英國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Brixton),一種稱為「英式鑽頭」(UK Drill)的次風格大約從二〇一二年隨之現身。而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紐澤西,在地的鑽頭類型也一一出現,豐富了鑽頭世界的多樣性,但不變的是與幫派與犯罪的緊密關連。
史都華是長期關注都市犯罪、貧窮與治理的社會學家,上一本專書《全面逮捕》(2016)(Down, Out, and Under Arrest: Policing and Everyday Life in Skid Row)處理的是在洛杉磯的一個邊緣社區中警察無止境的巡邏偵察。他問道,為什麼社區成員已被社會支持系統放棄,卻還是有大量資源投入其監控管制。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花了五年的時間在社區中進行田野工作,不只與居民密切相處,也與警察往來互動。由此可以看到他做研究的全貌關懷,也就是對多方行動者觀點與事件的留意。在《子彈歌謠》中,他來到了惡名昭彰的芝加哥南區擔任青少年課後計畫的輔導老師,並進而接觸到匿名為「街角兄弟」(Corner Boys)的鑽頭歌手與幫派青年,與他們廝混,慢慢進入他們的社會生活與心靈世界中。但如同史都華所引用的知名社會學家貝克(Howard Becker)的「藝術世界」框架,這個「鑽頭世界」的構成不是只有鑽頭歌手而已,還包括他們的隊友如像是保鏢的「槍手」、處理各種其他分工的「那些傢伙」、幫忙拍攝音樂影片的「導仔」、協助錄音的「鄰里工程師」。有時候,這個網絡還會溢流出他們的街坊地盤,搭上地方教會組織、各地愛慕他們的女性粉絲、西岸的富裕白人子弟、甚至遠在德國的節奏製作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這些在追蹤點閱他們社群媒體訊息的消費者。也就是說,只將治安問題怪罪於鑽頭歌手,低估了鑽頭世界去中心的複雜性,也忽視了鑽頭音樂作為一種追求網絡聲量的創意展演形式。事實上,《子彈歌謠》指出根據美國犯罪統計資料,會發現涉及幫派的年輕人增加使用社群媒體的同一段時間當中,暴力事件下降至歷史新低。正是如此,許多評論者認為將惡棍與其YSL夥伴形容為亞特蘭大史上最大犯罪集團的「勒索及貪污組織犯罪法」官司根本是一場鬧劇。
在二〇二四年剛出版的《幫派與社會牛津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Gangs and Society)中,史都華與摩爾(Caylin Louis Moore)合寫了〈什麼是幫派文化?〉這一章,裡面提到三種理解幫派文化的取徑:一、幫派文化作為引導行為的價值體系;二、幫派文化作為解決日常問題的工具箱;三、幫派文化作為社會行動者創造的物質與象徵產品。史都華將自己的《子彈歌謠》定位於第三種取徑中,關注作為幫派文化商品的鑽頭音樂如何能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甚至翻轉歌手的人生、使之脫離幫派環境。例如以二〇一二年一首在家中自製的〈恁爸無佮意〉(I Don’t Like)使鑽頭類型響徹雲霄的「酋長基夫」(Chief Keef),不但被唱片公司相中與之簽約,也搬出了芝加哥的鄰里。酋長基夫於是成為了《子彈歌謠》書中鑽頭歌手仿效的對象,不只是為了經濟利益,更是為了尊嚴與認可。
但史都華並沒有天真地只將鑽頭歌手當作藝術創作者。他們畢竟仍是幫派份子、真的有參與犯罪活動、有的甚至還犯過一級謀殺的重罪,只不過這些身分與行動往往和歌詞內容與社群媒體形象並非一致。他們在鑽頭世界中想要「做出的自己」(Keep It Real)是介於寫實與虛構、犯罪與藝術之間,並透過網絡流通,渲染成為商品與意象。這能賺取利益、但也會帶來真切的後果。這就是史都華所謂科技使用的「數位弱勢」,也就是「如何運用科技以及科技所帶來的後果在質量方面的差距」。某種程度而言,鑽頭歌手在做的事情與一些曾在社群媒體上展現叛逆暴力形象的中產青少年沒有不同,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能輕易告別這個「階段」然後邁向人生的下一個目標。鑽頭歌手則是很難擺脫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污名」,而弔詭的是這個「污名」是他們能改變人生的唯一手段。他們會因為在網絡上釋出的內容而被仇家找上門、會常常落入被剝削利用的境地、而就算真的闖出名堂也會像惡棍一樣成為刑事訴訟的目標。
史都華最後在結論處講到,「這些數位內容生產活動說穿了其實是對於美國財富、權力與社會地位嚴重分配不均的反應,是對於種族與階級壓迫的回應。」這是結構對上實踐的經典社會學命題,而《子彈歌謠》提醒我們的是在鑽頭世界中有著多重的關係、身分與行動者,不只是讚頌暴力犯罪的鑽頭歌手那麼簡單。這能帶來多重的實踐契機,也有行動介入的可能,例如認真看待鑽頭音樂反映社區現況的敘事能量,接受社群媒體建立社區青少年關係的重要性,由此提供適當的引導、干預與補助。有人或許會說這是史都華身為行動社會學家一廂情願的期許,無法真的撼動不平等的結構,但至少鑽頭音樂確實讓這些邊緣族群的聲音被世界聆聽到了(甚至引來社會學家進行民族誌調查,英式鑽頭的案例可見社會學家懷特Joy White於二〇二〇年出版的《貧民窟地球化》Terraformed: Young Black Lives in the Inner City)。畢竟這是一首「子彈歌謠」,而非「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