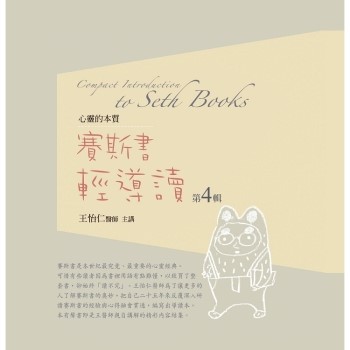本書包含八篇中篇小説和一個尾聲,反映大時代中普通人群悲歡離合的故事。在時代巨浪的衝擊、裹挾和推動下,渺小的個人往往深感命運之難以掌控,在人們這種困惑和無奈中,折射出人性的複雜和變異。然而,面對人生的無常,沒有人能逃避、躲藏,總須作出各自的抉擇。待一生終結時,究竟是無怨無悔,還是心存不少遺憾和愧疚;或者,前思後想徬徨迷茫,身陷其中依然找不到答案……
本書特色
▌作者的筆下人物猶如歷史般的巨浪拍打下,灑落岸上的破碎浪花,寫著見證歷史般的真實,刻劃著戰亂年代中人們的苦難與遺憾。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聚散(上冊):中篇系列小說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聚散(上冊):中篇系列小說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Songbird
1935年出生於上海。曾在北京、香港和溫哥華等地教授鋼琴及聲樂,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1997年移民加拿大,曾於西蒙菲沙大學兼職教中文,並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BC)音樂教師協會會員、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員。2010年出版了中文散文集《歲月遺踪》,2017年出版英語譯本The Unceasing Storm: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2019年出版了散文集《原來如此》。2023年完成中篇系列小說《聚散》的上冊,下冊將於2024年完稿。
Songbird
1935年出生於上海。曾在北京、香港和溫哥華等地教授鋼琴及聲樂,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1997年移民加拿大,曾於西蒙菲沙大學兼職教中文,並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BC)音樂教師協會會員、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員。2010年出版了中文散文集《歲月遺踪》,2017年出版英語譯本The Unceasing Storm: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2019年出版了散文集《原來如此》。2023年完成中篇系列小說《聚散》的上冊,下冊將於2024年完稿。
序
序言
《聚散》系列包含八篇中篇小說和尾聲:
1. 分道揚鑣
2. 夢斷京城
3. 似夢是真
4. 不期而遇
5. 荒誕噩夢
6. 錯失良緣
7. 劫後餘生
8. 返璞歸真
尾聲
今天我終於完成了中篇系列小說《聚散》的上冊,人說十年磨一劍,我則是十年寫一書。
2012年以前從未寫過小說的我,腦子裡忽然呈現出四個少女的故事,忍不住想寫一本長篇小說《命運四重奏》。強烈的慾望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著手寫了起來。然而,辛辛苦苦寫了十三章,卻遇上了瓶頸。我想,可能題材太大,不易掌控,放棄嗎?不。左思右想,有了一個主意:不如將素材結集成一本中篇系列小說,每篇約三、四萬字,那就比較容易掌控;而讀者則無需花很多時間每篇都看,可以選擇自己想看的篇章。此外我還可以選幾篇做成有聲讀物,以方便忙碌的讀者聽書,豈不更好?於是我將書名改為《聚散》,圍繞這個主題,創作了八篇中篇小說和一個尾聲,把幾十年來發生在我周圍的故事寫了出來。
這些中篇小說既是相對獨立,同時又有著內在聯繫。因此,我會在某處的括弧裡標明此段與另外一篇小說某一段的內容有關,如果讀者願意瞭解多一點,可以查看。這是參考了詞典的編纂方式。嘗試用這樣的辦法來寫小說,不知是否可行? 會不會有一點別開生面的感覺?
稱之為系列,是因為這八篇小說,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個獨立的故事,然而連續讀來,則會展現出一幅跨世紀的畫卷。涉及的地域有上海、北京、重慶、西安、長春、北大荒、朝鮮、韓國、貴陽、香港、美國、加拿大、溫哥華等國家和地區。
歷史的長河平時看似風平浪靜,但當時代的巨浪奔騰而來,芸芸眾生霎時間像砂礫般被席捲而起,不知拋向何方。無數家庭被沖散,多少親人天各一方;卻又有人意外地陌路相逢,結伴同行,譜寫出一曲曲奇異的命運重奏。在不可預測的人生旅途中,有人迷茫、沉淪或者隨波逐流,有人則清醒、執著地守護信念,逆風而行。面對衝擊,如何抵禦壓力,如何撥開迷霧,如何衝出峽谷,如何堅持真實的自我,則因人而異。古往今來聚聚散散,喜憂交加,確有說不完的悲歡離合,道不盡的酸甜苦辣。一齣齣撼動心靈的戲劇,在人生的舞台上連續不斷地上演,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書中眾多人物中有一位貫穿八篇的主要人物,其他則分別出現在不同的小說裡,敘述著各自的故事。
《聚散》系列包含八篇中篇小說和尾聲:
1. 分道揚鑣
2. 夢斷京城
3. 似夢是真
4. 不期而遇
5. 荒誕噩夢
6. 錯失良緣
7. 劫後餘生
8. 返璞歸真
尾聲
今天我終於完成了中篇系列小說《聚散》的上冊,人說十年磨一劍,我則是十年寫一書。
2012年以前從未寫過小說的我,腦子裡忽然呈現出四個少女的故事,忍不住想寫一本長篇小說《命運四重奏》。強烈的慾望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著手寫了起來。然而,辛辛苦苦寫了十三章,卻遇上了瓶頸。我想,可能題材太大,不易掌控,放棄嗎?不。左思右想,有了一個主意:不如將素材結集成一本中篇系列小說,每篇約三、四萬字,那就比較容易掌控;而讀者則無需花很多時間每篇都看,可以選擇自己想看的篇章。此外我還可以選幾篇做成有聲讀物,以方便忙碌的讀者聽書,豈不更好?於是我將書名改為《聚散》,圍繞這個主題,創作了八篇中篇小說和一個尾聲,把幾十年來發生在我周圍的故事寫了出來。
這些中篇小說既是相對獨立,同時又有著內在聯繫。因此,我會在某處的括弧裡標明此段與另外一篇小說某一段的內容有關,如果讀者願意瞭解多一點,可以查看。這是參考了詞典的編纂方式。嘗試用這樣的辦法來寫小說,不知是否可行? 會不會有一點別開生面的感覺?
稱之為系列,是因為這八篇小說,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個獨立的故事,然而連續讀來,則會展現出一幅跨世紀的畫卷。涉及的地域有上海、北京、重慶、西安、長春、北大荒、朝鮮、韓國、貴陽、香港、美國、加拿大、溫哥華等國家和地區。
歷史的長河平時看似風平浪靜,但當時代的巨浪奔騰而來,芸芸眾生霎時間像砂礫般被席捲而起,不知拋向何方。無數家庭被沖散,多少親人天各一方;卻又有人意外地陌路相逢,結伴同行,譜寫出一曲曲奇異的命運重奏。在不可預測的人生旅途中,有人迷茫、沉淪或者隨波逐流,有人則清醒、執著地守護信念,逆風而行。面對衝擊,如何抵禦壓力,如何撥開迷霧,如何衝出峽谷,如何堅持真實的自我,則因人而異。古往今來聚聚散散,喜憂交加,確有說不完的悲歡離合,道不盡的酸甜苦辣。一齣齣撼動心靈的戲劇,在人生的舞台上連續不斷地上演,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書中眾多人物中有一位貫穿八篇的主要人物,其他則分別出現在不同的小說裡,敘述著各自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