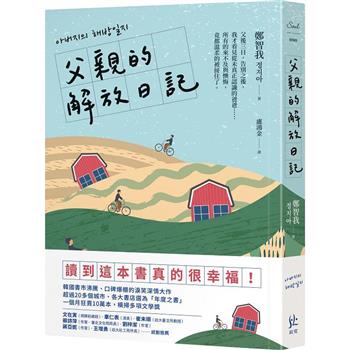自序
愛是什麼?說一個人愛另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當無辜的古代先知被上帝吩咐要去愛一個淫婦的時候,上帝究竟是要他幹什麼?父母、孩子、手足、情人、或者滿懷憐憫之心的好好先生好好女士、傳教士們⋯⋯等等,當這些自認為愛者的每一個人向著他的所愛者告白,或者自己在心裡說「我愛你」的時候,究竟意味著什麼?愛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種「意味」有何意義?以及,有可能嗎?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在《思想錄》(Pensées)中探索「自我」的含義時,留下了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假如人們因我的判斷、因我的記憶而愛我,他們是在愛我嗎?不是的,因為我可以喪失這些品質而不必喪失我自己本身。然則,這個我又在哪裡呢?假如他既不在身體之中,也不在靈魂之中的話。並且,若不是由於有根本不構成其為我的這些品質(因為它們是可以消滅的),又怎麼會愛身體或愛靈魂呢?因為難道我們會抽象地愛一個人的靈魂的實質,而不管它裡面是什麼品質嗎?這是不可能的,也會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們從來不是在愛人,而僅只是在愛某些品質罷了。因而,讓我們不要再嘲笑那些由於地位和職務而受人尊敬的人們吧,因為我們所愛於別人的就只不過是那些假借的品質而已。
伴隨著柏拉圖的影子,這段話的暗示—任何對「個人」的愛都不可能是真實的—說來未免太傷感情,雖然帕斯卡的用意似乎是鼓勵人們寬容一點。無論如何,帕斯卡的沉思精準(卻十足討人厭)地把握到了愛的這種疑難:由於自我是個極奇怪而難以界定的東西,因此說去愛一個自我或去愛另一個自我,就算到底沒有說謊,終究還是難以理解的。
在原本的碩士論文(《愛與被愛:以馬希翁《情愛現象學》為本的考察》,以下簡稱原碩論)中,我從兩條經典的岔路—我粗略地把它們稱為自然主義與律法主義(道德主義)的進路—出發構想這一問題,很快地來到了它們的盡頭。要克服帕斯卡提出的難題,需要從另一種出發點、另一種觀看的視角—或更準確地說,另一種「方法」—來對愛進行另外的考察。為了本真地去愛,或更保守地說,本真地意願愛,必須確保我們或至少豁免於上述難題。在這個背景下,我採用馬希翁(Jean-Luc Marion, 1946-)的《情愛現象學》(Le phénomène érotique)一書,與其說是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不如說從中借取思考和言說情愛現象的諸種「術語」。此是我認識並深入研究馬希翁思想的契機。
當初,作為私人切身的思想之旅,我把自己的論文界定為對《情愛現象學》一書的「閱讀與思考的心得筆記」,以相當個性化的思路和表達方式寫完這本論文,雖然在馬希翁研究還稍嫌薄弱的台灣或許多少帶來一些突破或啟發,但由於缺少了對馬希翁思想的系統性介紹,整本論文的視野難免有些窄小,這是不可否認的。從曾慶豹老師提議出版以及我接受了這一邀請的那天起,注定了我要償還偷懶的債,就是我認為原碩論在學術意義下所缺乏的東西,我有責任予以補上。因此,為原碩論進行增補的工作,便聚焦於將《情愛現象學》勾連到馬希翁學術生涯的幾個核心主題,甚至整個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脈絡,以便讓《情愛現象學》在更清楚明白的背景下得到認識。
為此,我以一篇四十餘頁的「導論」取代了原碩論的「前言」(其中仍有一些有價值的說明),對馬希翁的思想進行更全面的介紹。除此之外,我最後還新增了兩篇附錄,第一篇〈再見?以馬忤斯路上〉探討馬希翁對基督神學的定位以及相關的啟發,要獻給曾在新加坡神學院一起生活一起求學的朋友們,回報那些無以回報的款待;第二篇〈寄望於再見的愛〉則探討馬希翁在《情愛現象學》中對上帝的提及,是為Michelle寫的,為紀念獨一無二難得的友誼,並盼望下一次的再見—I bid you adieu, beloved friend, I bid you à Dieu!
本書有幸出版,是蒙受了曾慶豹老師的賞識,自論文口試上「鄉認」以來,就受到他很多照顧,尤其對於一個信仰的異鄉人來說,與他的相識更是一份沉重的禮物,常常不知如何向他道的謝,就在這裡表示吧;而作為現象學的引路人以及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游淙祺老師於這本書的完成可謂功不可沒,在此也特別感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