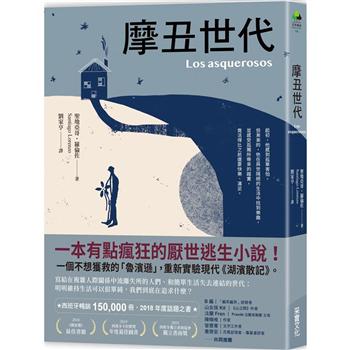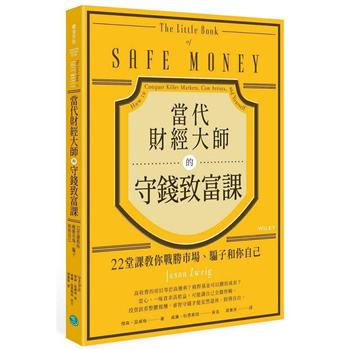蔣彥永:對醫生來說,講真話是最基本的要求
蔣彥永,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其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1990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兩人有過會面。
少年時期,蔣彥永因目睹姨媽患肺結核病逝,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余英時於同年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作為教會大學的燕京大學被解散,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代的青年普遍左傾,即便是燕京大學等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或協和醫學院這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大學,其提供的教育雖然包含美國文化,卻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觀念秩序,無法向學生提供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資源,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大都被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吸引和蠱惑。不過,燕京大學雖被拆解,其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對作為最後一批學生的蔣彥永產生深刻影響。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醫生涯中一直踐行這九個字—他後來教導學生說:「作為醫生,從自己學會看病,到能看一些複雜的病,能解決一些疑難的病,學校書本的教育固然重要,但主要還是靠從處理一個一個病人的經驗中逐漸積累起來。也就是說醫生一點一滴的進步,都是病人給的。因此,應該把從病人身上學到的本領,更好地用於為病人服務。」
1957年,蔣彥永畢業後被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三○一醫院)擔任外科醫生。這家知名醫院負責黨政軍高官的醫療保健工作,並診治全國各地疑難雜症。蔣彥永身材高大瘦削,以精確、穩健的雙手和願意接手疑難雜症聞名,贏得「蔣大膽」的綽號。1965年,成昆鐵路工程上馬,他參加了三○一成昆鐵路醫療隊,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開顱手術都做。
文革爆發後,蔣彥永因此前揭露解放軍總後勤部主任邱會作(三○一醫院直接主管)搞特權,被扣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壞頭頭」四頂帽子,遭到批鬥、毆打並監禁兩年。1967年12月,他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軍馬場在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大山裡,交通不便,資訊閉塞。他被迫幹重體力活,成袋的高粱不封口,扛著登板入庫。沒過幾天,馬場職工醫院院長得了闌尾炎,請蔣醫生主刀手術,順利康復。從此,他成為軍馬場的大夫。
1971年,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作為林彪在軍中的「四大金剛」之一的邱會作隨即被捕,蔣彥永於10月獲得平反。次年,他重返解放軍總醫院。文革結束後,他先後擔任黎介壽為組長的普通外科專業組第一副組長、吳孟超為組長的軍內腫瘤專業組第一副組長。1980年,開始指導碩士研究生,先後有九位畢業。1990年代,獲得博士授予權,先後帶出五位博士生。
1985年,蔣彥永以精湛的醫術,升任三○一醫院外科部主任、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他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以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的作風贏得「清廉醫生」之美譽。他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四十多篇論文,出版過《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2003年春,中國爆發SARS(亦稱非典、薩斯)疫情。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記者會上稱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認為衛生部長公然說謊,根據他了解的幾所軍醫院的情況,疫情並沒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數還在迅速增加。他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4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病毒,並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次日晚上,他將三所軍醫院收治SARS染病者的情況寫下來,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郵,該電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但這一信息被海外媒體獲知。4月8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週刊記者採訪蔣彥永。記者建議,為了安全緣故,蔣彥永最好不要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記者又問:「那樣做的後果,你考慮了沒有?」他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隨即,西方若干主流媒體都報導了蔣彥永揭露的SARS真相。
4月9日下午,蔣彥永給學生上課尚未結束,醫院領導來找他談話,警告他「作為一個軍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是違背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蔣彥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會找院方談。同時,他強調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4月11日,蔣彥永主動找到院領導,提出三點控制疫情的建議:一、鑑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面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因此,應儘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SARS病人。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與他一起核對SARS病例的數字。
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承認疫情統計「存在較大疏漏」,確認北京共確診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善於處理危機的王岐山被調任為北京市市長。這一切顯示新上任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似乎有意實施某種「新政」—事後證明這是民間一廂情願的幻想。
蔣彥永挺身而出,挽救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讓SARS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現重大轉折。他將真相公之於眾的舉動拯救了大量民眾的生命,許多人把他稱之為「英雄」或「吹哨人」。同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拉蒙.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其獲獎的理由是:「勇於揭露SARS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中共當局不允許他前往領獎。他告訴外媒:「因為我在部隊工作,雖然退休了,可還是在部隊。部隊領導跟我談,說軍隊對國外這類授獎應該都不允許去參加,我就只能按照軍隊的規定做。」
蔣彥永的女兒蔣瑞代父親出席頒獎典禮,領獎並發表感言說,「我更希望父親能夠親自前來接受這份榮耀」。說到這裡,蔣瑞心生感觸而哽咽落淚。她說,麥格塞塞獎不僅表揚了父親對人類的貢獻,也鼓勵民眾堅定地站在真理的一方。「父親要我傳達的訊息是,希望大家在遭遇問題或困難的時候,要勇於說真話、敢於說出真相」。
後來,蔣彥永謙虛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個醫生和公民理所應當做的事情:「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有的人,一生只說一次真話就夠了,從此在成績單上躺平,但蔣彥永不滿足於此。
早在1990年代初,蔣彥永就給當局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件(他使用的是「正名」,而非「平反」,這一差異非常重要)。1998年,他又與諸多老共產黨員一起聯署了一封同一主題的信件,但都未得到當局回應。2004年2月24日,他通過中共開明派元老李銳向最高當局轉達了一封要求為天安門事件正名的信件。當局仍置若罔聞。於是,他將此信公之於眾。當時,蔣彥永不再只是一位醫學圈內的專家,他因揭露SARS真相而名滿天下,這封信遂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蔣彥永勇敢地以一己之力推動六四正名。這封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信件,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建議,要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信中,他講述了1989年6月3日晚趕到醫院急診室的見聞:「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傷者中,有一個中彈的、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蔣彥永親自參與搶救卻未能搶救過來:「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盡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
蔣彥永揭露了軍隊使用達姆彈(開花彈)射殺人民的真相:「我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蔣彥永在信中寫道:「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十七歲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他們的願望—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蔣彥永當然知道這封信有可能招致中共當局的打壓。「當然我也考慮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確實,這封信件成為是否存在「胡溫新政」的最好檢測。六四問題始終是中共當局「嚴防死守」的「底線」。胡溫執政初期時,因根基不穩,及試圖在國際上營造開明形象,在SARS危機中表現出一定的開明度,但胡溫絕對不會在六四問題上鬆口,因為胡溫政權的極權主義底色並無絲毫改變。
2004年6月1月,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在從住所前往三○一醫院途中被祕密警察帶走,華仲尉在被軟禁兩週後獲釋,蔣彥永直到7月19日才被釋放,據說是被強制「上學習班」。此後,他一直被軍方和祕密警察嚴密監視,處於半軟禁狀態。次年3月22日,他重獲行動自由,但仍受諸多非法限制。2005年7月,他準備與妻子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許。他曾提出解除與三○一醫院的所有關係、退出軍隊,亦未獲准許。
在此期間,蔣彥永與丁子霖夫婦等天安門母親成員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他與他們結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劍、風沙撲面的北京,他們相濡以沫、並肩前行。他並利用醫生的身份和人脈,幫這些被打壓的友人聯繫醫院和醫生,檢查身體、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有一次,蔣彥永約我到他家做客,將他珍藏的很多照片給我看,並挑選一部分照片和手稿交給我保管。他擔心當局前來抄家,這些珍貴照片會被抄走。當我們正在聊天時,忽然電話響起來。蔣醫生接了電話後,表情嚴峻地告訴我,醫院領導說馬上來拜訪他,「或許是特務竊聽了我們的通話,要上門來圍堵你」。他又說,當局一定派執勤的武警到樓下看守,「如果你此時出去,很可能會被抓走審訊」。聽他如此說,我也變得緊張起來。但蔣醫生很鎮定,他稍一思索,就告訴我,「有一個辦法可以脫身,你不要慌」。他迅速帶我出門,敲開鄰居的家門,將此時的情形簡要告知鄰居,請求鄰居讓我前去躲避。鄰居同意讓我到他們家暫時躲避,再安排帶我離開家屬院。我在其鄰居家停留兩三個小時後,鄰居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一起出門,讓我混在其中,特別安排我懷抱著一名一兩歲的嬰孩。這樣,一行人出了院子,我安全地乘坐公交車回了家。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歷,讓我意識到,蔣醫生每天都過著這種不自由的生活。
2015年3月,蔣彥永突破封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採訪,揭露解放軍在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的「冰山一角」。他披露,由總後勤部掌控的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公安、檢察院、法院,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2018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紀念日,蔣彥永以快遞方式寄信給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正名。習的反應比胡溫更殘暴:立即升級對蔣彥永的監控,將其家中的電話切斷,連他的兒子也有一個月時間不能前往探訪。蔣彥永的妻子華仲尉以及幾位密友,都向外媒證實了蔣彥永遭軟禁的事實。有一次,蔣彥永出門看病,遭到軍警攔阻、粗暴推搡,老人「斥責解放軍違反憲法」。經過交涉,蔣彥永才住進其服務一生的三○一醫院的病房。獨立媒體人高瑜表示,據蔣彥永的妻子透露,蔣彥永在醫院被嚴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視。「蔣醫生受到刺激,心情不好,患上了阿茲海默症。」
2020年,一場規模和危害遠超當年SARS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在中國和全球蔓延。中國民眾擔憂當局是否再次隱瞞疫情,網路上熱傳一篇當年《南方人物週刊》專訪蔣彥永的文章—當時,當局允許《南方人物週刊》採訪蔣彥永,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蔣彥永並未受到迫害的信號。雖是官媒卻有一定市場化色彩、屬於「南方報系」的《南方人物週刊》,後來經過多次整肅,再也不能發表類似文章。這篇文章在發表前遭到新聞檢查官刪改,但大致可展現蔣彥永的面貌和風骨。這篇專訪讓很多民眾追問:「李文亮已死,蔣彥永何在?」人們以此懷念蔣彥永,該文卻頻頻遭網管以「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為由刪除。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裡,蔣彥永一直遭受非法軟禁,無法對外發聲,偶有幾張與作家章詒和、律師浦志強等友人餐敘的照片傳出。他還一度染上病毒送入醫院搶救。獨立公民記者趙蘭健在推特上發文指出,蔣彥永醫生是唯一能凝結SARS、六四和武漢肺炎病毒三個重要歷史事件的「全中華民族驕傲史詩符號」。
學者余世存評論說:蔣彥永先生一生救死扶傷,專心於人身的病理療治,與社會政治進程少有關聯。但在晚年,他卻破門而出,為這個全面淪陷的民族發出了救贖式的吶喊。他的聲音是一個充滿罪與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聲音,是一個喑啞的被綁票的民族悲憤而高貴的人心證明。他的聲音並非高深雄奇,他的聲音也非真理、大師、學問、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樸素的真實,他的聲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開。蔣彥永先生還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對手,他度過了個人面對極權政治、專制生活無力卑微而又屈辱的歲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時代的縫隙和技術文明帶來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為與罪惡的國家政權對抗的孤獨而有力的精神個體。他開掘了這個民族荒蕪已久的道義資源。在他孤身挑戰帝國的顏面和真相時,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後有著蒙塵廣眾的人心,以及人類主流文明。
2023年3月12日,蔣彥永因病在北京去世。蔣彥永去世後,家屬接到當局通知,對其身後事提出三不准:「不准公開遺體告別儀式;不准接受公眾哀悼送花籃;不准接受媒體採訪。遺體告別室在解放軍總醫院西院的第一告別室內,如果有人要送花圈輓聯,14日前交給蔣醫生的夫人華仲尉,再交給醫院審查,悼詞已經寫好了。」3月15日上午10時,蔣醫生的遺孀華仲尉和兒子蔣慶等幾名直系親屬代表家人出席遺體告別式。學者郭于華在微信群中寫道:「蔣大夫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置人性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於首要,早已超越了政治、黨派、意識形態。不許悼念他是愚蠢至極之舉,等於公開宣稱自己是人性人道的敵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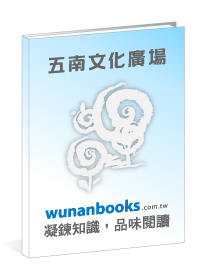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 作者: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6-2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12頁 / 15 x 21 x 2.5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25 |
社會人文 |
$ 450 |
中文書 |
$ 450 |
人物群像 |
$ 450 |
中國觀察 |
$ 450 |
歷史 |
$ 45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
本書《美好的仗,已經打過》為《民主英烈傳》之第一卷,收入2000 年之後辭世的50 名民主英烈,以不同的世代排序,時間跨度長達90 年。
本書所選之人物,生前皆以不同形式挺身反抗中共極權暴政,幾乎都受到過中共政權不同形式之迫害。其中,曾被流放、拘押和判刑者占一半以上,有多位人物慘死在監獄中或被釋放後不久就因健康被嚴酷的牢獄之災摧毀而病逝。他們的生命歷程即是對中共極權體制之強烈控訴和批判。
本書所寫之人物,其生活區域涵蓋中國本土、香港、台灣及海外,亦包括圖博人、維吾爾人、滿人等少數族裔。作者深切期盼,本書成為一座看不見的橋梁,將中國和海外的抗爭者及抗爭運動連接起來,促進不同環境下的抗爭者增加了解、交流、信任及彼此支持,並延續離世的抗爭者生前所積累的精神資源。
作者簡介:
余杰
作家、政治評論家、歷史學者。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只做這一件自己擅長做的事情。著作多達八十餘種,一千五百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等獎項。
程波
異議作家、人權捍衛者。
參與或記載了近年來中國的諸多維權事件,特別關注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有數十萬字的評論文章散見於網路。
章節試閱
蔣彥永:對醫生來說,講真話是最基本的要求
蔣彥永,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其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1990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兩人有過會面。
少年時期,蔣彥永因目睹姨媽患肺結核病逝,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余英時於同年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作為教會大學的燕京大學被解散,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
蔣彥永,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其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1990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兩人有過會面。
少年時期,蔣彥永因目睹姨媽患肺結核病逝,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余英時於同年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作為教會大學的燕京大學被解散,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吾輩愛自由,願奴隸根除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自序
俄羅斯民主人權活動家、普丁及其獨裁政權的批評者納瓦尼在獄中被害身亡後,俄羅斯資深媒體人塔伊西婭.別克布拉托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納瓦尼的死是一場政治暗殺,這一點我們都清楚。專制政權幾乎奪走了俄羅斯人的一切:奪走了繁榮的未來,奪走了每個人應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的信念。它剝奪了我們抗議和反抗的權利,奪走了我們的投票權。納瓦尼被殺,表明專制政權試圖奪走俄羅斯社會最後一絲希望。
納瓦尼是自由俄羅斯的活生生象徵,表明一個繁榮、和...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自序
俄羅斯民主人權活動家、普丁及其獨裁政權的批評者納瓦尼在獄中被害身亡後,俄羅斯資深媒體人塔伊西婭.別克布拉托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納瓦尼的死是一場政治暗殺,這一點我們都清楚。專制政權幾乎奪走了俄羅斯人的一切:奪走了繁榮的未來,奪走了每個人應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的信念。它剝奪了我們抗議和反抗的權利,奪走了我們的投票權。納瓦尼被殺,表明專制政權試圖奪走俄羅斯社會最後一絲希望。
納瓦尼是自由俄羅斯的活生生象徵,表明一個繁榮、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凡例與致謝 6
自序 吾輩愛自由,願奴隸根除 8
一九一○年代人 15
01|戈揚(1916-2005):我就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 16
02|王若望(1918-2001):豈願苟活吾土,寧肯客死他鄉 26
一九二○年代人 35
03|許良英(1920-2013):為真理奮鬥的愛因斯坦傳人 36
04|夏志清(1921-2013): 共產黨是一個怪物,它的殘暴超過人類想像的極限 46
05|李慎之(1923-2003):不能在刺刀下做官 54
06|何家棟(1923-2006):我不懼黑暗,因為總有群星在天上 65
07|李洪林(1925-2016):心中烈火,筆底風雲 75
08|江嬰(1928-202...
自序 吾輩愛自由,願奴隸根除 8
一九一○年代人 15
01|戈揚(1916-2005):我就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 16
02|王若望(1918-2001):豈願苟活吾土,寧肯客死他鄉 26
一九二○年代人 35
03|許良英(1920-2013):為真理奮鬥的愛因斯坦傳人 36
04|夏志清(1921-2013): 共產黨是一個怪物,它的殘暴超過人類想像的極限 46
05|李慎之(1923-2003):不能在刺刀下做官 54
06|何家棟(1923-2006):我不懼黑暗,因為總有群星在天上 65
07|李洪林(1925-2016):心中烈火,筆底風雲 75
08|江嬰(1928-202...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