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的無神論者
三十歲那年,我決定回到故鄉桃園落腳,開了一家出版社,當作送給自己的「而立」之禮。
這份禮物確實不曾辜負我,讓我遇見諸多美好的人事風景,當然,也讓我在好幾個淺眠的惡夢中驚叫出聲。嚴重低潮時,我巴不得穿越時空追殺當初三十歲了還一派天真的自己。
「你給我醒醒!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我習慣以創業時的三十歲,作為人生分水嶺。在那以前,因為念書當兵拖了很久才出社會,總有著自帶理想濾鏡的理直氣壯;三十歲後,則經常覺得身體帶有異常時差,鬼打牆幾百次,才終於體驗同齡者早就熟稔的人情義理與人生苦澀。
以往,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別人不做應為之事、不挺身而出,而卻選擇沉默;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對一翻兩瞪眼的事情說: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所謂的灰色地帶,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對理想世界的根本詆毀。那時我不懂,理想只有在實現的那一刻,才能印證其正確;在那之前,都是拿來破滅而後修復然後再次破滅的......
身為編輯,接觸的人多,遇到衝突的機率自然不低。更危險的是,成為編輯之前,我們往往是對書本懷抱著愛的讀者,自然對喜歡的作家或是文壇前輩抱有嚮往。直到吃過幾次不信邪的虧,我才學乖,知道作品與人不該畫上等號,知道不少受人愛戴者的黑暗面才是其本體,他們是會走路的地獄,把所有接觸對象都拖進火燄中焚燒。
那時我無法忍受模糊不清或是表裡不一,內心的肌肉卻還不夠堅韌,無法直面衝突與痛苦;忍受不了想逃避,又會憎恨自己的軟弱。
老媽大概從我神色看出,這個自作聰明的兒子無法消化那些障礙,儘管不懂出版是在做什麼,還是淡淡問了:「你是做生意的人了,之前叫你去大廟跟工作室後面的土地公廟拜拜,你有乖乖去嗎?」
有,也沒有。創業初始,老媽會在特定時節備好供品,提醒我帶去拜拜,但我往往人去了,但心不在焉。對當時的我而言,桃園大廟比較像是地理座標,而非心靈燈塔。儘管每次前往參拜也是虔誠,但那彷彿出自約定俗成,類似業務必訪財神廟的心靈機制,而沒有被理解或是所謂被療癒的宗教式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還是會去大廟或土地公廟拜拜,也會對神明傾訴內心的狀況,但仍暗自把拜拜當作身為信徒的義務,是不得不為。也因為年輕,我認為埋在內心之黑暗與痛苦,可以透過工作或是外在認可來舒緩。一旦忙起來,有了正在人生道路上大步前進的錯覺,好像也就沒問題了。
誰知那些黑暗的物質,並不會隨著時間自動分解。它們類似塑膠萬年不壞,永遠在你內心占了位置。正能量豐沛時,它們是囤積症患者的家居,雖然繁雜凌亂,生活在其中總能理出一條路來,即使這意味著必須拗折自己的肢體去遷就、躲避,但只要相安無事,也就接受了。不夠幸運的時候,那些黑暗物質便在你體內敲敲打打,你每說出的一個字每一個音節,都帶著悶悶的共振,它要你意識到它的存在,它要你痛,要你知道是它作主,它說了算。
那幾年,我每天練習忍住祕密,學習噤聲,試圖忽略內心的聲音,把心神專注在出版社的業務。隨著收入表現越來越好,我渾然不覺最嚴重的一次職業災害正醞釀而生。
那一陣子,每天深夜下班騎機車回家的路上,我像是心神失能,在全罩安全帽的遮掩之下,對著遠方的路燈喊出最粗鄙最骯髒的字眼;遭逢特別脆弱的時刻,則是希望眼睛一閉去撞牆。對外還是忙,還是逼著自己正常工作,繼續營造出陽光與開朗的形象,但內心其實是極端厭世的反社會危險分子,若用剛才的話形容,我也變成了會走路的地獄。
我渾渾噩噩,以最低標準的姿態活著。某天午休時間,我打算去市中心吃飯,散步到該轉彎的路口,不知怎麼的,內心覺得應該直走,便聽從直覺走了下去。一路經過好幾個路口,我都直行,最後來到桃園大廟門口,心想人都來了就順便拜拜吧。
我從右邊的門走進去,投了一百塊香油錢,收到一小疊金紙和餅乾。我點了香,對開漳聖王說話,祈禱總是這樣起頭:「弟子陳夏民,感謝開漳聖王照顧逗點文創結社,希望您繼續保佑,讓我們出版社可以久久長長。」但說了說,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開始掏出內心的黑暗物質,告訴祂那些接連讓我跌落地獄而遭受業火焚燒的人與事......參拜完全部神明後,我從供桌捧起金紙,向開漳聖王報告要燒金了,請祂慢慢吃餅不用著急,不忘補上一句:「請借給我智慧,讓我化解眼前的難關。」
焚燒金紙時,我熟練地用手指滑過紙面,在邊角捏出折痕,將之聚成一疊後,引火,投入金爐口。忽然轟的一聲,一陣風起,火勢加劇,一股熱浪撲到眼前,金紙紛紛在爐中飛舞,我加速擲入金紙,像是在牌桌上拋擲籌碼,甚至伸出雙手在爐口感受著熱度,幻想肉身正在爐底燒成一把人形火炬,吶喊著:「壞東西全部燒掉!燒掉!」
說也奇怪,那天回返工作室後,打開電腦,我竟然默默對著螢幕流淚,雖然沒有太戲劇化的轉折,但那次安靜的哭泣,的確卸下了壓在心頭上的不少重量。
之後,我時不時便上桃園大廟找開漳聖王「諮商」。有時候會站在廟裡對著祂說上十來分鐘。遇到彷彿被十八層地獄壓在底下燒的痛苦時刻,則是天天過去,好像是每天晚上都要來蹭飯的、不請自來的鄰居。
幸好祂不會拒絕我。
手裡拿著香,我只能誠實。腦海裡的不堪物事,想偷懶耍了小聰明而犯下的過錯,或基於職業道德無法對外言說,那些在黑夜糾纏著我、讓我喘不過氣的祕密,都隨著香火的煙霧,冉冉傳進了天聽。我們每一次的會晤,也是我無法別過頭去,必須張開眼睛把自己看清楚的時刻。眼前這一尊雕像,彷彿一面鏡子,我不能逃跑,只能持續地凝視著對方的雙眼,告訴祂所有的委屈、憤恨,或是歉疚。
我終於懂得老媽當初的教誨:你不能向神明索討你不該擁有的東西,只能卑微地請求祂借你智慧,讓你自個去消化,去排解。
凡人如我,不能也不敢揣測神的心意,只能在神蹟降臨之前,持續地反芻腦海中的困境,靜靜等待。覺得忍不住快要爆炸了,就再去一次大廟,向開漳聖王祈禱。因為急不得,又怕祂貴人多忘事,只好把事情經過與困境再說個明白,煩人的事情怕說錯了,還得多理幾次頭緒,說上兩三回,請求祂借給我更多智慧與時間來化解。講久,弄懂,好像也看穿了痛苦的肌理與層次。於是我終於學習到,只要沒有害人的意圖,沒有事情不能解決;如果事情始終無法善了,那便是對方的問題,我只能更沉穩,才不會把他的痛苦與業攬在自身,跟著焚燒。
後來,只要有朋友人生卡關,我就會告訴對方我在失意時所見證的金爐大風與夾帶著火燄如落葉飛舞的金紙,是如何焚毀寄宿在我心中的壞東西。然後,我會邀請對方來桃園大廟拜拜,拜完順便請他吃大廟後博愛路上的潤餅或是蚵仔麵線。
有一位無神論朋友陷入困境,我當然邀請他前來拜拜。他反問我,為什麼那麼迷信?
我暗想,虔誠的信徒多是無神論者吧。因為他們清楚向上蒼祈求的一切,不可能無中生有。而能夠接受自身無能的人,才能坦然迎接外在世界夾帶隕石般強大絕望的撞擊與破壞,而不在恐慌中自爆。這不是克蘇魯神話中那無法言說之恐怖詛咒,而是身而為人,有時活在爛泥一般的人生中,就算遭受踐踏,也無法逃離的卑微以及必須懷抱的理性。
其實,我早就知道那天焚燒金紙時所聽見的風起之聲,不過是環保金爐為促進金紙徹底燃燒而安裝在頂端的抽風扇運轉所致。但當下的我需要皮膚能直接感受到的那股燙熱,我有責任去詮釋那陣風聲:在廣闊無垠的世界裡,我必須相信有更高位階的存在,願意無私承接我這個失敗的人,如此一來,我才能夠好好地面對未知,安心活下去。
但我未如實回答那位無神論者,只是笑笑對他說:「等你來桃園大廟,和開漳聖王打過招呼,就知道嚕。」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迷信的無神論者(純文字無添加版,啾咪文庫本)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20 |
散文 |
$ 264 |
中文書 |
$ 270 |
中文現代文學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迷信的無神論者(純文字無添加版,啾咪文庫本)
「不能放過自己的人,眼前所見每一張臉,都是地獄。」
想要成為真正的大人,活得自由自在,要熬過多少來自外界的凝視、又得走過幾次地獄再折返?獨立出版人陳夏民細數成長歷程中的幻滅與矛盾:原來討好不保證能變得討喜;原來被眾人簇擁才更孤單;原來,原來自己才是摧毀他人幸福的大魔王……假如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敘事之中,我不是永遠無辜、永遠善良的那個角色,要如何繼續相信自己,坦然活下去?一本為普通孩子而寫,陪伴你成為大人的抒情散文集。
「我像是《綠野仙蹤》的錫人那般小心翼翼,一邊為踩到小蟲子滿懷歉疚而流淚,一邊為保護桃樂絲與夥伴而揮舞手中鐵斧,毫不遲疑砍下野狼的頭。」
本書特色
■除了文字,不包含其他成分。專注百分百,輕便帶著走,隨時隨地享受無添加的閱讀樂趣。
■睽違六年,繼《那些乘客教我的事》、《失物風景》,邀請你再次進入陳夏民「乘客系列」世界觀。
■不是教學書,沒有即刻上手的知識;以撫慰人心的方式,提供給你變成大人的know-how。
■《工作排毒:讓你咻咻咻的工作編輯術》的雙生之書,建議搭配服用,前中年人生排毒的極佳選擇。
作者簡介:
陳夏民
桃園人,做書的人,迷信的無神論者。桃園高中、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畢業。曾旅居印尼,現於故鄉經營獨立出版社comma books。
譯有海明威、菲律賓文豪卜婁杉作品若干,著有《工作排毒:讓你咻咻咻的工作編輯術》、《飛踢,醜哭,白鼻毛:第一次開出版社就大賣(騙你的)》、《失物風景》、《那些乘客教我的事》、《讓你咻咻咻的人生編輯術》、《主婦的午後時光》(與攝影師陳藝堂合著)等書。
章節試閱
迷信的無神論者
三十歲那年,我決定回到故鄉桃園落腳,開了一家出版社,當作送給自己的「而立」之禮。
這份禮物確實不曾辜負我,讓我遇見諸多美好的人事風景,當然,也讓我在好幾個淺眠的惡夢中驚叫出聲。嚴重低潮時,我巴不得穿越時空追殺當初三十歲了還一派天真的自己。
「你給我醒醒!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我習慣以創業時的三十歲,作為人生分水嶺。在那以前,因為念書當兵拖了很久才出社會,總有著自帶理想濾鏡的理直氣壯;三十歲後,則經常覺得身體帶有異常時差,鬼打牆幾百次,才終於體驗同齡者早就熟稔的人情義理與人生苦...
三十歲那年,我決定回到故鄉桃園落腳,開了一家出版社,當作送給自己的「而立」之禮。
這份禮物確實不曾辜負我,讓我遇見諸多美好的人事風景,當然,也讓我在好幾個淺眠的惡夢中驚叫出聲。嚴重低潮時,我巴不得穿越時空追殺當初三十歲了還一派天真的自己。
「你給我醒醒!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我習慣以創業時的三十歲,作為人生分水嶺。在那以前,因為念書當兵拖了很久才出社會,總有著自帶理想濾鏡的理直氣壯;三十歲後,則經常覺得身體帶有異常時差,鬼打牆幾百次,才終於體驗同齡者早就熟稔的人情義理與人生苦...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只是需要一個說法
在我印象中,榮華街老家一樓曾經掛著一幅黑白畫像,圖的正中央是稍顯模糊的觀世音菩薩站在龍上,周身雲霧繚繞,隱隱透漏著神威。畫像旁留白處則有毛筆字寫著「觀世音菩薩顯聖真影」,小學生時期的我每次經過都會盯著看,腦袋裡充滿疑問。
是誰站在雲上幫觀世音菩薩拍照呢?站在飛機上拍的嗎?當然,我也曾覺得那畫是假的,但畫中模糊的身影反而讓人越看越覺得真實。看久了,我也不再懷疑,就當是真的了。說也奇怪,不再懷疑的那一刻起,我好像就失去好奇心,鮮少再盯著這幅畫像查看細節。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後...
在我印象中,榮華街老家一樓曾經掛著一幅黑白畫像,圖的正中央是稍顯模糊的觀世音菩薩站在龍上,周身雲霧繚繞,隱隱透漏著神威。畫像旁留白處則有毛筆字寫著「觀世音菩薩顯聖真影」,小學生時期的我每次經過都會盯著看,腦袋裡充滿疑問。
是誰站在雲上幫觀世音菩薩拍照呢?站在飛機上拍的嗎?當然,我也曾覺得那畫是假的,但畫中模糊的身影反而讓人越看越覺得真實。看久了,我也不再懷疑,就當是真的了。說也奇怪,不再懷疑的那一刻起,我好像就失去好奇心,鮮少再盯著這幅畫像查看細節。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帶竹柏回家給爸媽養
偶爾想念收驚的感覺
每天Google水庫水位
只要我願意,還是可以躲進去
記憶一段車站時光
反殺麥克.邁爾斯的女人
失去界線的人
疑似住在計程車上的人
日記一
練習不傳遞惡意
屈辱,讓我領悟孤獨的真義
我為什麼變成難搞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你的禮物
不要讓它斷掉
越是低潮,越是要好好吃飯
不想一個人吃飯
日記二
沒有兩碟小菜,不算真正吃飯
有一種冷漠正在蔓延
想要認得Minji的臉
成為專業的人了
漫長的動森暑假
日記三
被感冒病毒帶走的超人
如果永遠無法打敗大魔王,怎麼辦?
把活著...
偶爾想念收驚的感覺
每天Google水庫水位
只要我願意,還是可以躲進去
記憶一段車站時光
反殺麥克.邁爾斯的女人
失去界線的人
疑似住在計程車上的人
日記一
練習不傳遞惡意
屈辱,讓我領悟孤獨的真義
我為什麼變成難搞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你的禮物
不要讓它斷掉
越是低潮,越是要好好吃飯
不想一個人吃飯
日記二
沒有兩碟小菜,不算真正吃飯
有一種冷漠正在蔓延
想要認得Minji的臉
成為專業的人了
漫長的動森暑假
日記三
被感冒病毒帶走的超人
如果永遠無法打敗大魔王,怎麼辦?
把活著...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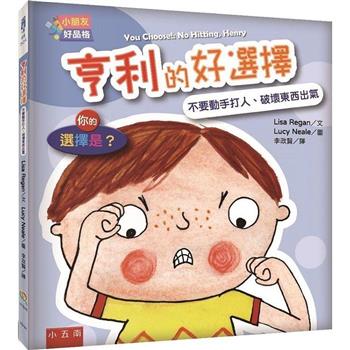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國民營事業]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