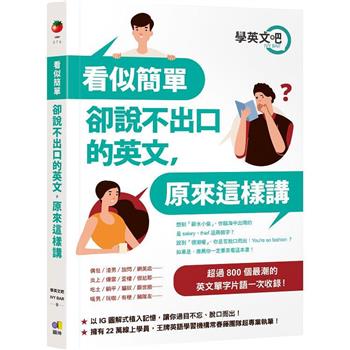嚴歌苓開啟時代敘事的大門——
世界是不安分者發現並開墾出來的,
人生無論成敗,都不過是一場海市蜃樓。
90年代的中國海南島,猶如美國西部拓荒時代,混亂無序、充滿機遇,吸引了無數懷揣夢想的闖蕩者前來追逐財富與成功。
在這片充滿機遇與陷阱的土地上,河北青年張明舶邂逅了命運中的兩位女性——富商情婦小婷和煙花女藍蘭。小婷是他的初戀,她在張明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然而,現實中的重重挑戰讓這段愛情變得脆弱而遙不可及。藍蘭則是張明舶在困境中的依靠,她的無私奉獻,讓張明舶在生活的風雨中找到力量。
期間,張明舶還遇到了神秘多金的標總、狡猾貪婪的阿埠,捲入了泡沫經濟的貪婪與混亂,經歷了人性的掙扎與沉淪。
★如《大亨小傳》般的夢想與幻滅
張明舶追求愛情和財富的過程,猶如蓋茲比對綠光的追逐,美麗而脆弱。小婷如同那遙不可及的夢想,激發了張明舶無盡的渴望,然而現實的殘酷,最終讓夢想如同海市蜃樓般破滅。
★以《繁花》般的濾鏡,刻畫大時代下的小人物
《蜃樓》的時代描寫,與金宇澄的《繁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嚴歌苓用她敏銳的觀察力和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中國90年代充滿生機與複雜人性的社會畫卷。
「他捨不得的,還有藍蘭。會做重口味貴州菜的藍蘭;忍辱負重、舉重若輕的藍蘭;知福惜福的藍蘭,總是說:『怎麼都比我們老家好多了,我們老家窮得呀⋯⋯』她總是斷在這裡,似乎看到了那樣遼闊廣袤的貧窮,一眼望不盡,令她目瞪口呆,訝異失語,因為那貧窮超過了語言的形容,就像美景美到了超過任何詞句的描述。」
本書特色
1. 深刻而真實的愛情描寫
嚴歌苓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男主角張明舶與藍蘭、小婷之間的情感糾葛,不僅真實感人,還揭示了愛情的善變、甜蜜與苦澀。
2. 豐富的歷史與社會背景
故事以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海南島為背景,真實再現了底層小民為了夢想和生計而拼搏的故事。
3. 真實呈現中國房地產泡沫
《蜃樓》反映了90年代海南島的經濟繁榮與泡沫化危機,在跟隨著張明舶追求財富和夢想的過程中,彷彿親身經歷了當代中國房地產的起伏。
4. 立體豐滿的人物形象
嚴歌苓善於塑造複雜而真實的人物形象:張明舶的勇敢執著,藍蘭的無私奉獻,小婷的清純溫柔,標總的狡猾貪婪⋯⋯,性格鮮明的角色,展現了人性的多樣與複雜。
推薦人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羅毓嘉|詩人
顧玉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