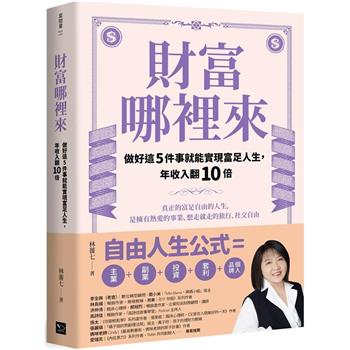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老人與海【中英對照.權威教授譯本】的圖書 |
 |
老人與海 作者:歐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 譯者:黃源深 出版社:大溏 出版日期:2024-12-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64 |
美國文學 |
$ 276 |
中文書 |
$ 277 |
世界古典 |
$ 315 |
歐美文學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譯者身兼英美文學研究學者、教育家及資深翻譯家,在《老人與海》的眾多譯本中,提供了一個兼具文學與語言專業與教學示範的精采譯本。
★林桂鳳(新竹市新竹女中校長)、周婉玲(台北市仁愛國中校長)、張麗萍(台北市政大附中校長)、鄭文儀(高雄女中校長).誠摯推薦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卻不能被打敗。」
老漁夫聖地牙哥連續出海已經84天了,一條魚都沒有到手。
整個小漁村裡,只剩一個叫曼諾林的孩子還對他充滿信心:聖地牙哥是他所認識最厲害的漁夫。
第85天,聖地牙哥在晦暗的清晨與曼諾林道別,直到天濛濛亮時,他發現自己來到了比自己預期得更遙遠的海域。
茫茫大海上,他隻身一人,像廣袤草原上的一頭老獅子,遭遇了此生未曾見過的龐然大物……
精簡的文字,深刻的描述,直白的情節與充滿力量的故事,令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始終名列各種百大必讀書單,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通過老人聖地牙哥這個「硬漢」形象,海明威熱情歌頌了人在充滿暴力和死亡的現實世界中表現出來的永不言敗的勇氣和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作者簡介:
歐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他最傑出的作品是《老人與海》,此外還著有《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又譯《戰地春夢》)和《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又譯《戰地鐘聲》)等名篇佳作。海明威的寫作風格非常簡潔,對美國文學及20世紀文學的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讚譽:「他能把一個短篇的故事反覆推敲,悉心剪裁,以極簡潔的語言,鑄入一個更小的模型,使其既凝練又精當。讓人們獲得極鮮明、極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達的主題。」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評價海明威:「幾乎沒有哪個美國人比海明威對美國人民的情感和態度產生過更大的影響。」稱讚海明威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譯者簡介:
黃源深,1940生於浙江新昌,歷任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教師,澳大利亞雪梨大學碩士,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主任,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現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黃源深同時是中國著名的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英語教育家、資深翻譯家,曾任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長、上海翻譯家協會副會長、教育部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其所翻譯的《簡.愛》、《老人與海》、《格雷的畫像》、《歐.亨利短篇小說選》……等十部英美和澳大利亞小說,也因其流利的文筆和翻譯的準確性及靈活性,廣受譯界關注與好評。其中《簡.愛》之節選收入高中語文教材,並被譽為「最好的《簡.愛》譯本」。
老人瘦骨嶙峋,頸背上刻著深深的皺紋,臉上留著良性皮膚腫瘤引起的褐色斑塊,那是陽光在熱帶洋面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