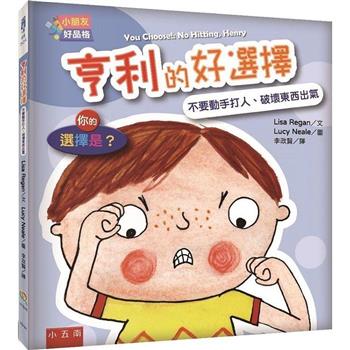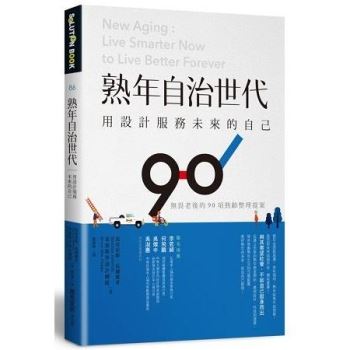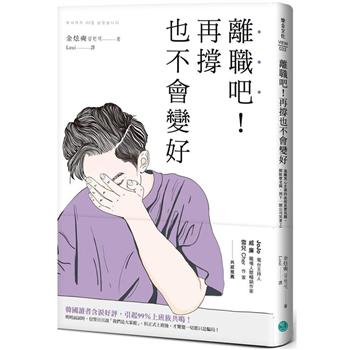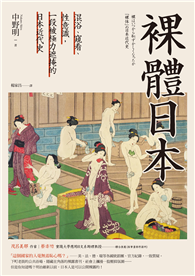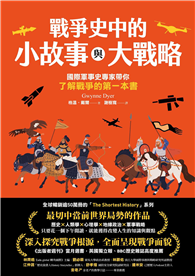本書是作詞家林煌坤先生所著,自述其先祖自福州渡海來臺,迄今已傳承四代以來的家族故事。
長達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跨度,臺灣歷經了清廷統治、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接管,這樣的時代更迭也如實呈現在故事之中;此外,作者穿插不少真偽交錯的歷史事件、甚或鄉野傳說,更讓本書不僅僅是私人的家族傳記,增添了許多歷史小說般的閱讀趣味。
作者一生致力於臺灣民歌和臺灣歌謠的紀錄與保存,在故事中,可以尋得其對音樂藝術的天分與熱愛是從何而來;其對樂曲演奏、舞蹈、戲劇等描述,無不細膩動人,讀之宛如躍然紙上,彷彿觀賞了一場又一場精彩萬分的演出。因作者曾從事編劇工作,書中最後一篇更是別出心裁、使用了劇本的形式撰寫,呼應了其人生經歷。
一位由福建隻身渡海來臺的青年──林水泉,
一段三弦與月琴的交響的音樂奇遇,
自此開啟了林家四代在臺南落地生根的家族傳承。
他們大多才華洋溢,熱愛音樂、熱愛歌舞,卻更熱愛自己的家國;
他們不屈於權勢與異族的統治,敢於起身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
歷經時代的更迭,不變的始終是這個家族的風骨,以及他們對家鄉與對這片土地的關懷。
正如一首首誕生於民間的歌謠、流行於各時代的歌曲,
是另一種有別於文字記載歷史的方式;
林氏家族在致力於保存這些珍貴「歌史」的同時,
更見證了臺灣百餘年以來的音樂發展。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恁的時代,咱的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恁的時代,咱的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煌坤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臺南縣歸仁鄉,天資聰穎,音感和文筆俱佳。家中務農,因經濟因素考入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
畢業後,林煌坤在劉家昌的片場擔任場記,受到賞識,兩個月後升任為副導演,開始其編導生涯。一次機會,毛遂自薦為劉家昌新作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填詞,推出後竟一炮而紅,成為暢銷超過百萬張的流行歌曲。
之後,他又陸續創作了〈祝你幸福〉、〈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含淚的微笑〉、〈償還〉、〈美酒加咖啡〉、等歌曲。在一九七○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共創作出上千首歌詞。
除寫詞之外,他也從事編劇工作,如《春寒》、《在水一方》、《電影秀》等電影劇本,後來更為豬哥亮的餐廳秀編寫了一千多集的劇本。
林煌坤亦熱心於臺灣民謠、歌謠的資料保存;並曾與汪笨湖主持《黑狗來了-台灣歌謠一百年》節目,解說臺灣歌謠背後隱藏的故事。
林煌坤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臺南縣歸仁鄉,天資聰穎,音感和文筆俱佳。家中務農,因經濟因素考入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
畢業後,林煌坤在劉家昌的片場擔任場記,受到賞識,兩個月後升任為副導演,開始其編導生涯。一次機會,毛遂自薦為劉家昌新作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填詞,推出後竟一炮而紅,成為暢銷超過百萬張的流行歌曲。
之後,他又陸續創作了〈祝你幸福〉、〈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含淚的微笑〉、〈償還〉、〈美酒加咖啡〉、等歌曲。在一九七○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共創作出上千首歌詞。
除寫詞之外,他也從事編劇工作,如《春寒》、《在水一方》、《電影秀》等電影劇本,後來更為豬哥亮的餐廳秀編寫了一千多集的劇本。
林煌坤亦熱心於臺灣民謠、歌謠的資料保存;並曾與汪笨湖主持《黑狗來了-台灣歌謠一百年》節目,解說臺灣歌謠背後隱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