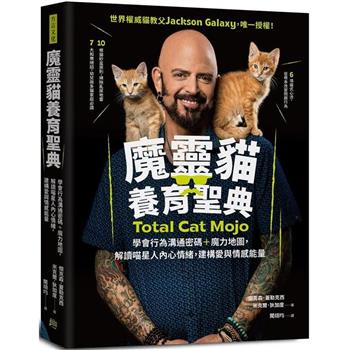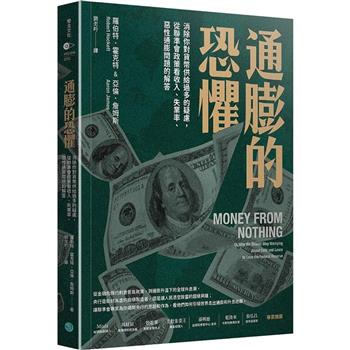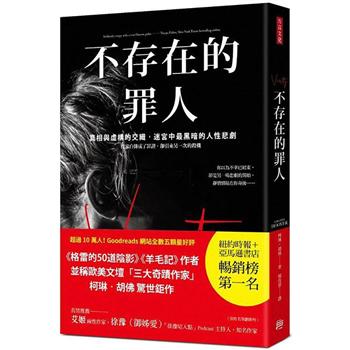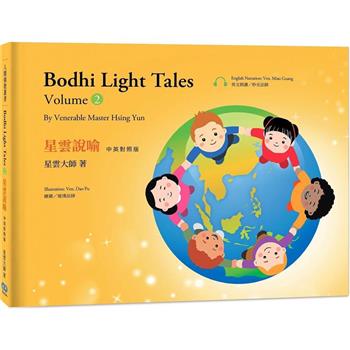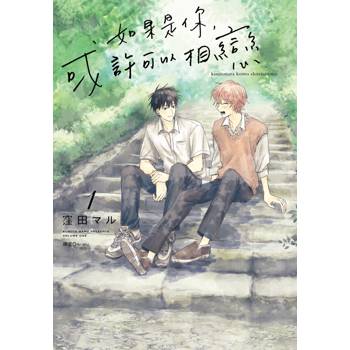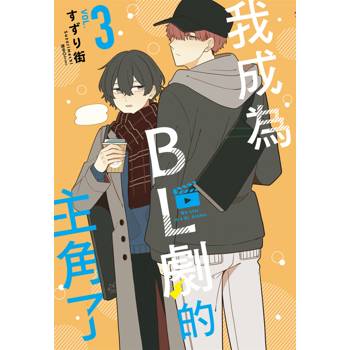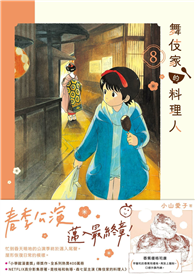作者序
莊子對秩序很失望
時空是由秩序構成的,萬物就是一個由秩序構成的巨大的自組織系統,所謂自組織系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系統,道家稱之為「道」。大到日月星辰,小至微塵蜉蝣,它們載沉載浮,天生天滅,無不統一在這個宏大循環之中……
基於這一前提,從道家的觀點來看,我們有史以來經歷的所有的秩序無一不是人為的,也即不自然的,而不自然的秩序一定會出問題。莊子對現實是持否定態度的,莊子對現實的否定也即對一切人為秩序的否定。
這一否定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即便人類一定離不開某種秩序,那麼我們也不應該對其預期過高,甚至也無須預期過低,對任何一種秩序預期過高或過低,都會叫我們付出相應、抑或是慘痛的代價,起碼會使我們變得庸俗和淺薄。假定人類由於沒有產生自我意識而從動物種群中獨立出來,假定人類沒有因為使用工具而讓生產力得到提高了不恰當的程度,那麼一切問題也就無從產生了。
自我意識滋生了私欲與貪婪,剩餘價值產生了誘惑與傲慢,它們如影相隨,與人類一同步入了文明的門檻,然後又從生物學的層面,每每將人類重新帶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之中。
這使人類不得不匆忙地面對這樣一個不期而遇的難題,即如何建立一個自然不曾賦予的秩序系統,用以安頓心靈,維繫存在。
應該說,在天人合一、也即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而非主宰的前提下,對自然的敬畏並未使中國的先民凱歌高奏,膨脹為宇宙的管理者。他們希望儘可能不另起爐灶,而是透過仿效自然並與其保持平行的情形下,構建起一套與之相與協調的秩序,然後將人類的行為重新納入到自然的那個大系統之中……大量歷史資料表明,自新石器末期開始,至遲到西周時期,以《周易》為標誌,中國文化已經完成了理論建樹。
為什麼一定要以《周易》為標誌呢?在此,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古希臘哲人柏拉圖說過的話:「真正的知識存在於兩個層次,只有在第二個層次,即形式的層次,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的所在,真正的知識是關於形式的知識。」而太極為標誌,《周易》恰恰為中國文化提供了這樣一個難以撼動的核心,暨一個形式完美、邏輯嚴謹的解釋系統與推理系統。
靠著這個解釋系統與推理系統,中華文明在哲學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同時為保障人與自然的普遍聯繫不被人為割裂,在科學上確立了用時間和空間為座標,把萬事萬物用功能(而非結構)統一起來的邏輯體系;在文化上則將和諧—即「禮」作為最大價值共識。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體系或道統就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儘管在生產方式的制約下,尚需足夠的交通與通訊作保障,但是縱觀有中國文化理想國之稱的《周禮》,我們仍會歎服其設計的宏大與縝密,比如其監察與制約機制即便是放到今天也不失嚴謹。如果這樣一種秩序出了問題,那麼一定是人類本身出了的大問題。
春秋末年以降,由於鐵器的廣泛應用,生產力空前提高,剩餘價值得到了大幅增加,固有的平衡被打破,在私欲與貪婪的驅動下,發端於黃帝,完成於周公的禮樂文明,價值體系迅速瓦解,仁義道德異化為爾虞我詐和巧取豪奪的藉口與工具,在利益的重新整合中,中國進入了劇烈的擺盪期。
道家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現象的本質,與其說是現行秩序出現了破綻,毋寧說是人類本身出現了大問題,而人類的秩序系統即使再完美,再縝密,也無助於解決這個大問題。
實際上是道家的楚隱者與孔子學生子路的對話應該是二者的最直接表白:
楚隱者說:「世道衰落,禮崩樂壞,私欲如同滔滔的大水氾濫,天下都是這樣啊,你們和誰去改變這種現狀呢?」意在救己。
孔子聽後對子路說:「人與鳥獸是不可同群的,我不同世人相處,又和誰相處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會與大家一起去改變這種現狀了。」志在救世。
作為道家代表的莊子無疑是救已派,沒落貴族的身世使其遠離主流,天賦的敏感使其性格內向,所以與其說莊子崇尚自由,不如說莊子崇尚尊嚴。而在充滿動盪和憂患的現實世界中,到處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傾軋與尷尬。在夾縫中生存的每一個個體生命都無所謂自由與尊嚴。這使他意識到,要保持自由與尊嚴,就要盡可能地與所處的環境拉開距離。他希望透過摒棄世俗價值的約束、拒絕合作,來保全人格的獨立和完整,去追求無條件的精神自由,從而使心靈得到解脫與超越。
這使他自覺地退出了秩序之外,而秩序之外的旁觀者身份也賦予了他精闢和冷峻的洞察力。
莊子認為,人們置身這樣的秩序中,要麼利用、要麼被利用,都是對生命的戕害與褻瀆,所以他既排斥儒家取法自然的仁義道德、亦否定墨家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平等博愛。面對人類的私欲與貪婪,對任何一種秩序的選邊都是幼稚可笑的。
但是事實上,在利用與被利用之外,莊子還是別開蹊徑,給後人、或者說給中國的知識分子開闢了第三條路,也就是他自己選擇的這條路。
孔子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帶進秩序中,叫他們滿腔熱情的學以致用,立功立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他們一旦受到挫折和打擊,莊子就把他們從秩序中收容過來,消除他們的鬱悶和創傷,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撫慰。莊子以其所確立的「精神自由」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營養和用以安頓心靈的精神家園,也塑造了最具中國文化特徵的關於「自由」的完美原型。
而賴於莊子所面對的秩序在理論上的完美與嚴謹,使其得以超越對具體社會現象的憤世嫉俗,昇華成對人類秩序本身進行質詢,具備了理性的高度和永恆的價值。這是道家的幸運,也是莊子的幸運。
在秩序之內人們的眼中,鵬鳥一飛沖天,扶搖直上九萬里,背負青天似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礙它了;而列子樣子輕盈美好地御風而行,一去十五日方才返回。他們超凡絕塵,似乎已迫近了自由極限,但在秩序之外的莊子看來,由於不能不有所憑藉,所以都算不上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或尊嚴。
關於人類秩序之藏否、或者說是救世與救己的不同主張自古及今一直存在著,甚至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世要救、已也要救,二者各行事,並行不悖,無疑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