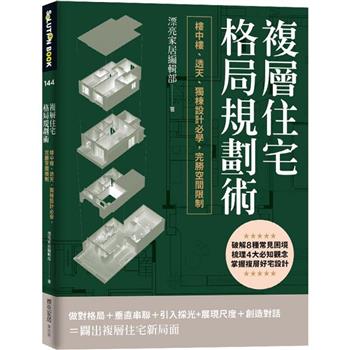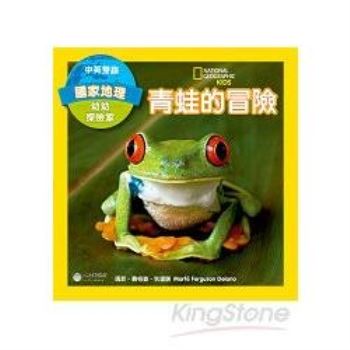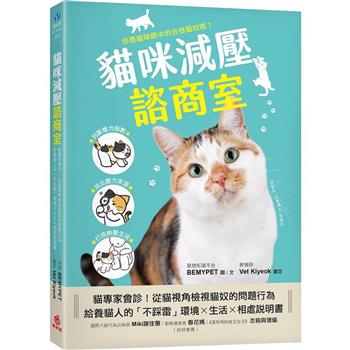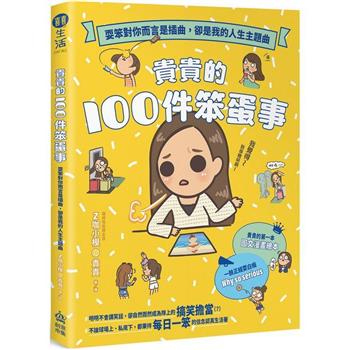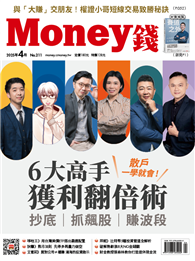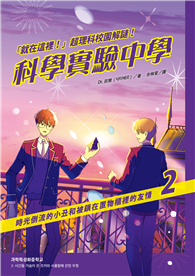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白醫師回憶錄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本當代醫療現場的回憶錄小說
「我當醫生是為了救人,救人什麼時候變成折磨人?
是什麼讓助人的現場變調?
種種念頭一閃而逝……」
他們說我是守護者,守護患者免於疾病的傷害,為什麼帶來傷害的、跟我交手的,不是疾病?
他們說我從事醫治的職業,是撫慰病痛的工作,為什麼我診察這個職業,發現這行深陷病痛、需要醫治?
他們說我們應該重視生命,因為人命關天,為什麼我撞見生命被當作交易權勢與地位的籌碼,被廉價地賤賣拋售?
《白醫師回憶錄》回放白醫師記憶中最難忘的一段歲月,為讀者敞開住院醫師小白的所思所想,及小白如何懷著這些疑惑,在血雨腥風的白色叢林探險,摸索陷阱之上的求生藝術。
共感推薦
侯文詠(華文暢銷作家)
林運鴻(文字工作者)
楊鎮宇(文字工作者)
熊一蘋(文字工作者)
吳易澄(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
劉介修(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醫師)
謝宛婷(奇美醫院緩和醫療中心主任)
「一直沒有搞明白,當初醫學院畢業時,沒有選擇直接去當醫生的原因。好不容易考進了醫學系,又花了七年在課堂和醫院關關難過。成為醫師學徒之路,不知道何時開始變得徬徨。從這個一層一層,彷彿只能直線攀爬的階梯上出逃,因為時常感到格格不入,感到生存艱難。
閱讀《白醫師回憶錄》,是種療癒的經驗。原來,我們都在白色叢林裡尋找生存之道。
已經不太確定最後究竟是倖存,或滅絕。繞路多年後回到醫院,生存依然艱難,也許正因為太在乎。倖存者與出逃者真誠對話的集體敘事,在細菌病毒與個人化的道德勸說外,指向更根本的制度與文化根源。我們繼續一邊掙扎生存,一邊一起找路。」
——劉介修(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醫師)
「如果把一百位醫師的回憶錄放在一起,會有多少核心的情節類似?恐怕程度非常高。《白醫師回憶錄》正是一本這樣掏心剖肺把臺灣醫療社會的實相與鏡映端給眾人的小說,真實的主角並不是白醫師,而是一齣名為『醫療』的劇碼。作為總是會走上這個舞台搬演一段人生的每個人,我推薦大家都能讀過它。
小說裡的白醫師彷彿滄桑盡歷、俯案自嘆,然而作者對醫療的熱情卻掩蓋不住,那是內心仍兀自猛烈跳動的醫者之筆才能流淌的文字。我想起某個清晨,我在樓梯牆邊陪伴一位因為病人而痛心流淚的後進醫師,爾後我因為他給我的感觸,想起《小孤島大醫生》的主題曲〈騎在銀龍的背上〉中的那幾段歌詞:
悲傷啊 快變成羽翼吧
傷痕啊 快變成羅盤吧
就像仍不會飛的雛鳥般 我感嘆著自己的無奈
在夢想尚未來到之前 昨日我徒然顫抖地等待
明天 我將登上山崖往龍的方向前去 我將高喊:走吧!出發吧!
白醫師與千千萬萬個白醫師,還在醫療進行曲中前進,這是讓人安心的。」
——謝宛婷(奇美醫院緩和醫療中心主任)
「這是一本白袍之路的反敘事。所謂的『反』,在於作者忠實地寫出行醫路上可能降臨的不滿、困頓與叛逆。有別於訴求溫情的溫馨小品,或是強調仁心仁術的勸世之言,作者把住院醫師訓練過程中可能稍縱即逝的各種反省與批判端上了主桌。這本小說可說是白色巨塔中的『謎之音』,雖為虛構卻又真實無比。它讓我們看見行醫並不只是醫病,同時也是與自己搏鬥。作者時間魔術師告訴我們,行醫並不一定總是遵循著至高無上的醫師誓詞,大多時候可能需要在規則的邊緣遊走;在面對各種倫理困境、文化衝突、勞權低落,乃至於科層官僚的壓迫之中,仍需本著善意行動,但也必須練習在制度的夾縫中抵抗。」
——吳易澄(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
「對醫院環境和醫護人員心理的描寫非常深入,讀到和自己經驗相關的部分甚至會有點抗拒,但也因此恍然大悟:原來之前在大醫院裡感受到的冷淡和武斷,其實也是醫護人員為保護自己設下的防衛,在我們承受原因不明的肉體苦痛時,診斷的醫師也在腦中與過多的可能性和風險奮鬥,讓我第一次感覺找到了可以和醫師共感的起點。」
——熊一蘋(文字工作者)
「那位醫界政治明星從神壇猛然跌落的今日,或許我們會想,百年來集臺灣社會三千寵愛的白袍醫師,是不是其養成培育之過程,已經悄悄質變?本書讀來有如青年醫師的職場手札,帶著熱血真誠的小白兔,短短數年蛻變為世故又悲傷的胡狼──從急診室到醫師協會、從理想崇高到筋疲力竭,險惡職場如何耗盡一名年輕新血的能量?不按牌理出牌的懸壺心情又怎樣在現實利益中騰挪妥協?《白醫師回憶錄》或許是醫者未老先衰的緊急告白:若國民生病,有大夫來治,但如果醫療體系傾斜失衡,這慢性重症又該求救何處?」
——林運鴻(文字工作者)
「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是講幫助人的故事,傳達溫馨的感覺。而《白醫師回憶錄》也談助人的事業,但帶來的是不安、恐懼、痛苦等情緒。讀這本書,會引起諸多身心不適,卻也是個模擬面對病痛、生死議題的機會。
我們大多數人去醫院,不外乎兩種情況:自己生病了或陪生病的親友去看病。只要我們去醫院,很難不面對擔心、病痛及對死亡的恐懼。在醫院裡,被這些問題纏繞的我們,很少有機會或很難有餘裕,去體會醫師的想法和感受。
每天跟病痛與生死議題打交道的醫師在追求什麼?他們因為什麼而受苦?最害怕什麼?用什麼心法來面對?多了解這些,對我們很有幫助。有朝一日,我們成了病患或病患家屬,會更知道怎麼跟醫師合作,更知道怎麼讓醫師發揮得更好。人們常說良藥苦口,這本書讀起來也是這種風味。」
——楊鎮宇(文字工作者)
作者簡介:
時間魔術師
一介寫作新手,白醫師的好朋友,普通的古道熱腸醫生。
回憶我的一生,刻骨銘心莫過於住院醫師訓練時期。
二十九歲那年,我在首都歷史悠久的醫學中心擔任第三年住院醫師。
上過無數夜班,依然不習慣內科加護病房。
剛跟同事交接班,「那床」就心跳停止,我請護理師聯絡主治、把太太扣來醫院。面對六神無主的家屬,我當場壓斷病人肋骨。卡滋卡滋、啪嘶啪嘶,隨著聲響變化,三十分鐘過去,我們宣布急救無效。主治醫師到來,描述團隊的種種努力、會診過的各科醫生、安排的許多檢查治療,並將家屬們帶到休息室安撫。
水珠撞擊窗戶玻璃。
首都的夜晚,暴雨滂沱、悶雷滾滾。...
第一章 鬼故事
第二章 虛妄與真實
第三章 發聲障礙與失智
第四章 剝皮地獄
第五章 不朽的永動機
第六章 出院、住院
第七章 病識感
第八章 醫糾與醫術
第九章 白血球
第十章 布巾上、布巾下
第十一章 新冠肺炎隔離病房
第十二章 VIP
第十三章 會長
第十四章 送行
第十五章 我很快樂
第十六章 年休
第十七章 行醫
尾聲
後記
作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