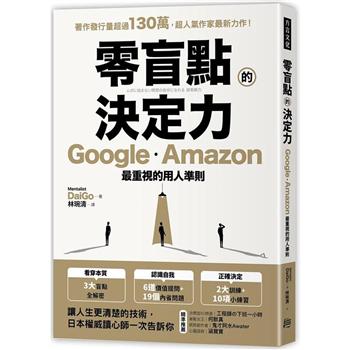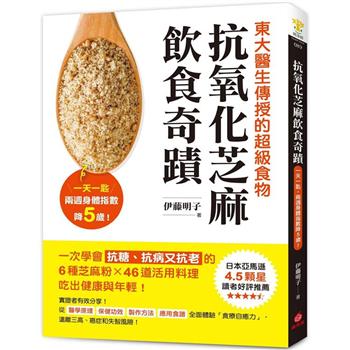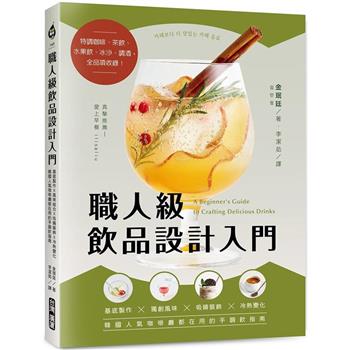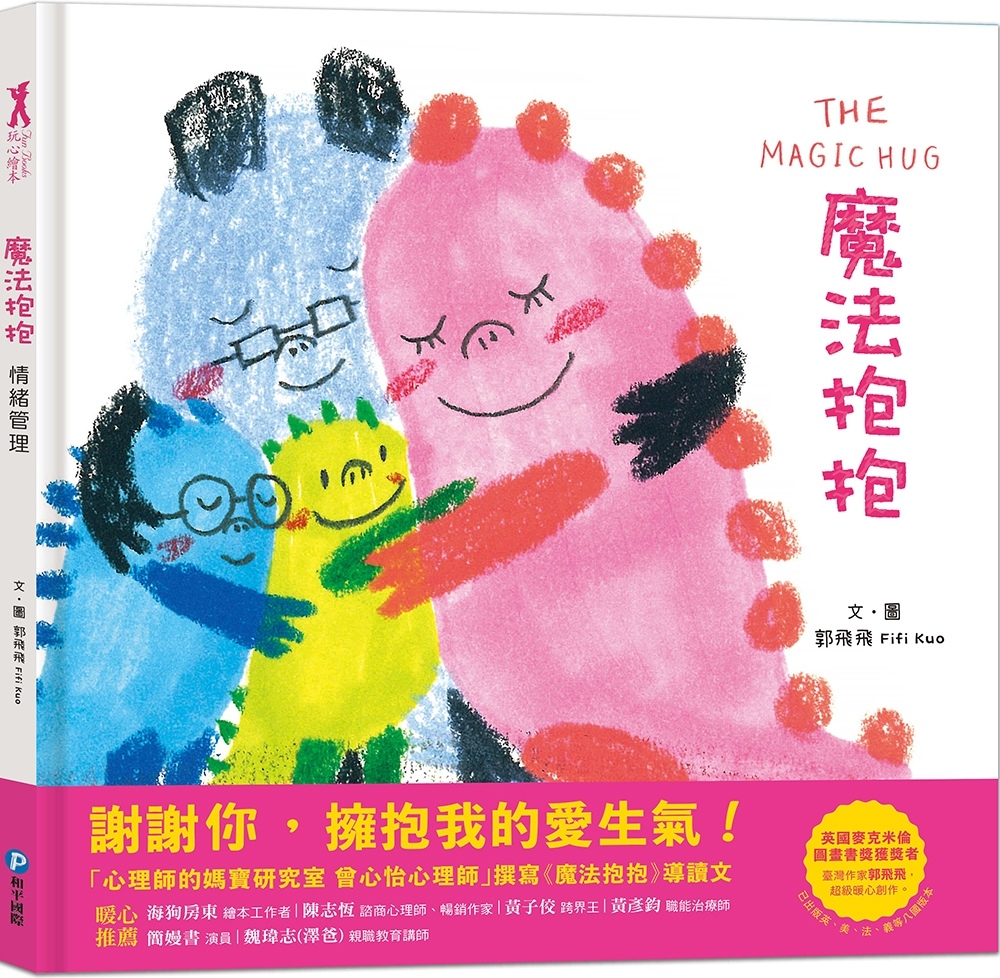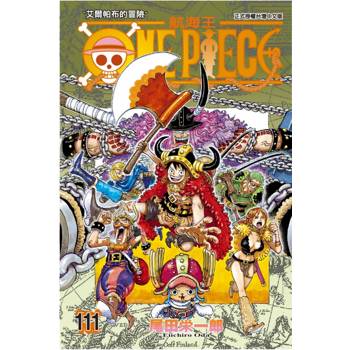執手當代理論大師,走過時代的荒漠
孤獨是寫作的本質,思索堅定意志
書寫是為了鎮痛,或者鎮魂
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洛楓
理論就是某種高點,賦予我們框架去觀察時代與自身,思考現實與行動。本書文章聚焦歐陸哲學當代思潮,包括羅蘭巴特、班雅明、福柯、阿甘本、蘇珊桑塔格等;並討論當代著名作者如村上春樹、昆德拉、里爾克、夏宇、西西等。書中從理論大家以及經典作者的作品中尋找書寫理論的根柢,探求書寫的內在動力與自我要求,同時一一面對嚴肅評論不敵網絡口水泥沼、閱讀氣氛低迷、時代狀況令人失語等等負面條件,再轉而尋找書寫的堅實意志,兼具批判力與情感召喚。為當代理論愛好者、文青、創作者與研究院學生所必讀。
同好推薦
「洛楓是我當年的同事,她的新書, 內容豐富,都是我喜歡的題目, 真是迫不及待想拜讀。作家和散文家筆下的理論, 就是與眾不同,可以把文化理論融入essays的模式。」——李歐梵(學者)
在孤獨的核心兀然四望,書寫的策略原來如此豐饒。洛楓為作者和評論人燃點的指路明燈,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辯證的溝通。能與一個又一個「孤清」的身影相遇,注定必須獨然,卻不寂寞。
——朗天(文化評論人)
做不合時宜的事,往往就是合時的。洛楓,她喜歡思考,喜歡閱讀跟她一樣喜歡思考的人,然後寫下一段一段她們的邂逅,其實是一個一個的邀請,請我們一同思考。在這個不特別鼓吹思考的年代,寫這樣的一本書,多不合時宜,多合時。
——周耀輝(學者/作者)
不合時宜者,正因錯過當下,而得以享有與任意當下一再斜身對接的自由。作品要求重讀,理論期待重寫,洛楓在書中勾出私選清單,砌作群像,反思書寫在當下的意義。於此,洛楓以實踐印證,理論正是生活的方式,也是生活下去的可能。
——葉梓誦(作家/《字花》主編)
羅蘭.巴特一生寫作而且決定持續下去,歸根究柢還不是源於一種不得不寫的存在狀態?這種狀態只為個人出發,不涉及讀者的考量、刊物的載體或媒介市場,甚至公眾利益或道德教化,完全只是自我界定的一種行為。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阿甘本對「當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第一個定義是「不合時宜」(untimely),指出真正的當代人不與時代吻合、也不順應時代的需求,他們徹底是不相關、不切題和毫不相干(irrelevant)的人;然而,正正由於他們跟時代斷開連接,才比其他人更能抓住當下,這種不合時勢並不代表活在其他時空,這些人不過是鄙視那個既不能改變又無法逃避的時代而已。
——〈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阿甘本論「當代性」〉
評論人問:「別人對你的詩的理解總是不及你自己?」夏宇答:「這個問題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有意義。」詩人認為一個讀者怎樣閱讀作品,無論是否理解、同意不同意,作家不一定知道,也很難干預,這種狀態像極了愛情:「我愛你,可是與你無關!」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作者簡介:
洛楓
香港詩人﹑文化評論人,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擔任台灣金馬獎電影評審委員、香港電台廣播節目《演藝風流》主持、香港舞蹈團舞劇《中華英雄》的文本構作,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
著有詩集《距離》、《錯失》、《飛天棺材》、《頹城裝瘋》、英譯詩集《自我紙盒藏屍的日子 Days When I Hide My Corpse in a Cardboard Box》和《愛在創傷的城 Love in the City of Trauma》;小說集:《末代童話》、《炭燒的城》和《第三身》,以及散文集《變臉幻書》。另有評論集《世紀末城巿:香港的流行文化》、《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女聲喧嘩:媒介與文化閱讀》、《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情書光影:洛楓演藝評論集I》、《迷城舞影:洛楓演藝評論集II》、《游離色相:香港電影的女扮男裝》和《獨角獸的彳亍:周耀輝的音樂群像》等。
其中詩集《飛天棺材》獲2007年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文化評論集《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獲「2008香港書獎」及「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等獎項;2016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界別)、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頒發「城市當代舞蹈達人獎2016」,2023年再度獲得「藝術家年獎」(文學藝術界別)。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洛楓是我當年的同事,她的新書, 內容豐富,都是我喜歡的題目, 真是迫不及待想拜讀。作家和散文家筆下的理論, 就是與眾不同,可以把文化理論融入essays的模式。
——李歐梵(學者)
在孤獨的核心兀然四望,書寫的策略原來如此豐饒。洛楓為作者和評論人燃點的指路明燈,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辯證的溝通。能與一個又一個「孤清」的身影相遇,注定必須獨然,卻不寂寞。
——朗天(文化評論人)
做不合時宜的事,往往就是合時的。洛楓,她喜歡思考,喜歡閱讀跟她一樣喜歡思考的人,然後寫下一段一段她們的邂逅,其實是一個一個的邀請,請我們一同思考。在這個不特別鼓吹思考的年代,寫這樣的一本書,多不合時宜,多合時。
——周耀輝(學者/作者)
不合時宜者,正因錯過當下,而得以享有與任意當下一再斜身對接的自由。作品要求重讀,理論期待重寫,洛楓在書中勾出私選清單,砌作群像,反思書寫在當下的意義。於此,洛楓以實踐印證,理論正是生活的方式,也是生活下去的可能。
——葉梓誦(作家/《字花》主編)
名人推薦:洛楓是我當年的同事,她的新書, 內容豐富,都是我喜歡的題目, 真是迫不及待想拜讀。作家和散文家筆下的理論, 就是與眾不同,可以把文化理論融入essays的模式。
——李歐梵(學者)
在孤獨的核心兀然四望,書寫的策略原來如此豐饒。洛楓為作者和評論人燃點的指路明燈,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辯證的溝通。能與一個又一個「孤清」的身影相遇,注定必須獨然,卻不寂寞。
——朗天(文化評論人)
做不合時宜的事,往往就是合時的。洛楓,她喜歡思考,喜歡閱讀跟她一樣喜歡思考的人,然後寫下一段一段她們的邂逅,其實是一個一個...
章節試閱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發需要尋求文化上的突破與革新,而「寫作」是其中一個戰場。對於這樣的提問,一些作家覺得太空泛而採取防衛的姿態,只簡單的回應說沒有其他專長;也有作家洋洋灑灑列出非常宏偉的理由,像為了娛樂自己和大眾、教導別人一些道理、改變世界、傳揚前衛的思想、抒發情操、獲取名氣和報酬等等。卡爾維諾認為這些宏願跟他都有很遠的距離,他既不從事教育工作,也不相信寫作可以改變現實,而且有時候連自己的理念都感到疑惑或發生錯誤,又如何給予別人指標?相反地,寫作不單要付出勞力的代價,而且也會對自身產生暴力的回擊,因此,他只能從個人細小的位置思考這個為何而寫的議題。
一、由「為何寫」到「寫下去」
卡爾維諾列出的理據有三:第一是由於不滿意以前的書寫,所以必須不斷寫下去以尋求補救、更正和圓滿,寫作是將舊有寫下的東西刪除、抹去和擦掉,再以新的、未知寫成怎樣的作品替代。第二是每當看到有人寫得這麼好的時候,自己也心動技癢而躍躍欲試,可惜優秀的作品通常都無法模仿,卡爾維諾只好將書放回書架上,然後突然一些字詞、一些句子湧現腦海內,於是他不再惦記那本寫得成功的書或任何類近的範式,而是專注於思考自己還未寫出來的那本著作!第三是學習個人不懂的東西,不關乎寫作的技法,而是特殊的生命經驗(life experience),不是為了教導別人,或以此作為寫作材料,而是發掘自己不足的痛苦意識;在這種狀況下,為了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卡爾維諾說必須不停累積資料、概念、觀察和經驗,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知識和智慧,只能寫於紙上的剎那才能達到和完成。卡爾維諾的闡述,在我看來,活脫脫就是怎樣維持寫作行動(action of writing)的實戰方法:不滿意過去完成或成就的作品,想像和追求未來寫得更好的表現,以寫作填補個人的欠缺,同時不斷更生和蛻變自我,不讓寶貴的經歷流失,印記每個瞬間的人生體驗—這是一種流動不息的狀態,目的已經不是單單的「為何寫」,而是為了「寫下去」。
二、為了鎮痛或鎮魂
時間來到二〇二五年,同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最早的兩篇文章寫於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七年,其餘的二十篇全部完成於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四年之間,這是香港最動盪而封閉的時刻,「反修例」的社會運動還未完全落幕,「新冠肺炎」的疫症隨即展開,中間還有幾個月是兩者重疊一起的。時間像失控的馬達,轟隆轟隆的四處亂撞,撞得地動山搖、城牆破裂而人心惶恐,城外的世界在看我們,我們在城內看自己也看世界,在看與被看的落差中撐住日常生活,「社交距離」、「疫苗通行證」、「強制檢測與隔離」等等,都是這本書的時代佈景!對卡爾維諾來說,寫作是檢測自我不足的鞭撻,是在縫補傷口的生活裡維持活存的能量,而我則在被禁止進入公共場所和朋友聚會、無日無之的抓捕新聞、實體課堂變成電腦虛擬的畫面、戴著口罩呼吸等磨難裡,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或活下去),是因為城市腐爛了、身體病了、心受傷了、思想閉塞了、路被堵住了!因此,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三、系出理論大師的名門
《不合時宜的群像》是一本關於「書寫理論」 (theory of writing)的書,副題「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有兩個指向:第一是個人指涉—研讀理論是一個漫長、孤絕和抗世的旅程,出身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在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選修法國學者佩吉.雅穆夫(Peggy Kamuf)的基礎課程,她是理論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研究者和翻譯家,課堂上鼓勵多元文化的交錯與撞擊,例如不懂中文的她,要求我將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詩翻成中文,然後用英語解釋翻譯的方法和策略,讓我學習如何辯證地處理語言的流動與溝通;此外,她還邀請後現代主義大師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來班上講課,當時他在書頁上的簽名「For Chan, in the memory of USC 」,我還保留至今!
兩年後我轉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 San Diego)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遇上影響一生的老師群,包括日裔文化研究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印裔後殖民理論家羅斯瑪麗.喬治(Rosemary George)、建立城市詩學的邁克爾.戴維森 (Michael Davidson)、巴赫汀(Bahktin)研究者唐納德.威斯令(Donald Wesling)、酷兒理論的跨性別者朱迪思.哈爾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變性後更名Jack Halberstam)、後現代理論批判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既是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又是詩人的葉維廉。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好將夫,他在課堂上常常強調知識是維持公義、對抗強權、揭露黑暗和反省自身的力量,課堂下又告訴我跟他要好的理論大師那些身體力行的動人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說他怎樣在飄離的身分與血癌的纏繞中掙扎,而且充滿睿智和強大的心志,聽著聽著給我植入了許多研讀理論聯繫人性、人生的滋養,「理論」不是紙上談兵,也不再標示權威,因為它的出發點來自改變世界的願景,為弱勢發聲、為自我明證!
我在這群理論大師的教導和熏陶下,逐步深化各個門派的學說,堅持閱讀原典或英譯本,有些英譯本如果有疑問,便跟法文的原版對著讀,而且重複二讀或三讀。這輩子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完成了博士口試之後,印裔的喬治教授說從此我們不再是「師生」關係,而是「同行者」,要一起努力為世界戰鬥,而身旁的三好將夫卻打開隨身的皮箱,跟我說:「這是最新出版的理論專書,回去好好的讀!」出身破碎家庭的我,必須依靠獎助學金才能赴美深造,卻幸運地遇上許多無論學識還是人格都充滿個性的老師,有時候想,或許這是上天給我的補償,讓「良師」補償「無父」的空位!
四、在亂世,不合時宜的獨行者
「書寫理論的獨行者」第二個指向是書中引述的理論大師和文學家,像死於交通意外的巴特(Barthes)、為自己診症的弗洛依德(Freud)、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在邊境服毒自殺的班雅明(Benjamin)、不停給自己挖井的村上春樹、承受童年創傷的里爾克(Rilke)、從捷克流亡到法國的昆德拉(Kundera)、經歷阿根廷極權統治的貝列西(Bellessi)、粉碎作者權威的福柯(Foucault,臺譯傅柯)、透視黑暗和抗衡異化的阿甘本(Agamben,臺譯阿崗本) 等等。他們一輩子特立獨行,睥睨世俗,堅守個人思想的陣地,對抗外在惡劣的環境和生命掣肘,通過書寫活出自己的光彩,走過歷史崩塌的階梯,照耀仍然孤獨的當世。借用喬治教授的話語,我跟這些理論大師和文學家都是同行者,在各自的時代跟世道格格不入,用不合時宜的姿勢敲鑿主流的意識形態或流行觀念,力量或許很孤絕,文字碎裂如風沙,卻也成了一道一道的亂世微光,穿越時代的墓碑。
全書分成「寫作學」、「創作論」和「藝術評論」三個部分,但這樣的編排只是為了方便閱讀,彼此之間不像切割豆腐或磚頭那樣工整和壁壘分明,而作為一個長年的跨界者(或拆界者),創作與評論、文學與藝術、甚至哲學、美學、社會學、政治論述和文化研究等各種理論之間,早已不存在任何派別、科際或類型的牆壁了!因此,我的書寫策略也不按照一般板著臉孔的學術格式,而是企圖糅合說故事的技巧、抒情的感官和論辯的邏輯等元素,不逃避個人言說、或激烈而尖銳的觀點,通過轉化東西方理論大師或文學家的話語,來述說這個城市的時代身世。然而,香港不是孤立的,它跟周遭的地脈相連,而且世界到處亂象和破局,那些地區戰火、街頭抗爭、極權統治或天然災禍,燒得整個地球像一個氣候與人性一起失常的鍋爐,沒有人是局外人!因此,那些標題像〈死前留言〉、〈沒有聲音的尖叫〉、〈凝視孤獨的深淵〉、〈時代的碎裂〉、〈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解放記憶〉、〈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讓我散落四周〉和〈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等等,或多或少能夠燭照暗夜裡一些圍爐取暖的身影。沒錯,我們的四周漆黑朦朧,邪惡的樹在暗處張牙舞爪,海上表面很平靜,但突如其來的海嘯隨時捲起巨浪,而文字像小飛蟲,微小卻有光,只要翅膀依然震動,便仍有扳動地殼的蝴蝶效應!
有人說,在亂世,寫作無用,也有人說,在互聯網資訊氾濫的界面,文字早已貶值!或許這都是對的,但假如寫作和文字真的成了亂世的錯置或錯配,那麼便讓我(或卡爾維諾們)繼續錯下去,反正無用,也沒有阻礙了誰吧?!何況「無用」才能維持獨立和尊嚴,不被收編、磨蝕或利用—黯黑的邊境上,閱讀是光,只要仍有人在看、在寫,光便拉著弧線繼續向前飛翔導引⋯⋯
22.01.2025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喜歡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人,總有自己連著年代記憶的閱讀書單,說幾歲、幾時讀他的第一本小說,前一點世代會說中學幾年級讀《聽風的歌》、或大學時期讀《挪威的森林》,後一點世代大概從《海邊的卡夫卡》或《1Q84 》開始。我一直覺得村上是通過寫小說這個形式來讓自己永遠年青的,而我們卻藉著讀他書寫的世界來哀悼自己的青春,於是他的作品才不斷超越世代的時間和空間。追隨村上三十年,我也有閱讀的年代版圖,加上年復年無間斷的重讀,版圖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印刻了從青澀到青春再到苦澀的生活味道。這一趟不談那些100%的女孩、羊男、電視人、發條鳥的冷酷異境或國境南北,而是用自言自語的方式跟村上的創作觀做一場對話,當然不是面對面的磋商(我也沒有這個資歷),而是文字論述的搭建。
一、鍛煉身體減除文字的贅肉
以前許多人都說作家是文弱書生,中式的想像是鏡頭下文人對著原稿紙吐血的畫面,西方的論述就是蘇珊.桑塔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提及「肺癆」是藝術家的專有病症,但我們知道村上春樹跑馬拉松、早睡早起、不交際應酬,而他竭力維持規律的生活,都是為了應付書寫長篇小說的體力消耗,這種身體力行打倒了慣性的作家形象。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村上表示與其用頭腦、不如用「身體的感覺」寫文章,讓脈搏和心跳形成節奏。他從醫學角度指出有氧運動能夠刺激腦內海馬迴神經元的產生數目,從而提升學習、記憶和創造力,因此,寫作人必須訓練身體,因為體力一旦衰退,思考能力隨之下降,而且人到中年之後,還會無休止的發胖,「物理上的贅肉,也是隱喻上的贅肉」(這個比喻太恐怖了)!村上認為寫作人也是普通人,常常面對日常各種危險與撞擊,而生活和寫作又充滿深度黑暗的力量,必須讓身體變成強大堅壯的容器,才能承載和抵禦得住,尤其是寫作依靠強韌的精神力,所以要建立能夠支撐靈魂「框架」的肉體。
從實際的應用考量,村上的話很有道理,寫作人都是長期埋首書桌疾書或打字(會不會有人站著寫呢),坐骨神經痛、腰酸背痛、眼睛的毛病等都是家常便飯,而沉入深層挖掘人性黑暗的日子,還會迎來因失眠、抑鬱、悲慟而攪纏的各樣痛症,運動身體其實就是釋放負能量、打開閉塞的血脈(仿若內功心法),同時清除體內和腦內的廢物垃圾(清空之後才能裝載)。日本臨床心理學者和治療師河合隼雄更從村上這個主張,歸納出「身體」影響「文體」的概念,那是「連身體性都包含進去的文章體裁和作品」。說得真好,精神力與體力是互相呼應、互為表裡的,化成文字便建構了另類的文本互涉,於是,為了減除「文字的贅肉」,我們還是努力減肥吧!
二、吞下黑暗的力量治療創傷
「不管任何人,在甚麼樣的環境長大,成長過程中都會分別受過傷,都有被傷害過。只是沒有留意到那事情而已。」村上在討論《1Q84 》的創作時,跟採訪者松家仁之這樣說。河合隼雄也提出有些病人受到的創傷太深邃複雜,無法浮現病徵,無論通過心理分析還是藝術行為都無法探究。書寫作為治療,是很普遍的意念和實踐,即使不是作家,也常常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個人創傷,問題是普通人無法將兩者的關係說得確切,而村上與河合的對談卻勾出線條深刻的輪廓來。村上毫不諱言指出寫小說就是自我治療的行為,在形成故事的深沉過程中,浮出個人潛藏的問題;又說寫小說像電腦遊戲的角色扮演,不知道畫面上接續出現甚麼樣的角色,敲著鍵盤便會慢慢形構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那就是一直深埋意識底層的內容;而所謂「故事」,從遠古已經存在,是每個人擁有的物事,寫故事就是發現自己的存在。河合索性說人類某種意義上全體都是病人,問題是有沒有能力將這些病情引發或轉化出來,不單要有表現的形式,還要有力量,而藝術家必須擁有這些能力去承擔時代與文化的病。村上接著補充說,寫小說除了治療作家本人外,也同時必須治癒讀者才行,架起兩者關係的就是「感應」(或包括移情),即使不被讀者接受,被他人批評、厭棄和攻擊,寫作人也必須承受難過,因為當一個作家不能吞下這些負面和憎恨的話,深度可能也出不來。
我比較在意的有三個重點:第一,每個人都有故事,也同時都是病人,如何發現、轉化這些故事,似乎是非常個人的修行了,同樣的事件有人說得很動聽、有人寫得很沉悶,故事是自己的,如何跟他人聯繫,要看搭建橋樑的本領了。或許這就是河合強調作家要承擔時代與文化的病,內裡包含克服自己的創傷,以同理心走入他人的處境,用文字替自己、也替別人承載那些抖動的情緒和心結,從而表現普遍性和普世價值了,壞時代一個一個的過去,最終留下了作品。第二,村上描述的書寫和自我治療過程,也分成許多階段,起初是自發性和無意識的形態,能夠產生淨化的效果;其後進入猶如「挖井」那樣挖掘意識,當生命繼續累積創傷,黑暗的漩渦不斷加深,寫作人便需要強化自己的裝載容量,發展與人互動的關係,擴張故事的幅度,這是他由《聽風的歌》走到《發條鳥年代記》的歷程。事實上,許多作家年輕的時候亮麗地完成了第一個階段,卻無法跨越第二、三個層次,越來越用計算的方式製造「故事」出來,失去了鮮活的氣息和生命的維度。第三是如何面對讀者的「反感」,村上命名為「憎恨的回饋」,就是被文壇前輩、評論人、以至實體的讀者否定和痛恨,出道以來他承受很多。村上說要將這些負能量全部吞下,藉以推動寫作的齒輪,才能強化文字的深度。這行動真不容易啊,寫作人必須具有瞭解自己的初心、堅定信念的雄厚基礎,才能不為負面評價而動搖。「名氣」總像黑色的深淵,會能以虛榮將人的創造力吸入和消解,不為市場和他人認同而寫,不單需要勇氣,還需要澄明的意志!
三、結語:世代平等
村上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很明確的說:「我向來主張:世代之間沒有優劣之分。絕對不會有某個世代比另一個世代優秀,或低劣的情況⋯⋯當然傾向或方向性方面可能分別有差異,但質量本身則毫無差別。」又說:「各個世代在面臨要創造甚麼的時候,只要分別往﹃擅長領域﹄勇往直前地推進就行了⋯⋯沒有必要對其他世代感到自卑。或奇怪地擁有優越感。」香港也很喜歡講「世代論」,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的平臺上,充斥世代優劣的比較,在這些新世代優於舊世代的講談中(還未有達到論述的架構),總潛藏許多怪異的情緒:第一是懺悔,以前自己做得不足也不夠好,現在的困局由我來承擔責任(真夠自負,時代不是屬於你一人的)!第二是疏懶,中老年已經不行了,讓年輕人去做(或犧牲)吧(推卸的肩膊像山泥傾瀉,最好不要煩擾我)!第三是偽善,站在道德的頂峰,向山腳負重前行的人指指點點,高呼時代是你們的,卻從不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跟世代二元論相反的情況是一場運動浩浩蕩蕩的開展,經歷時間和空間的醞釀浸染,總有許多不同年齡層的人,在不同的崗位和領域以血肉和精神付出,正如村上所言,當中沒有優劣、只有差異,所以毋須自卑或奇怪地擁有優越感。因此,無論你或妳第一本讀村上的小說是《挪威的森林》還是《海邊的卡夫卡》,在文學閱讀的邊界上,我們都是平等的!
17.02.2021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說故事的人 〉
偉大的說故事者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擁有在個人經驗的階梯上升降起落的自由—這是一個論述,也是一個比喻,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班雅明的文字難讀卻又有牽引追看下去的動力,他的大部分著作屬於理論系列,卻佈滿詩意和象徵,他是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之後讓我體驗跨文類書寫的實踐,讀到盡頭不再汲汲於界分到底是論述還是故事,而是沉浸於那些街道、人潮和城市的生活氣息,以及星空、顏色、光影等細節羅列。班雅明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原是論析俄國作家尼古拉.科夫(Nikolai Leskov)的寫作,卻以說故事的方式勾出甚麼是「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概念,而且連接歷史和記憶,讓我思考當代城市的身世。
一、故事的根源:流徙與留守
「說故事者」已經消失了,「說故事」的藝術已經終結!班雅明在文章的開首便這樣慨歎,而消失和終結的原因是生活經驗的貶值,人們甚至沒有交流經驗的能耐。二十世紀是戰爭和媒介發達的年代,前者的殘酷及其帶來經濟、民生與精神文明的崩潰,讓痛苦的人無法言說;後者伴隨科技而來鋪天蓋地的資訊,代替了表述的方式。班雅明追溯以前口述故事的流傳形態,說的和聽的彼此交換經驗;他說「故事」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遠遊外地的經歷,另一種是活在原居地的體驗,遠行回來的人必有故事要說,而居留者也有許多當地的事件或傳統可以分享,如何敘述一個或一些地方,便是故事的根源。班雅明指出,說故事者很務實,以教誨引動道德和智慧,目的不是要為難題提供答案,而是打開故事延展下去的可能,從而追尋真理—當我們想弄清楚一些事理的時候,便會繼續聆聽和講說故事,這是溝通的橋樑,將分散的人聯繫起來。
班雅明開宗明義的闡釋讓我串連香港的處境,「後二〇一九」的歲月裡,我城的故事也有兩種,一種來自海外的流徙者(流亡或移民的),另一種便是留守本地的人,合起來便是如何「書寫一個地方」的命題。跟班雅明的論述有點不同,我們的流徙者大部分都不再回來,那麼他/她們的故事到底跟誰說呢?只是,「香港文學」的定義從此跟過去截然不同,產生的變貌更繁複、分歧也更多!前些時候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提問:移民遠走的人不能一輩子寫香港故事,寫完了離去的經驗後還如何寫下去才是創作更大的考驗;另一方面,留在原居地的人每天承受城市不合常理的異變、不合比例的崩塌,當文學不能改變現實的時候,該如何擺放寫下去的位置和理由?時代的板塊仍在分裂和移動中,二〇二三年的這一刻,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距離讓我看清變異和發展,但可以確定的是,評論人和文學史研究者已經不能用舊有的方式理解香港文學的組成,如果說書寫「香港」的都是這個地方的文學,這是個怎樣的「地域」邊界?無論是游徙還是留守的,又是怎樣的身分結構?在離散和連結的矛盾中,我們怎樣評價「如何寫」的形式和「寫甚麼」的內容?寫給誰看的這個「誰」到底是誰?
二、直面不可說的死亡
寫於一九三六年,〈說故事的人〉剖析當時媒介社會導致人類溝通出現碎片化的現象,資訊以洶湧而搶耳的姿態佔據每日生活,人們得到一堆沒有關連、彼此割裂、平庸、冰冷而彷彿事不關己的訊息,無從也不去求證當中的真假。人們不再需要「故事」,而是五光十色和無遠弗屆的資訊,「說故事」的藝術從此沒落和消失。班雅明認為故事無論來自鄉村、海洋還是城市,都是一門溝通的手藝,讓說故事者沉澱生命,猶如製陶工人抓住黏土器皿上的指印那樣再現出來(又是一個生動的比喻),而為了呈示生命,說的故事必須直面死亡。在遠古的時候,(西方)人不忌諱死亡,而是勇於思考永恆與再生的力量,但自十九世紀以降經歷一系列公共衛生、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公眾與私人的規範之後,死亡從日常生活中隔離,在現代社會裡,死亡被越推越遠,以至不可觸碰。班雅明指出,「死亡」是生命的來源,也構成故事的底本,當它被裁決變成禁忌,便削弱了故事的根基,無法形構道德和智慧的內容。班雅明這個論述,使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臺譯米歇爾.傅柯)著名的文章〈論其他空間:烏托邦與異托邦〉(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當中勾勒二十世紀在城市規劃下,為了開發更多有用的土地,不惜將原本建在市中心和教堂旁的墳地遷移到邊陲的地方,促使人減退了對死亡的宗教信仰與膜拜、對家族記憶的存念和延續。「死亡」觀念的改變,不但顛覆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同時也影響了文化和藝術的想像;對班雅明來說,「故事」被平板的資訊取替,說故事者也不得不失去了應有的位置,而更重要的是「死亡」不單關乎個體,也聯繫歷史—這才是班雅明苦苦扣連的核心論述!
三、故事作為記憶:記錄破敗的歷史「故事」連結生死(life and death),生死是年代記(chronicle),年代記是史詩(epic),史詩是史料編纂(historiography),而史料的基礎便是記憶(memory)——這是班雅明猶如鎖鏈環扣的論述線路,他說只有通過全面的記憶,史詩式的書寫才能吸收發生的事件,使它超越死亡的力度,因此,記憶是歷史的形態!「記憶」跟時間(Time)競賽,是生存留下的唯一憑證,一代一代流傳下來便建構了傳統的鏈接,只有當故事一路說下去,才能完成歷史的敘述。美國後現代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的《班雅明:多重面向》(The Benjamin Files)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班雅明這樣的扣連,是以「故事」來重新定義「記憶」,記憶標誌客體或物體的存在,同時通過值得紀念和可供記認而識別,那就是傳統說故事人的述說;這些民間藝人是歷史的見證者,化身為口述的、老輩的、圍在篝火旁或榕樹下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關於戰爭的、死亡的、疾病的故事,藉以重建希望和治癒創傷。寫到這裡,頓然發現班雅明和詹明信彷彿在論述我城的境況,這是理論超越了時空?還是人類歷史一直在走圈圈的輪迴?當亂世來臨,真相會變成濁流混淆不清,記憶會被禁止、清洗、截斷、抹掉或取替,我們如何書寫自己的年代記?怎樣跨過時代的生與死?納粹時期的猶太裔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藏匿於不見陽光的閣樓,以日記形式記錄逃避政治屠殺的日常生活和青春的蠢動;史太林時代被流放的索隱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用集中營一天的敘述框架,寫出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剝削與生活的嚴酷;還有經歷布拉格之春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政治抓捕的黑暗沼澤裡,融入個人的生命、希望與傷痛,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倡議以活在真實中的信念來對抗極權。有人說亂世文章無用,的確,文學不能改變現實,但可以改變人心,拓闊對將來的想像,給予勇氣和希望,同時記錄曾經發生的人和事情。這是由班雅明的概念延伸而來的當代思考,說故事者是時代和地方的歷史見證人,層層挖開被掩埋的記憶和真相,用故事承載道德和智慧,只要有人想聽,故事便會延續下去⋯⋯
(因篇幅所限,此篇為部分內容節錄)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
作者序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發需要尋求文化上的突破與革新,而「寫作」是其中一個戰場。對於這樣的提問,一些作家覺得太空泛而採取防衛的姿態,只簡單的回應說沒有其他專長;也有作家洋洋灑灑列出非常宏偉的理由,像為了娛樂自己和大眾、教導別人一些道理、改變世界、傳揚前衛的思想、抒發情操、獲取名氣和報酬等等。卡爾維諾認為這些宏願跟他都有很遠的距離,他既不從事教育工作,也不相信寫作可以改變現實,而且有時候連自己的理念都感到疑惑或發生錯誤,又如何給予別人指標?相反地,寫作不單要付出勞力的代價,而且也會對自身產生暴力的回擊,因此,他只能從個人細小的位置思考這個為何而寫的議題。
一、由「為何寫」到「寫下去」
卡爾維諾列出的理據有三:第一是由於不滿意以前的書寫,所以必須不斷寫下去以尋求補救、更正和圓滿,寫作是將舊有寫下的東西刪除、抹去和擦掉,再以新的、未知寫成怎樣的作品替代。第二是每當看到有人寫得這麼好的時候,自己也心動技癢而躍躍欲試,可惜優秀的作品通常都無法模仿,卡爾維諾只好將書放回書架上,然後突然一些字詞、一些句子湧現腦海內,於是他不再惦記那本寫得成功的書或任何類近的範式,而是專注於思考自己還未寫出來的那本著作!第三是學習個人不懂的東西,不關乎寫作的技法,而是特殊的生命經驗(life experience),不是為了教導別人,或以此作為寫作材料,而是發掘自己不足的痛苦意識;在這種狀況下,為了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卡爾維諾說必須不停累積資料、概念、觀察和經驗,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知識和智慧,只能寫於紙上的剎那才能達到和完成。卡爾維諾的闡述,在我看來,活脫脫就是怎樣維持寫作行動(action of writing)的實戰方法:不滿意過去完成或成就的作品,想像和追求未來寫得更好的表現,以寫作填補個人的欠缺,同時不斷更生和蛻變自我,不讓寶貴的經歷流失,印記每個瞬間的人生體驗—這是一種流動不息的狀態,目的已經不是單單的「為何寫」,而是為了「寫下去」。
二、為了鎮痛或鎮魂
時間來到二〇二五年,同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最早的兩篇文章寫於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七年,其餘的二十篇全部完成於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四年之間,這是香港最動盪而封閉的時刻,「反修例」的社會運動還未完全落幕,「新冠肺炎」的疫症隨即展開,中間還有幾個月是兩者重疊一起的。時間像失控的馬達,轟隆轟隆的四處亂撞,撞得地動山搖、城牆破裂而人心惶恐,城外的世界在看我們,我們在城內看自己也看世界,在看與被看的落差中撐住日常生活,「社交距離」、「疫苗通行證」、「強制檢測與隔離」等等,都是這本書的時代佈景!對卡爾維諾來說,寫作是檢測自我不足的鞭撻,是在縫補傷口的生活裡維持活存的能量,而我則在被禁止進入公共場所和朋友聚會、無日無之的抓捕新聞、實體課堂變成電腦虛擬的畫面、戴著口罩呼吸等磨難裡,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或活下去),是因為城市腐爛了、身體病了、心受傷了、思想閉塞了、路被堵住了!因此,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三、系出理論大師的名門
《不合時宜的群像》是一本關於「書寫理論」 (theory of writing)的書,副題「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有兩個指向:第一是個人指涉—研讀理論是一個漫長、孤絕和抗世的旅程,出身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在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選修法國學者佩吉.雅穆夫(Peggy Kamuf)的基礎課程,她是理論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研究者和翻譯家,課堂上鼓勵多元文化的交錯與撞擊,例如不懂中文的她,要求我將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詩翻成中文,然後用英語解釋翻譯的方法和策略,讓我學習如何辯證地處理語言的流動與溝通;此外,她還邀請後現代主義大師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來班上講課,當時他在書頁上的簽名「For Chan, in the memory of USC 」,我還保留至今!
兩年後我轉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 San Diego)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遇上影響一生的老師群,包括日裔文化研究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印裔後殖民理論家羅斯瑪麗.喬治(Rosemary George)、建立城市詩學的邁克爾.戴維森 (Michael Davidson)、巴赫汀(Bahktin)研究者唐納德.威斯令(Donald Wesling)、酷兒理論的跨性別者朱迪思.哈爾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變性後更名Jack Halberstam)、後現代理論批判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既是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又是詩人的葉維廉。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好將夫,他在課堂上常常強調知識是維持公義、對抗強權、揭露黑暗和反省自身的力量,課堂下又告訴我跟他要好的理論大師那些身體力行的動人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說他怎樣在飄離的身分與血癌的纏繞中掙扎,而且充滿睿智和強大的心志,聽著聽著給我植入了許多研讀理論聯繫人性、人生的滋養,「理論」不是紙上談兵,也不再標示權威,因為它的出發點來自改變世界的願景,為弱勢發聲、為自我明證!
我在這群理論大師的教導和熏陶下,逐步深化各個門派的學說,堅持閱讀原典或英譯本,有些英譯本如果有疑問,便跟法文的原版對著讀,而且重複二讀或三讀。這輩子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完成了博士口試之後,印裔的喬治教授說從此我們不再是「師生」關係,而是「同行者」,要一起努力為世界戰鬥,而身旁的三好將夫卻打開隨身的皮箱,跟我說:「這是最新出版的理論專書,回去好好的讀!」出身破碎家庭的我,必須依靠獎助學金才能赴美深造,卻幸運地遇上許多無論學識還是人格都充滿個性的老師,有時候想,或許這是上天給我的補償,讓「良師」補償「無父」的空位!
四、在亂世,不合時宜的獨行者
「書寫理論的獨行者」第二個指向是書中引述的理論大師和文學家,像死於交通意外的巴特(Barthes)、為自己診症的弗洛依德(Freud)、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在邊境服毒自殺的班雅明(Benjamin)、不停給自己挖井的村上春樹、承受童年創傷的里爾克(Rilke)、從捷克流亡到法國的昆德拉(Kundera)、經歷阿根廷極權統治的貝列西(Bellessi)、粉碎作者權威的福柯(Foucault,臺譯傅柯)、透視黑暗和抗衡異化的阿甘本(Agamben,臺譯阿崗本) 等等。他們一輩子特立獨行,睥睨世俗,堅守個人思想的陣地,對抗外在惡劣的環境和生命掣肘,通過書寫活出自己的光彩,走過歷史崩塌的階梯,照耀仍然孤獨的當世。借用喬治教授的話語,我跟這些理論大師和文學家都是同行者,在各自的時代跟世道格格不入,用不合時宜的姿勢敲鑿主流的意識形態或流行觀念,力量或許很孤絕,文字碎裂如風沙,卻也成了一道一道的亂世微光,穿越時代的墓碑。
全書分成「寫作學」、「創作論」和「藝術評論」三個部分,但這樣的編排只是為了方便閱讀,彼此之間不像切割豆腐或磚頭那樣工整和壁壘分明,而作為一個長年的跨界者(或拆界者),創作與評論、文學與藝術、甚至哲學、美學、社會學、政治論述和文化研究等各種理論之間,早已不存在任何派別、科際或類型的牆壁了!因此,我的書寫策略也不按照一般板著臉孔的學術格式,而是企圖糅合說故事的技巧、抒情的感官和論辯的邏輯等元素,不逃避個人言說、或激烈而尖銳的觀點,通過轉化東西方理論大師或文學家的話語,來述說這個城市的時代身世。然而,香港不是孤立的,它跟周遭的地脈相連,而且世界到處亂象和破局,那些地區戰火、街頭抗爭、極權統治或天然災禍,燒得整個地球像一個氣候與人性一起失常的鍋爐,沒有人是局外人!因此,那些標題像〈死前留言〉、〈沒有聲音的尖叫〉、〈凝視孤獨的深淵〉、〈時代的碎裂〉、〈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解放記憶〉、〈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讓我散落四周〉和〈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等等,或多或少能夠燭照暗夜裡一些圍爐取暖的身影。沒錯,我們的四周漆黑朦朧,邪惡的樹在暗處張牙舞爪,海上表面很平靜,但突如其來的海嘯隨時捲起巨浪,而文字像小飛蟲,微小卻有光,只要翅膀依然震動,便仍有扳動地殼的蝴蝶效應!
有人說,在亂世,寫作無用,也有人說,在互聯網資訊氾濫的界面,文字早已貶值!或許這都是對的,但假如寫作和文字真的成了亂世的錯置或錯配,那麼便讓我(或卡爾維諾們)繼續錯下去,反正無用,也沒有阻礙了誰吧?!何況「無用」才能維持獨立和尊嚴,不被收編、磨蝕或利用—黯黑的邊境上,閱讀是光,只要仍有人在看、在寫,光便拉著弧線繼續向前飛翔導引⋯⋯
22.01.2025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
目錄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I 寫作學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沒有聲音的尖叫:杜哈絲的孤獨寫作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凝視孤獨的深淵: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時代的碎裂:跟創傷同命相依⋯
發現病徵,成就藝術:弗洛依德的「屏障記憶」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
肖像畫與寫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藝術觀⋯
II 創作論
小說的歷史學與輸入法:昆德拉的時代思慮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站著寫作:西西的小說講臺
從手書記事到電腦鍵盤:日記書寫
解放記憶:從班雅明思考抒情詩的當世景觀
在亂世,我們棲居於詩:海德格的詩學
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貝列西寫在動盪時期的詩
III 藝術評論
文字的刀刃:評論人作為藝術家
為誰而寫和寫了甚麼:藝術評論的危機與機制
讓我散落四周:福柯的〈甚麼是作者?〉
如何說好論辯:伊格頓的〈評論的功能〉
功利庸俗的評論機制:蘇珊.桑塔的〈反詮釋〉
拒絕溫柔的年代:札記《藝術評論的終結》
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阿甘本論「當代性」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I 寫作學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沒有聲音的尖叫:杜哈絲的孤獨寫作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凝視孤獨的深淵: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時代的碎裂:跟創傷同命相依⋯
發現病徵,成就藝術:弗洛依德的「屏障記憶」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
肖像畫與寫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藝術觀⋯
II 創作論
小說的歷史學與輸入法:昆德拉的時代思慮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站著寫作:西西的小說講臺
從手書記事到電腦鍵盤:日記書寫
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