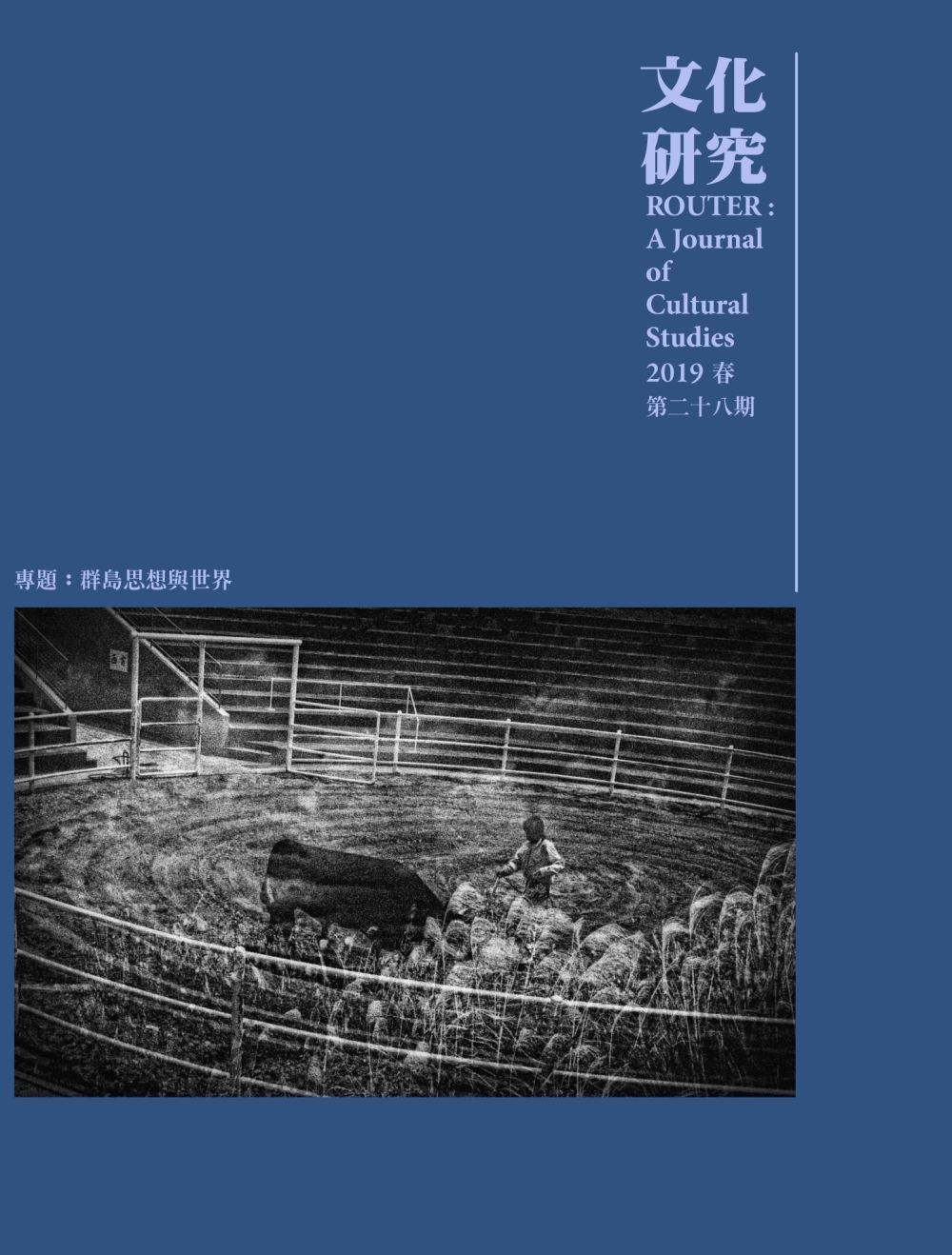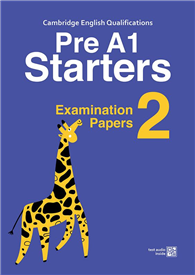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沒有人是一座島嶼No Man is an Island ──編輯室的話
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唐恩(John Donne)的〈沒有人是一座島嶼〉,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詩作。此詩將人的孤寂以及人際連動的想望,透過島嶼和大陸的比喻,表露無遺。島嶼和大陸,因而被預設為一組相連又分隔的對比:島是孤獨的,大陸是擁擠的,但無論大小,總是暗地相接,唇齒相依。然而,這樣的比喻流露著一種以大陸觀天下的心態。其實,島嶼並不孤獨,本來就有著島島相連的群島想像。海流並非分隔彼此的監獄,而是連通群島的大洋,群島人民自由來去,順著季風與洋流,呼應、交往而共存,直到大陸予之霸道強佔、獨攝、切割。群島並非相對於大陸,自處邊緣的存在;它們有自己的網絡和結構,既不仰賴大陸,也從未與之截斷。島嶼就在那裡,不渺小也不孤獨,它們自成世界。如果大陸也能放棄佔有獨斷的妄想,或許它也能在方言的幽微與國境的豐饒中,探觸到自身的群島靈魂。
本期專題「群島思想與世界」,希望透過一連串島嶼的影像、詩歌與論著,重新展開一個群島的世界,並且將其思想呈現在世人的眼前──不為反抗、不為挑釁,只是呈現自身莊嚴的存在。透過濱田康作和東松照明的影像創作,島嶼被想像與理解為一種「共鳴體」,在太陽的曝曬和水波的折射中相互輝映,那是從島的物理形式去理解其生物與文化形態的方法,光影的互涉與水波的共振,暗喻了人的漂流與語言的演化,以及歷史的複寫和文化的交涉。如同客座編輯今福龍太和朱惠足在〈序言〉中指出的,「自從薩依德宣稱『亡命』之精神姿態日益成為現代人普遍的生存條件以來,『群島』這個家也成為我們從現實或象徵的『家鄉』被拋擲後,漂流上岸的地方。但那不是能夠安心的『家』,因而也不是能夠『自得自在』的場所。置身於那樣的流謫之所,正是現代的我們之世界道德產生的條件」。換言之,群島並非浪漫的懷鄉,而是在資本帝國與民族國家下的人類生存境態,漂浮著、流浪著,無以所終,無處可至,卻又在浮沉中自足,在相遇的想像中完滿。於是乎,行旅不再具有壯遊探險的氣魄,而是對身份、言語與國境進行存在主義式的探索。一如當前流行的「北漂」話語,人的漂浪,離土而棲,正是對現實最嚴格的批評,而群島之謎則在於如何在浮塵之世重新找到牽絆彼此的關係──在國境之外,方言之間,想像之極限。
非常感謝今福老師與惠足將這批豐富的文獻帶到我們的面前,讓海島臺灣能夠不再獨弔自身孤懸海外的身世,或是留戀西邊或東邊若即若離的大陸;讓我們往北向南,甚至穿透自身,抵達地球上的其他島嶼,看見群島之浮沈、徬徨、勇氣與堅持。我們亦感謝協助翻譯的朋友們──惠足、于珊、佩怡、耀宗、書媺、家瑄、鈺淩等──帶我們穿過文字的迷障,抵達言語的深處,落腳在故事的家鄉與詩的遠方。
除了專題外,本期收錄了四篇論文和一篇實驗書寫。楊建章的〈音樂、國家、與時間性:以日本二戰前後音樂關於日本特質的論爭為例〉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關於日本音樂當中日本特質的論爭,尤其關注日本1930年代起,音樂與法西斯政治體制的共鳴關係,以重新展開音樂特性中關於時間與空間的討論。楊建章強調,自明治維新,日本進入現代以來,天皇制成為日本國體的基石,歷戰敗而不改,這種強調單一血緣萬世一系的時間感,恰恰與充滿歷史斷裂的現代,形成一種違和感。因此,現代日本音樂的創作者與體制──包括深受西方音樂教育薰陶的音樂家與俗稱「在野派」的作曲家──要如何面對與彌合這樣的斷裂,在曲式和曲風上調合西方與日本,就成為一大挑戰;這也成為現代日本音樂史研究上的重要課題。楊建章整理了日本從1930年代到戰後的一系列討論,扼要地分析了幾個重要的辯論和發展,並提出重新檢視「民族風格」作為現代音樂形式的要求,以再次展開對於音樂現代性及其意識形態的討論。這對於我們重新面對文化與家國的共構和共謀,有著莫大的助益。
同樣討論音樂,陳培豐的〈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將焦點轉向臺灣,特別是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當中的社會邊緣人。陳培豐採取文化翻譯的觀點,來看待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對日本「望鄉歌謠」與「股旅演歌」的翻唱與轉譯。他強調,雖然臺、日兩國都受益於韓戰所帶來的經濟提振,但是在這個經濟歷史脈絡下所出現的農村移民,就臺、日兩國的文化記憶而言,仍舊透露出不同的感受,反映出臺灣基於其歷史與經濟政策所發展出來的獨特情感結構。陳培豐強調,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裡的社會邊緣人面對的是農村落敗,階級幽閉兩座大山,因而成為因失業流落街頭,終而成為失聯人口或淪落風塵的社會底層。「望鄉歌謠」中綿密無盡的傾訴、悲情、頓挫、哀嘆,乃至柔弱的男子氣概,反映的正是這群人在都市中無依無靠的困境,以及對公平和正義的呼求。閩南語裡所謂的「出外人」,不僅僅是離鄉者,更是在都市中迷失、淪落,回不去農村的漂浪之民。流行音樂所承載的文化記憶與情感,於是提供了我們理解社會狀態與經濟結構的重要線索,一如知識分子對自身的主體性探問。
黃琪樁的〈殖民現代性主體的生成與破滅:再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某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接續著陳培豐的問題意識,將文化記憶與情感的問題轉向了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探問。藉著對龍瑛宗著名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展開深入討論,黃琪樁思考著日據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如何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開展與衰敗,理解自身主體、情感與存在的問題。強調龍瑛宗創作當時臺、日社會上普遍感受到的「不安」,黃琪樁指出,文學──一如流行音樂──乃是龍瑛宗面對社會變動,苦思自身存在的載體,而在這個渾噩與妥協時代中逐漸解體的知識分子自我,正是在西方與東方的對比中感受到主體形成的內在張力。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雖然孺慕現代,但在殖民地中,無法成為日本人的他們,因此也無法真正擁有「向上發達」與「教養」這兩種現代性特質,只能轉而追求有限的經濟個人主義,並且透過這些現代性的濾鏡回望滋養自身的鄉土。這種扭曲與挫敗不只是個人的,更是殖民地社會的共業。從這個角度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也是一首關於社會邊緣人的哀歌與怨曲,並且深刻地突出了個人主體之有限,主體的詰問最終必然轉向社會的命題。
羅皓名的〈邁向反知識原詩:詩人工作者谷川雁的聲響認識論〉再將我們的焦點從臺灣轉向日本。在這篇研究戰後日本重要詩人谷川雁的文章裡,羅皓名不只梳理了谷川詩學與臺灣的連結,更花費了相當的工夫展現谷川如何從1960年代日本安保運動的脈絡中逐步展開「反向知識」的批判工作,連結詩與散文,朝向大眾意識中的原點探去,以解放、批判僵固且自我封閉的學院知識,並且為另一種源於大眾語言與常民文化,但不以其為終點的知識與思想,打造語言與認識論的基礎。尤其他提出了「聲響認識論」這個饒富深意的概念來重新理解谷川的詩學與政治,以說明詩之於谷川大眾想像中的深刻意涵,並藉之在其中探究更為深刻的,乃至於是根源性的,抵抗的可能。羅皓名的文章,不只是華文世界至今最為深入而完整的谷川雁研究,更有效地為安保運動之後日本思想的變化進行了系譜性地整理。更重要地,他在谷川著作中發掘出的聲響、大眾、共鳴與知識等議題,亦為「群島思想與世界」專題中的文章做了極為細緻而深入的舖墊,讓我們看到在「群島共鳴體」這個想法的深處,其實是1960年代反帝國、反極權、反佔領的安保抗爭所遺留下來的思想遺產。這項遺產,至今仍以藝術行動的形式進行跨境思想上的踫撞,以及對現實政治的探索。
在實驗書寫這個欄目裡,董顯亮的文章〈壓抑的「言語」與再造的「身體」:《香・夭》重演之過程及其評論〉,雖然討論與記錄的是一齣關於香港的音樂舞蹈表演,但其思索的內核其實亦與「群島思想與世界」有所共振,既將香港放入群島的視野裡,也敦促我們在香港的困局中思考群島共鳴,跨域同行的可能。董顯亮關心的問題是,這樣一部音樂舞蹈,從創作、排演到演出,從標題、台詞到評論,究竟如何面對與回應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至今仍難平復的複雜情緒,創作者與舞蹈者又如何將自身的故事擺放在當前香港這樣的一個空間裡?如果《香・夭》不只是一首確認香港已死的安魂曲,那麼它又如何召喚過去與未來,在「我城」的九死一生中,讓港人看見彼此,攜手向前?在六月以降的「反送中運動」逐漸走向終局之際,這樣的反思與情緒尤其值得我們重視。但願香港經此劫難,能夠浴火重生,得其所願。
最後,本刊編輯室要為本期拖刊,向讀者們、作者們,尤其是擔任本期客編的今福老師和惠足老師致上最大的歉意。準時出版本是學術刊物的基本義務,但是過去一年,學刊面臨稿量與人力不足的雙重擠壓,一方面好些通過的文章未能如期進稿,致使本期陷入漫長的等待,另一方面幾位編輯同仁也進入了完成論文的長期抗戰當中;在學業與刊物兩難全的境況中,我們決意以同仁的學業為優先考慮,因此造成的不便,我們深感愧疚與遺憾,只能希望讀者和作者能夠同情與諒解。此外,今年九月,本刊進行小幅改組,有王志弘(臺大城鄉所)與汪俊彥(臺大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程)兩位加入編委會,並成立國際諮詢委員會,以強化學刊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社群的連繫,開拓稿源,促進合作。我們特別感謝前任編委李根芳和林純德過去兩年在編務上的協助與支持,並熱烈歡迎邱澎生、賀照田、羅小茗、周耀輝、魏月萍、鈴木將久、白池雲、劉奕德、洪國鈞和李明皓等朋友同意擔任國際諮詢委員,予以協助,本刊不勝感激。在這些朋友與各位讀者的支持與鼓勵下,本刊也將會更加努力,繼續推動文化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王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