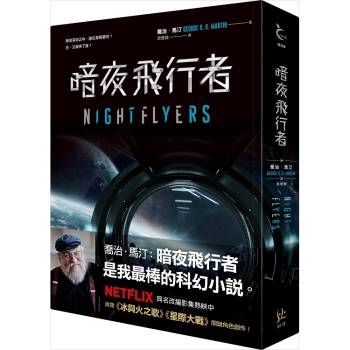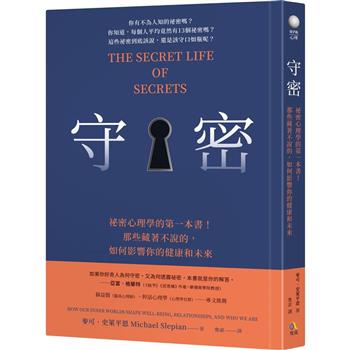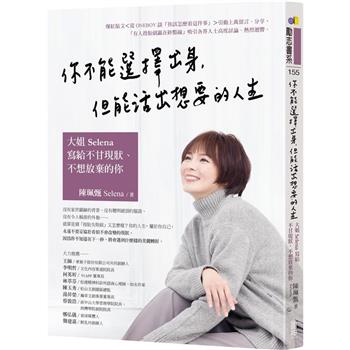本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早期創作的代表作,是對法國“新小說”派的傳承和創新,在對景物的描繪中穿插故事情節,青年男女的愛情,海灘上天真的孩子,一切都融入了詩意的畫卷中。在景物描寫中運用通感、幻想等表現手法,亦真亦幻,虛實結合,把由對社會環境的感知轉向一種對于存在的思考,爲我們揭穿幻象的同時,也把他所期待的存在方式精雕細琢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作品指出了西方城市文明所面臨的問題和人們的恐懼,以濃厚的神秘氣氛、深遠的哲理寓意、新穎的寫作手法獨樹一幟。
「巨人和普通人不同,他們說話的時候不用詞,而是用電閃雷鳴。他們的嘴上裝有一座秘密的閘,打開閘門,詞便如泥石流一般奔騰而下,這是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語言。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麽,沒有人聽得懂。他們的詞如同湍急的怒濤,氣勢汹汹。他們的語言,對我們來說,是一場驟不及防的海上風暴,烏雲翻滾著從地平綫上涌來,凜冽的風在呼嘯,大海在咆哮,狂風中巨浪滔天。思想的主人。這個世界上有思想的主人。而我們却在逃避這個事實。
我們以爲自己在思考。有時候我們甚至以爲,思考根本不需要詞,腹內一陣莫名的顫動,嗓子眼裏一串奇怪的抽搐,或是後腦勺中突如其來的一個激靈,就叫做思想。但這不是真正的思考。這個世界上沒有可以被稱作思想的東西。如果世界沒有這般嘈雜,如果天地間寂靜無聲,也許,思想才真的會出現。像一隻金色的圓盤,撥開蒸騰的雲霧,露出地平綫,冉冉升上漆黑如墨的天空,在戰鼓氣壯山河的助威中,發出驚天動地的嘶吼。」
作者簡介:
勒克萊齊奧,一九四○年生於法國尼斯,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訴訟筆錄》,並獲得勒諾多文學獎。至今已出版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說,隨筆,翻譯等。一九八。年,勒克萊齊奧以小說《沙漠》獲得保爾·莫朗文學獎。一九九四年,他在法國《讀書》雜誌一次讀者調查中,被評選為當代最偉大的法語作家之一。 二○○八年,勒克萊齊奧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章節試閱
我要說:解脫出來!是時候了,正是時候。再耽擱,就爲時已晚。突然間混沌消散,萬物顯形。世界的輪廓明朗起來,綫、圈和結逐漸清晰可辨。癌已開始擴散,向廣場和空地蔓延。此刻,它聳入空中,儼然一座十五層的高樓,在混凝土柱子上保持平衡。再耽擱,你將再也看不見天空。看不見海,看不見風,也看不見平原。碩大的黑影正以飛機的速度奔跑,它如禿鷲般舒展雙翼,鋪天蓋地。黑影中的你,心在狂跳。無論你怎樣跑,也只是徒勞。黑影總能抓得到你,它的速度快過你的心跳,你逃不出它的掌心。不要再等了。逝去的每一秒都打成一個新的結,每天,都有一堵墻在某個地方竪起、一扇窗被封閉。對此我曾一無所知。我曾以爲世間萬物無章可循,它們的循環往復也只是偶然。我曾以爲人是自由的,所有的路和門都在眼前,可以任我選擇。我曾以爲有方向、有進程,就像在原始叢林裏,一枝一葉相輔相成,萬籟有聲、草木有情。但我不曾想到,人們恰恰因此而去破壞身邊的草木,因爲他們見不得天成造化,只想要人爲、人力、人工。他們想要一座草木都長著五官的森林,也即所謂“社會”。
就這樣發生了,如夢如幻。當我們猛然清醒,才發覺一切是真而不是夢,才發覺可怕的夢幻意味深長。醒醒吧!眼睛只需睜開片刻,你就可能看見天光。我們猛然清醒,發現自己始終囿于樊籬之內,從未擁有自由。我們想弄個究竟,費盡心力、絞盡腦汁,也是枉然,因爲我們自己也只是夢幻。如同影片裏的人:放映機把膠片投上銀幕,我們就在幕布上變幻的光影中。如此豈能自由?或者說,如同書中的人:白紙黑字的書頁間,我們寓形于詞句之內。我們在一切之內,對此却毫不知情。很多東西我們都信以爲真。其實它們的出現就是爲了讓我們相信,爲了在我們耳畔輕聲說出那個帶小舌擦音的句子:我是自由的。我也聽到了這個聲音,它給了我繼續生活的渴望。如果不是因爲這個聲音,我不會做自己現在所做的一切:等公交車,聽日本箏樂的碟,抽薄荷味的烟,在雜貨店裏等店主對我說:您要點什麽?等女人、錢、革命、希望或者報紙,等困倦蛛網般向我襲來。等。無盡的等待。但我是自由的,不是嗎:自由!意識、選擇、死亡、荒誕、幽默,我對這些假玩意深信不疑。
但是那些舉足輕重的東西,那些真實的東西,被藏在夢的另一邊,藏在樊籬之外,怎麽可能瞭解?慢慢地,我們醒來,穿越黑影重重。我們摸索著走過臥室,家具在劈啪作響,很多東西都在往下掉,巨大的撕裂聲震耳欲聾。這是怎麽回事?但我們沒有時間弄清究竟,依然跌跌撞撞地前行。終于來到了夢的另一邊,縷縷輕風拂面,我們如醉如痴。我們就這樣蹣跚學步,是的,蹣跚學步。
解脫出來!穿過夢的黑色帷幔,你就能看到萬物的另一邊。詞是囚禁你的牢籠,該遭唾弃。別再對鏡自憐,自我意識有什麽用?只是另一個外表,另一層僞裝。不如抄起鐵棒,把這些反光的玻璃砸碎。
也許現在我們可以有所作爲。我的意思是,我們也許能够擺脫自己,如同一隻氣球冉冉升空。爲了自由,我們應當這樣做:表達。不僅用嘴,還要用手、用脚、用肚子。只用詞表達,幷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讀書裏的詞,我們始終是囚徒。
我們還要去語言的另一邊——語言的締造者一邊,在語言的另一邊表達。像翻手套一樣,把每個詞都翻個裏朝外,掏空所有的內容。每次表達都應當像飛機擺脫大地,騰空而起,都應當具有衝破牢籠的威力。而在此之前,我們一直是奴隸。我們掌握的詞都是爲了服從、爲了奴役,只能寫出奴隸的詩歌和哲理。是時候了,把詞武裝起來,扔出去,說不定這一扔,它們就能沖出樊籬。
快,快:墻越來越多,拔地而起,直沖雲霄。墻的繁衍速度比老鼠還快。每一秒,都有一堵新的墻竪起。墻、窗、裝甲門、帶刺的鐵絲網、栅欄、鎖。人們曾經以爲墻的出現皆是偶然,出現在哪裏都無關緊要。我原來也這麽想,墻就是墻,有什麽大不了?可事實幷不是這樣。這不是普通的墻壁,而是牢獄的高墻。有人在蓄意謀劃,圖紙已經就緒,他們暗中早就破土動工。認識認識他們吧!這些躲在暗處的人!他們的眼睛在玳瑁眼鏡後閃著光,因爲凡你所不知,他們都明瞭。他們的詛咒讓世界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們神秘而可怕,因爲他們知道如何讓詛咒永生永世都靈驗,就像他們認識路,能一直抵達走廊的盡頭。他們在嘹哨中看你在地上爬,他們預先知道你要做的一切。他們在地上辟出布滿倒鈎的通道,看你像蟲子一樣在裏面蠕行。怪异而恐怖之處在于,他們不是世界的締造者,不製造行動和思想,但他們却對萬物的關聯了如指掌。
人成爲人的研究對象,唯一的對象。解脫出來!不要再任人分析、琢磨。誰也沒有瞭解人的權利。因爲,瞭解意味著更勝一籌。醒醒吧!白晝的圖景慢慢顯現,于是我們看到了陷阱。罪惡的手遍設機關,你每一挪步,都有被吞噬的危險。
對言語的痴迷,是唯一的自由力量。要說!趕快!不論以什麽方式,不論說什麽。嗓子裏語流汹涌,衝開了口腔粘膜,嘴唇上下翻飛,就像樹枝在狂風中搖擺。風後跟著暴雨,我們已經聽到迫不及待落下的雨滴。嘴在動,却什麽也沒說出來。女人們站在亮處,大張著嘴說,可我們什麽也聽不見!這怎麽可能?難道空氣凝固了,有了水一樣的密度,玻璃一樣的冰冷?人們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會立即被氣泡吞沒,然後消失殆盡?說吧!說吧!把氣泡打破!說什麽都行,怎麽說都可以。如果你沒有詞可說,就不要說詞。喊叫、咳嗽、唱歌,隨便發出什麽聲音都行。你就說:
Zip!
Flak!
Wlapi!
但是空氣依舊透不過聲音。有人手裏拿著刺穿過鼓膜的細針。耳朵在傾聽,却什麽也聽不見,變成了魚和蛇的耳朵,形同虛設。誰讓耳朵失聰?陽光下有身材高挑的美女在側耳傾聽,可她們什麽也聽不見,如同被悶在無聲的世界裏、幹瞪著眼睛的魚。
世界怎麽可能這樣安靜,怎麽可能沒有一絲響動?我要告訴你:我看見衆多的男男女女在光天化日裏長久伫立,他們其實都又聾又啞。我呢,我還能聽到窸窸窣窣的動靜。但我幷不因此而驕傲,因爲當世界需要雷聲的時候,這只是低語。大張著嘴、扯著嗓子對著麥克風發出的嘶吼,在我聽來却輕得像管道中的水流。成群的人在撕心裂肺的呼號中葬身火海,在我聽來,動靜也不會大過梳齒摩擦髮絲,或一根火柴燃著。巨型炸彈在天邊爆炸,升騰起百公里高的蘑菇雲——死亡之雲,對我來說却只是一聲屁響。不,我一點都不感到驕傲。
我們用棉花團塞住了耳朵和鼻孔,把眼睛藏在墨鏡後。解脫出來。摘掉墨鏡,是它使你漠然。我們的視網膜上被人貼了圖片,虛假的影像遮擋住視綫。有人在我們眼前放了兩台電視機,幷對我們說:你看到的就是真相,是事實,是生活。有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欺騙了我們。墻。墻上畫著幾何圖形:這就是一幅幅生活圖景。白色的布景,黑色的邊綫,每個虛構的細節都熠熠生輝。到處寫滿我們應當遵從的指令:女人,孩子,工作,戰爭,死亡,歡樂。必要的依據也一樣不落:照片、示意圖、曲綫、數據。眼前的圖景是那麽的顯而易見,不容置疑。叫人怎麽可能不相信?只靠眼睛、手、充滿詞的嘴巴怎能走出迷宮?怎能走出自己?
世界幷不安靜。它的安靜只是因爲我們在談自己,爲自己而談。我們什麽也聽不見,如在井底。生命伊始,我們就把車窗關閉,爲了不聞不見。
打碎玻璃!冰冷的玻璃上,光綫在瑟瑟發抖,仇恨和欲望得以重生。光綫就此止步,目光也就此止步,因爲它們穿越不了這冰冷透明的圍墻,我們的保護墻。但這是多麽可怕的保護!我有話要說,它却不讓我作聲。我想對樹、對石頭、對大海、對鳥、對沙漠說,我想遠遠地壓低聲音對它們說,像打電話一樣。不用眼睛,不用詞,不試圖占上風或者說服,而是像這樣,簡單而平靜地對它們娓娓道來。但在玻璃窗前,我被制止,于是我攥起拳。玻璃的另一邊,是所謂“不可企及”的一切,如同一場盛大的表演,我只有觀看的份。空氣、水、草、大海、光。寶藏近在咫尺,天堂從未這樣觸手可及。對玻璃的仇恨!對玻璃墻的仇恨!我攥緊的拳頭是一隻鐵錘,石子是供我調遣的軍隊。拳頭再也不能鬆開,永遠不能。我手上的骨頭都焊在了一起,指甲像釘子一樣嵌進肉裏。解脫出來。攥起拳頭。如果你的手攥不起來,或者你擔心拳頭會鬆開,那就找一桶冰,把手伸進去,等待。我攥緊的手指不帶半點生氣,指尖沒有一絲暖意,冰融成的水在我的腕骨中流淌。不堪一擊的壁壘。不要以爲用玻璃就能遏制我周身的力量,不要以爲可以把世界圈養在魚缸中。長著狗一樣鼻尖的海鱔在玻璃墻裏游來游去,它們說的話,沒有人能聽見。蟒蛇把頭使勁甩向玻璃,也只是白費力氣。而我,用我的混凝土拳頭,我能砸碎玻璃,我肯定能成功。蒼蠅會因爲飛行而饑餓、疲乏,但我,我不是蒼蠅。我有一隻攥緊的拳頭,我要出擊。注意!是時候了。只一念之間,甚至更快,拳頭已經打出。幷沒有猛烈的衝擊,玻璃一點也不結實,輕而易舉就被粉碎:衆多的欲望和仇恨已經耗盡了它抗擊打的能力。它就這樣碎了,像被腐蝕過的或者早就有裂紋的玻璃一樣,在一聲脆響中粉身碎骨。鋒利的邊沿,粘著血。光綫依然冰冷。空氣進來了,不是一下子灌進來,而是緩緩流淌。聲音……什麽聲音?我們什麽都沒聽見。沒有聲音。充其量也只是竊竊私語,像車流涌動時輪胎摩擦地面的聲音,偶爾夾著幾聲烏啼似的喇叭。沒有聲音,幾乎萬籟俱寂。還是同樣雜亂無章的窸窸響動。沒有痛苦,沒有喊叫,也沒有呼喚。嗓音,在哪裏?氣味,在哪裏?光彩熠熠的圖畫、閃電、自由和愛的行動、樹的語言、天堂,它們在哪裏?叛徒!卑鄙!玻璃的後面,竟然是另一層玻璃!
我們想用拳頭打碎玻璃:可事實是,我們永遠也辦不到。玻璃太多。不是一層、兩層或十層,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萬、不計其數。玻璃的大小不一:有的像山一樣高、像海一樣寬、像天空一樣沒有邊際;有的則很小,小到我們必須用鑷子和放大鏡才能把它們打穿。形狀也各异:平面的、球形的、螺旋形的、星形的。水滴似的玻璃,眼泪似的玻璃、湖水似的玻璃、海洋似的玻璃。有的玻璃把整座城市覆蓋在它們的穹隆之下,有的玻璃在空中竪起無形的墻。有的玻璃在人的眼睛裏,在女人琥珀色的虹膜深處。更可怕的是,有的玻璃在你的身體裏,看似透明,却如同懸崖峭壁,使你身體裏的各個部分永遠彼此分隔。所有這些,你是一點一點知道的。可是今天,必須衝破阻隔。一切都是砸向玻璃的錘子。一切都是攥緊的拳頭。如果每秒鐘進行上千次擊打,出現上千次斷裂,你說不定就能獲救。
... ...
我要說:解脫出來!是時候了,正是時候。再耽擱,就爲時已晚。突然間混沌消散,萬物顯形。世界的輪廓明朗起來,綫、圈和結逐漸清晰可辨。癌已開始擴散,向廣場和空地蔓延。此刻,它聳入空中,儼然一座十五層的高樓,在混凝土柱子上保持平衡。再耽擱,你將再也看不見天空。看不見海,看不見風,也看不見平原。碩大的黑影正以飛機的速度奔跑,它如禿鷲般舒展雙翼,鋪天蓋地。黑影中的你,心在狂跳。無論你怎樣跑,也只是徒勞。黑影總能抓得到你,它的速度快過你的心跳,你逃不出它的掌心。不要再等了。逝去的每一秒都打成一個新的結,每天,都...